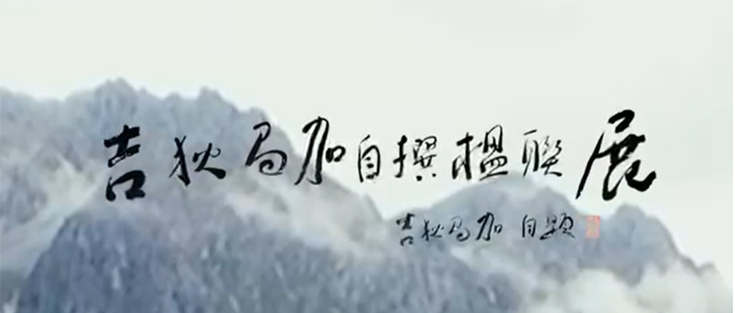兴安:繁花在天边怒放
—— 2021年度《草原》阅读手记
作者:兴安
纵览2021年的《草原》,“自然写作”无疑是这一年的亮点,即使从全国文学期刊来整体考察,也应如是。《草原》聚集多位作家、评论家,重新倡导“自然写作”,可以说是“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的一次整合和梳理。近年来,中央号召和倡导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保护环境、关注自然和生态平衡成为人们的共识。“自然写作”的提倡应时而生,是作家和文学对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对人类未来发展的一种自觉反思和担当。
当然,提倡“自然写作”,并非要求作家都跑到荒野上去,它应当是一种身心的自我净化,是让我们重新思考和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找回已经被我们遮蔽或丢失的自然之眼和自然之心。《草原》第1期的前言《自然写作:构建一个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以及张炜的《我行走,我感动》对此阐述得非常明确。张炜对“自然写作”的思考,多年前便在其《融入野地》中有过表达,一个人面向大地,与自然万物静默相视,将身心完全融汇于原野、山峦和丛林,体悟和惊喜于生命的繁衍、生长和奇迹。这是我心目中“自然写作”的经典范例。之后我又在陈应松的《森林迷境》中找到了这种感动,森林和自然在他眼中,是无法企及的仙境和神奇力量,它可以改变我们以往的认知和世俗经验。正如文中所说:“在我的身体里,许多过去看似有用的东西在崩溃,而又有许多东西在悄悄重建,这是森林的法则。”
总体考察这一年的“自然写作”,可以说是佳作频出,各有分量。徐刚、梁衡、蔡测海这三位文坛老将都拿出了自己年度最好的作品,尤其是徐刚的《金沙江笔记》,以诗人的情怀徜徉古今,将历史与现实、文化与自然景观融于一体。中年作家是“自然写作”的主力军,如陈应松、王松、鲍尔吉·原野、皮皮、李青松、任林举、葛水平、苏沧桑、庞余亮、凸凹、周蓬桦等等。同样面对一棵树,皮皮的《大树来途》写了一位老人与一棵橡树的奇妙关联,老人不仅是这棵树的所有者,更是将其视作自己的亲人和生命寄托,为此她要尽全力保护它,及其周围所有。王松的《谁是谁的树》则记录了中国乡村中农民与树不同寻常的关系,神秘的灵魂文化和丧葬习俗,关乎生者的归宿与死者的安宁,让人对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产生思考。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乡村无疑是与自然最近距离的所在,用列奥·马克斯的话说,“乡村是一种中间景观”,介于城市与自然之间。纵然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乡村正在被千篇一律的建筑样式所替代,但那些相对偏远的乡村以及乡村留给我们的记忆,却依然保持着原初的宁静和深度。我以为,这种所谓“中间景观”或许正是“自然写作”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苏沧桑的《冬酿》记录了南方山村“冬至酿酒”的民间遗俗。酒由粮食酿造,是天地孕育的精华,而冬至则预示着春天行将到来,万物开始复苏。作者看似写酒,写节气和风俗,实为写世道人伦,抒发生命中的欢乐。如果说苏沧桑的基调是浪漫主义的,那么庞余亮的《在那个湿漉漉的平原上》则是冷峻的现实主义,给我以痛感。他笔下的乡村是严酷的,严酷到让我想到了刀耕火种。“那个湿漉漉的平原上,坐在石磙上的我,似乎是蜘蛛做过的一个梦。”很久没有读到这么真切、这么刻骨铭心的乡村景象了。
李青松的《大兴安岭笔记》和《牦牛与野牦牛》,前者是对中国北方最大的绿色屏障大兴安岭林区的考察,后者是对西北祁连山野生牦牛和驯养牦牛生存状态的追踪。王蕾则是一位陌生的年轻作者,她的《滴水,即世界》以田野调查的手法,以水为例,揭示了云南大理草海保护区所面临的生态危机。
在“自然写作”这个集体中,“70后”乃至“80后”是一个正在上升的群体。这其中有周华诚、傅菲、宋晓杰、东珠、格日勒其木格·黑鹤、棉棉、周李立等。在我看来,格日勒其木格·黑鹤是一个朴素的自然主义者,这与他的族属以及长期生活在内蒙古草原有关。蒙古族“万物有灵”的自然观造就了他体察天地万物的独特视角,而常年置身草原营地的半游牧状态的生活,又让他拥有了其他作家无法取得的生存和写作经验。《驱熊犬》写了一只名为阿兰卡其的猛犬,为了保护驯鹿与来犯的黑熊搏斗,受了严重的内伤,但它依然在临终阶段完成哺育幼崽的使命。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仅写了人与犬的感情,同时也描写了使鹿鄂温克人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的生存智慧。《杭盖诺亥》是对一个家族狼群的寻踪和考察。在作者的笔下,狼并不是让人憎恶和恐怖的异己形象,而是有自己性格和生存法则的普通生灵。
“自然写作”对内蒙古的本土作家来说,有着得天独厚的地域和文化优势,况且他们中的不少作家原本就有“自然写作”的经验。比如艾平,她生长于呼伦贝尔,几乎走遍了那里的草原和森林。她的《北行第一站》写的正是她无数次自驾深入草原腹地的经历。她了解草原上的每一条河流,熟识草场和牲畜,她尤其关心当下牧民的艰辛与快乐,她甚至尝试以蒙古牧民的视角和腔调讲述他们的故事,这使她的写作彰显出独特的审美价值和社会意义。
还有两位本土女作家也值得关注。刘惠春的《春天,在西鄂尔多斯》写的是被誉为“活化石”的濒危珍稀植物四合木,它自远古陪伴地球和人类至今,赋予大地生命的能量。谢春卉的《夜夜夜夜夜》是一组草原和森林的笔记。其中《上帝的牧场》描述了作者的一次奇异经历。在一个几乎见不到人的牧场,人瞬间回到了自然的原初状态,此刻,人几乎是多余之物,自然以其神秘的内在轮回和逻辑,凝视着人类的贪婪和傲慢。
值得注意的是《草原》刊发的两篇关于“自然写作”的评论,王昉的《自然写作考辨与当代困境》和钟媛的《梭罗的复活及其对现代性的启示:重提自然文学的价值与意义》,对“自然写作”的概念、缘起以及与“生态文学”的差异,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阐释。其中王昉对当下文学创作中出现的“两种不同的二元对立的极端思维: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还有“生态文学”写作中“拘囿于生态批判的现实功利性向度”等等的批评,都给人以启发。
在“自然写作”之外,《草原》本年度的其他栏目也保持着相当的水准。本年度“特别推荐”,一篇是特·官布扎布的《人类笔记》,另一篇是海勒根那的中篇小说《巴桑的大海》。《人类笔记》虽然只是作者长篇散文的节选,但也足够管窥其构架的宏大与思想的深远。作者曾说他要沿着人类种群起源、生存、发展的线索,探寻和破译人类生存的密码。他提出生存资源的争夺与再分配才是人类发展和进步的真正动因。从《蒙古密码》到《人类笔记》,官布扎布实现了从本民族出发、放眼世界的飞跃。《巴桑的大海》应该是海勒根那最成熟的作品之一,作品开始回归他早期作品《父亲鱼游而去》的“超现实”叙事手法,讲述了一个失去了双腿却痴心向往大海的少年的故事。《父亲鱼游而去》里的父亲最终变成了一条鱼,而《巴桑的大海》则是儿子为了追寻父亲的梦想投身大海。两篇作品相隔多年,彼此却有某种神秘的因果关联。
“小说现场”栏目,我比较看好娜仁高娃的《驮着魂灵的马》。小说写了一个蒙古牧民与马的情感。为了生计,他将马卖给了马术队,结果马在一次赛马中与其它马相撞而死。他就像失去了魂魄的行尸走肉,孤独地在荒漠上游荡,以酒为食,以荒林为家。小说描写了牧民与牲畜、与大自然的紧密关系,尤其揭示了这种关系在发生现代性转化之后,牧民的迷茫和困惑。
邓文静的中篇《太阳以东,月亮以西》以童年的视角书写人性的善恶。其中孩子与祖父间的情感,尤其是在祖父临终状态下,爷孙俩隐秘的情感互动,令人感动。同样是童年视角,达拉的《阿库萨的太阳》写了失去双亲的孤儿阿库萨与小狗相依为命,在森林中自由地生活。小说的结尾耐人寻味,在小狗不幸离他而去后,与世隔绝的他被一曲盛大的琴声所吸引,音乐的力量让他抛开了一切。
高占江的中篇《桂花一朵也芬芳》和鲍尔吉·原野的短篇《演出开始了》作为“主题创作”,其对当代社会的观察和对历史细节的呈现,都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前者写的是在扶贫脱贫和乡村振兴进程中人们生活和心理的变化,后者写的是“乌兰牧骑”的往事。作者用笔幽默风趣,让人忍俊不禁。
“草原骑手”是一个专为推出内蒙古籍青年作家设置的栏目。近几年,“90后”的渡澜、阿塔尔、苏热等已经给我们带来不少惊喜,而“00后”作家晓角的出现,则让内蒙古文学的未来增添了底气。晓角,一个失学的农村女孩,17岁就充分展现了她的才华。《清冷之人》是她的小说处女作。艾略特曾说:“具有自我意识的诗人就像是审视自我的旁观者。”小说里那个“他”应该是她自身的真实写照,她将自己设定为另一个人,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冷观自己作为诗人的言行和状态,有自嘲,有安慰,也有指引。瑠歌的《一无所有》则是一篇很特别的域外题材小说。一个叫莫里的富家女孩,无所事事却自视甚高,偶然结识了一个流浪汉,在与流浪汉的交往过程中,看到了资本社会虚伪而又冷酷的本质,也学会了怜悯和同情。
如果让我在本年度的年轻作家中挑一篇我最欣赏的小说,扬清的《月末归不归》将是我的选择。小说的故事扑朔迷离,时空叠错交汇。这是一个“太爷爷”“爷爷”与“我”的感伤故事,首先是“太爷爷”的等待,等待“爷爷”每个月末回来为他剃一次头发。老父子俩的情感只能借助一次次短暂的相聚,获得平复和安慰。但真相是“太爷爷”已经老年痴呆,他其实一直活在过往的时空里,而“爷爷”也早已因病离世,他只能在“太爷爷”的幻觉中一次次复活。小说最让我感动的是“我”送“爷爷”回家时的情景,“爷爷”即将回到他那阴冷黑暗的黄泉世界,但两人的对话依然是那么平静坦然,让人感觉,生者与死者的距离其实不该那么遥远和荒凉。
“塞外随笔”本年度有两篇散文需要推荐,首先是安宁的《人间切片》,作品写了人世间的冷暖,写亲情邻里的嫌隙,但是它深刻地揭示了人性,况且出自一个敏感而又早熟的孩子的视角,就愈发显得真切合理,比如写母女俩在姨妈家的尴尬遭遇,写对逝者的尊重,以及生死两界亲人无法忘怀情感和思念,都给人一种温暖的感动。田鑫的《农事诗》也是一组写故乡的作品,细腻而温馨。其中《锄头》写父亲衰老后,开始侍弄早已被人遗弃的锄头,希望借助这些已经消逝的农具缅怀过去。《碗筷》则以儿时的回忆和民间敬先人的习俗,记述了碗和筷子在人生中的重要位置。
相对于“自然写作”的红火,“北中国诗卷”在这一年里却相对沉寂。已过不惑之年的“北中国诗卷”,确实需要思考一下未来的走向。由此我想继续以晓角为例。“我们惊异于这样的风/一天之内/土和人就混为一谈//桃花腐叶风中相聚/塑料和戒指没有区别/没有区别的/甚至还包括黑白/应该惊异于这样的风/风中的我们/一无所有。”这是晓角的组诗《土豆城的公告》中的《沙尘暴》一首。很难想象它出自一个不到18岁的农村女孩之手,它没有修饰,真实灵动,且一语中的。客观地讲,《草原》本年度的诗歌还是有相当水准的,比如广子的组诗《苍天》。他的诗冷眼望去外貌豪放粗粝,读后却会发现其内里的细腻和阴柔,充满了莫名的感伤和孤独气息。比如这首《大雁飞过》:“大雁飞过,带走鸣叫/我从未飞过,也没落下好名声//每次大雁飞过/我就感到一阵孤单//每次大雁从我的孤单中飞过/我就感到,我是掉队的那一只。”而他的《把照耀古代的太阳从岩石里挖出来》却又是另一种气象,潇洒而又义无反顾。桑克的《在任师的告别会上》是一首典型的口语诗,记录了在诗人任洪渊先生的葬礼上,“北师大诗群”的诗人们送别恩师的情景。诗的结尾让人唏嘘:“写不下去了,让雨替我写下去吧……/雨,越来越大,比我更擅长记录悲痛的雨……”女诗人中,刘琳的《大地上的神仙》给我印象最为深刻,她的诗能自觉地将个人的独特境况转化为人类共通的经验和思考,比如《拴马石》《旧汽车》《熬药》等。
原载于《草原》2022年第一期

作者简介:
兴安,文学评论家、水墨艺术家、编审。蒙古族。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北京作家协会理事、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文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世界华文创意写作协会理事。著有散文集《伴酒一生》《在碎片中寻找》及评论近百万字。主编有《九十年代中国小说佳作系列》《女性的狂欢:中国当代女性主义小说选》《蔚蓝色天空下的黄金:中国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代表作品展示》《中国乡土小说大系》《知识女人文丛》等几十部。水墨艺术作品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意大利贝纳通学术基金会、法国作家之家、巴黎艺术中心、古巴哈瓦那大学艺术学院等国内外藏家收藏。2018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白马照夜明 青山无古今:兴安水墨艺术展”。2020年在国际文化交流艺术馆举办“在碎片中寻找:兴安水墨艺术展”。曾参加书堂山当代文人书法周书法展、梦笔生花:当代语境下的文人艺术展等。

作者:兴安
来源:草原文学月刊
https://mp.weixin.qq.com/s/qbaAmYJp_BCx5SXXexHtTQ


 纯贵坊酒业
纯贵坊酒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