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诗人的城市诗写

诗人安琪(刘不伟/摄)
“城市诗”在中国当代诗歌语境里并非一个陌生的概念,1980年代,宋琳、张小波等人出版了《城市人》并先后在《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展》和《中国当代文学思潮》杂志上提出了鲜明的“城市诗”诗学主张,他们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中国“城市诗”派。有意思的是,30多年来,“城市诗”一直不温不火,并未获得足够的重视,城市诗的书写者也相对稀缺。“中国古代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制和格局中,古人与土地河川交往甚密”(张德明),古人们写起田园诗、农事诗堪称游刃有余,由此形成一系列相对稳定的美学词汇和象征指向一直影响到今日的新诗诗人。现今很多诗人的写作其实是旧体诗的白话译本,所写的事物、所抒发的情感、所向往的人生,就像活在当代的古人。但这类诗依旧拥有强大的作者群和读者群,刊物也中意这类诗作,毕竟每个中国人血液里流动着的依旧是传统的血,教育所输入、环境所熏陶,很难改变。所谓的“诗意”在中国当代,就是小桥流水、就是春暖花开,诗人们处理起农业文明的题材身手不凡,面对工业文明就不免捉襟见肘了。
“上海是中国首个现代化的城市,城市生活丰富多彩,许多生活内容与形式已经在根本上超越农业文明、田园隐逸范畴,对包括诗歌在内的艺术提出了挑战”,批评家许道军教授“挑战”一词道出了城市诗写与乡村诗写的关系,它不是继承而是另辟蹊径,城市诗写要寻找自己的意象、自己的表达方式,要打破习见的“诗意”,重新创造“诗意”,这是一个艰难的历程。经常见到的是,诗人们一面享受着工业文明、现代文明带给他们的便捷和舒适,譬如飞机、空调、电脑,乃至抽水马桶,一写诗就歌颂农业文明、咒骂工业文明,这里面有心态问题和写作能力问题,他们写不了城市诗歌,只能抱着农业诗歌粗壮的大腿不放,相比于城市诗,农业诗的大腿确实还很粗壮。真让这些诗人定居到农村去耕田种地,保证他们个个叫苦,迫不及待要回到城市。这就是当下我们的诗歌写作现状之一。
北京跟上海不同,有极其现代先锋的气息,中国各界最高端的人才几乎都汇聚到此,北京也有极其腐朽的封建王朝的遗存,故宫、紫禁城、颐和园,都是帝制时代的产物,北京周边的农村也并未全部城市化,像宋庄这一个举世闻名的艺术区,艺术家所租住的依旧是农民的房子。这一个混杂的复合型城市有一个庞大的群体称之为“北漂”,北漂这个词兴起于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历经30年而不衰,迄今已成为一个固定词汇。北漂诗人群体的写作和北京这个城市一样,也是混杂而丰富,各类题材都有,本文我想分析的是北漂诗人的城市诗写作。
北漂诗人因着各种原因离开自己的家乡来到北京,对北京这座城市有何感受,认同还是拒绝?构成了北漂诗人城市书写的一个主题。诗人许多直接说,“北京就是我的家”,小海赋予北京一个新名词,“梦想之都”,于丹用“这是一个巨型城堡”来形容北京,郭福来“走在北京的路上”,身子虽然缩小成蚂蚁,心却拔得很高,这些青春与激情尚在的诗人,对北京充满着勃勃旺盛的想象,他们有行动力,有干劲,北京对他们而言,有未来,有奔头。诗写北京更多的是这么一种,从北京风物入手,写北京地理、北京风俗,李肇庆的“潭柘寺”、周瑟瑟的“动物园”、安琪的“菜户营桥西”、花语的“北京地铁”、张小云的“卧佛寺”、姜博瀚的“新街口”,角度独特令人过目难忘的还有杨北城的《散落在北京的朋友》,写了33个北京地名,每个地名又分别对照着与此地名构成反差或对应的朋友的体征,他让青光眼住在灯市口、弱听者住在锣鼓巷、左撇子住在右安门,等等,杨北城此诗可以列入城市诗写的典范。北漂诗人就这样用诗歌的形式把北京这座城市搬运到纸上,每一处地理都蕴涵着写作者的生命体温和语言尝试。诗写北京还有这么一种,回向自己内心,体察自己与北京的关系,闭上眼睛对北京这个城市做冥想式的追问,对自己选择北漂做刨根问底的反思:杨拓在小寒日的京城街头,看见一丝不挂的乞丐,只能无奈地一声叹息;张后因为“你”不在了,就把北京当作“一座荒城”;蔡诚在北漂的宿舍里一遍一遍问自己,你“幸福了吗”?读之心酸;老巢在一次又一次的搬家之后终于明白,“和家一样可靠的名字是我租用的”,哀莫大于心死啊,连名字都不属于自己。安琪的《极地之境》则触及了这样一个永恒的悖论和内心的挣扎,“一个/出走异乡的人到达过/极地,摸到过太阳也被/它的光芒刺痛”。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是北漂队伍不断壮大的一个原因,农田被征用盖房,耕田的成本和所得的回报不相抵,迫使青壮年农民出外打工谋生,北京成为他们的选择之一。打工遇到欠薪怎么办,读读孙恒的《天下打工是一家》《团结一心讨工钱》,一辈子稳稳地躲在体制的饭碗里的人当能从此诗看到另外一个世界。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光怪陆离的人,沈浩波诗中的那个已婚女“马丽”,被老板一句“我爱你”哄住,死心塌地为他卖命,这样的人自然不仅北京这座城市有,此诗的现实意义也因而不仅局限于北京。
宋庄作为艺术家的集散地早已闻名世界,它自成一个小世界,颓废、奋进、快乐、悲伤、一夜暴富、落荒而逃,这里每天都在上演着生活的悲喜剧,居住在这里的诗人群体自然是这个小世界最有力的观察者和书写者,沈亦然《活得简直就像一件艺术品》以自嘲的方式,写出了北漂者与家人的矛盾冲突;阿琪阿钰用“飘在宋庄的毛”来形容宋庄形形色色的艺术家无 根的状态,特别有画面感;牧野则用文字记录下了一个反叛者的行为艺术(《关于冬天的回忆》);潘漠子的“808路巴士”宋庄人都不陌生,这是通往宋庄的最著名的一趟巴士,在这趟巴士上,一切皆有可能……宋庄是一个真正“相逢何必曾相似”之地,在这里,你可以尽情释放你内心的魔鬼,宋庄当然也是需要你去挣养家活命的口粮,区别只在,在他处用体力,在此处用艺术、用脑力。我特别羡慕宋庄的艺术家们,羡慕他们时时行走在空气中都是艺术气味的宋庄。
2017年,我和师力斌博士联合编选了一部《北漂诗篇》,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这是北漂诗人的第一次诗歌集结,在编选过程中我发现,北漂诗人写乡村写田园的反而不多,这让我很有一种欣喜,仔细想想也正常,如果诗人们迷恋乡村、迷恋土地,他们自然不会选择北漂。北京是一个锻炼人的地方,诗人们投身于此,被各种不可测的遭遇击打所迸发的创作灵感,自然以北京这座城市所提供的生活种种为主,这是我认为的北漂诗人城市诗写的理由。而此时,居住在自己的城市安稳过日子的诗人们正闭门造他们的田园诗和乡村诗,那些诗,古典诗词里可以淘得出的。
研究城市诗不可绕过北漂诗人。当然,北漂诗人所有的,沪漂诗人也有,粤漂诗人也有……北漂之北,可替换为任何一座城市,如果你选择了漂。
2018-5-15,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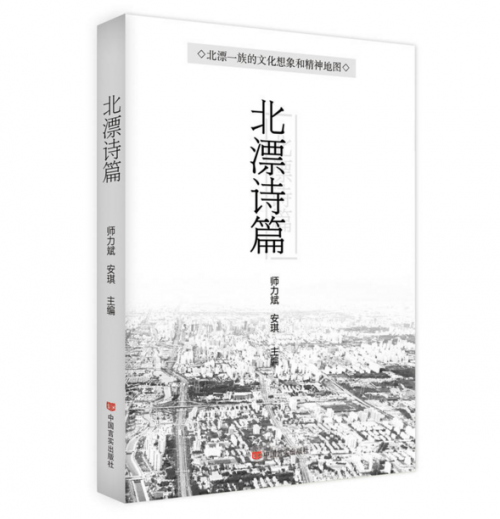
作者:安琪
来源:安琪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c557e20102xr31.html


 纯贵坊酒业
纯贵坊酒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