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头记
作者:乔辉
一
元旦一过,在北京空军总院挂了个号,治疗头疾。
五六年前,头顶偏右一块指甲大的地方发痒,淡红。理发师说,毛囊炎,遂推荐等离子洗发水,两千多,不管用。几年下来,红斑如侵略版图,先东一块西一片,后竟合龙,占领了整个头顶,日渐稀疏的头发如种植在赤壤上的荒年庄稼,萧条而羸弱。经常痒,一挠,无边头皮萧萧下,大煞风景。
开始求医问药,北京大医院、个人小偏方,中医蒙药,试了个遍,确诊为头部银屑病。但无论哪个大夫都会问我,喝酒吗。喝。吃这个药一定要戒酒。啊?!
一次吃蒙药,大夫说一个月必愈。二十多天时,外地好友来呼小酌,看他们推杯换盏,我仿佛成了陌生人,便拿起电话:
——杨大夫好,我打个比方,吃了头孢再喝酒会死人,吃您这个药再喝酒会死吗?
——呃,倒不会死,就是你前面的药都白吃了。
如拔河,反复许多次,去年底,敌方大获全胜,银屑病开始向身体流窜。
北京空军总院皮肤科的蔡主任说,一定要戒酒啊!另外,要把头发剃了。第二天,曾经长发飘飘后来板寸挺拔的我终于变成了秃瓢。
二
想想第一次剃秃头竟是三十六年前的事了。
从小都是母亲给理发,那时,一个大院十三四户,二十多个男孩子,一把神奇的推子每月穿梭。很多时候,推子缺油,扯得头皮生疼。上高一了,班里很多男生穿着时髦,发型有郭富城头、马拉多纳头,潇潇洒洒、顾盼生姿。而我,还是母亲理的“锅盖头”,其实没人在意我和我的锅盖头,但我总觉得女生们扎堆一起,指指点点、突然爆出哄的大笑,其中一项是耻笑我的发型。终于,强硬地向母亲摊了牌——我以后也要去理发馆理发。
一天晚饭后,母亲说,去老刘师傅那里理吧,钱我已给了。于是,人生第一次坐在可升降的椅子上,脖子以下都裹在洗得泛黄大布里,即梁实秋说的“虎皮宣”,刘师傅理得很认真,终了,一照镜子——秃瓢!
原来,母亲为节约,提前告诉了刘师傅,理得尽量短点,以延长理发周期。结果刘师傅会意过“深刻”,一步到位。
翌日上学,戴了顶帽子,还是被后座的同学看出了端倪,自习课上,猛地揪下我的帽子,全班哄堂。
顺理成章的,就是回家和母亲吵闹。这次争吵后的十一年,母亲故去了,又过十八年,父亲故去。今天,当年过半百的我顶着秃瓢,写下这段文字时,泪已潸然。
三
几年后,到通辽上大学。校外商业街布局是典型的十来家小饭馆夹一家理发馆,随便进了一家。
老板兼理发师漂亮、丰满,理发店只有我们俩,九月的午后,燠热无比,头顶的电风扇“嗤嗤”转着,热仿佛凝滞,空气中弥漫着暧昧且迷离的味道,女理发师的胳膊偶尔蹭一下我,细腻光滑又若有若无,恰勾起我再被蹭一下的欲望,她在我身后时,有时竟能感觉到她的胸,顶顶的。我脸红心跳,想逃离,却又希望这次理发能无限地延长下去。
这次理发也成了心里的一个秘密,多年来秘而不宣,我想,这算是早年的一次性启蒙吧。
记忆中,除了这一次,我是绝不喜欢理发的。其一,当被禁锢在那个椅子中时,“呆坐如僵尸,轻易不敢动弹”,眼睛亦被摘去,对面的镜子一片模糊,根本看不见理发师每剪下去的绩效,尤其在刮脸时,我的颈下、后脖袒于剃刀,耳边响起赵传的歌:每一个早晨,在浴室镜子前,却发现自己活在剃刀边缘,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殆殆乎危矣”之感。其二,太浪费时间,那几年,在风剪云、圣尼阁办过理发卡,其实,发型早已处理好,然后,理发师一根一根地修剪,他是用消耗漫长的时间来体现这项工作的物有所值。其三,现实中的理发师绝不像美国小说家拉德纳笔下理发师惠蒂那样喋喋不休,只顾诉自己的苦,他们先是辛勤耕耘,临近尾声才循循善诱,对发型满意吗?还需如何修?最后,他们会关切地讲,哥,你最近头发发脆,我们这里新添一款洗发水正治这个,纯进口的。多少钱。洗发乳加护发素一套1680。
今年,终于解脱了,北京大夫要求剃秃头。董小姐说这个简单,遂买来推子,纵横几下,落发簌簌如落叶,脑壳即成蛋壳,省时又省力。过两天,小小的头发茬长出来,自己用电动刮胡刀一剃,又油光锃亮了。
但董小姐的收费绝不低于风剪云,她理由充分:发型虽简单,但扫地特别费劲,发屑到处都是,犄角旮旯,我得收拾半天。
开价吧。
一次200,办张年卡吧。
嗖,2400元,微信转账
四
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伤损”的年代,剃光头竟然是种刑罚(上古五刑之一),曰“髡”,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在呼市,有两个写诗的朋友,广子和赵卡,年轻时都长发飘飘,如迪克牛仔或金毛狮王,近几年不约而同剃成秃头,轻易地从一个极端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俩当然不屑髡刑之说,但我觉得,在内蒙古,如果诗歌写不过广子赵卡,就不要剃光头,否则,会被疑为化疗出院或刑满释放。
当我剃了光头,与二人喝酒,自嘲曰,原来髡不是罚,而是奖,既神清气爽、了无挂碍,又省了洗发水,真正的环保人生。
今年四月,呼市解封,正是春光最好的时候,城市如冰河解冻,活泛起来。某日驱车至旧城某处,有座石桥,桥侧一株丁香树,瘦瘦小小,开着紫白的花。
乍见桥头边有个挑担子的剃头匠,整副行头立在桥墩下,小红圆笼,中置炭炉,嘟嘟煮着一壶水,旁边竖根小旗杆。一秃顶银须老者,竟能施出洗、剃、刮、捏、捶、按、掏的“净发行儿的全套文武行当”,理发毕,如“还债毕”,一老者欣欣然离开,此时,太阳明亮,他的头亦明亮,偶有风过,将地上的头发吹远,然后看不见了,剃头挑子打在桥墩上,咯噔咯噔响,后面还稀稀拉拉排着几个老人,有一句没一句拉着家常。一派古意。
我如痴般观摩了半天,不由为金圣叹先生补 “不亦快哉” 第三十四则如下:春四月,暖阳停天,亦无风,亦无云。大爷持剃刀如云长使青龙偃月,用之快当,顷刻,化繁为简,削发如泥,落之如雪。不亦快哉!
作者简介:乔辉,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察右后旗。大公报,小记者;文不成,武不就;喜诗文书法,皆中途毁弃。曾经执鞭从教,又恐误人子弟;欲以文章报国,无奈才情不逮;遂混迹江湖,诗酒飘零;开公号“交代”,以悼青春。人生十六言:低一点头,喝一点酒,悄悄生活,默默奋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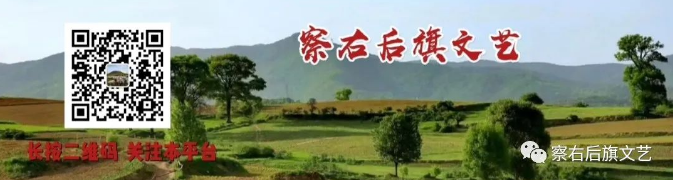
主办:察右后旗文联
作者:乔辉
审核:李立群
编辑:红梅

来源:察右后旗文联
https://mp.weixin.qq.com/s/moDqGVZWNjHW0-Sd56Q09g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



 纯贵坊酒业
纯贵坊酒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