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南山
作者:王英然
东沙河的杏,西沙河的桃,比不过南山的野酸枣。
时隔三十年,终于再次踏上了故乡的土地。出走半生,归来已是鬓染繁霜。梦萦魂牵的南山啊,你还认得出你这个漂泊异乡多年的游子吗?你还记得起那个在你怀里撒欢跳闹的野丫头吗?你是否也和我一样历尽沧桑尽失了旧时的模样?
南山是我心中的神山。关于它的来历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据说三只眼的天神杨二郎是我们桥头镇河庄村人,杨二郎的母亲曾是财主家的长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纺线、织布异常辛苦。杨二郎有了法力后就担起两座大山一路追赶太阳,当大山挡住了太阳的光线,母亲就可以安歇了。杨二郎追呀追、赶呀赶,挥汗如雨,掸尘如山,汗水洒下来就是我们的滹沱河、木刀沟,鞋窝里的土磕下来就是一道道沙土岗,我说的南山呀,就是二郎神担山赶太阳时鞋窝里磕下的土。它在我们村南四、五华里处,自东向西、几列并行、连绵不断、高低起伏,也有人叫它沙土疙瘩。“南山里住着狐仙儿。”这是老人们说的。“再不听话,让狐老仙儿把你架走!”一茬又一茬的娃娃们都听着这句话长大了,也没见哪个被架走过,但那关于狐仙的美丽的传说,却深深的印刻在了我们幼小的心灵上,成为长大后负笈他乡时行囊里的珍藏。狐子窝里装扮的花枝招展的女子怎样咿咿呀呀的唱小戏,有了红白喜事的人家如何到狐仙庙里借桌椅板凳等等,但我最喜欢听的还是那段儿白胡子老头的故事。说,村里有户人家的娃娃淘气闯到了南山的最深处——狐子窝。怎么转也转不出来了,家人找了半夜都快急死了。有位身穿一袭白袍,须发洁白的老头把娃娃送了回来。家人自然是千恩万谢,想报答点儿什么。老者说,“不用了,我们一家老小就住在南山里,只求给我们一块儿栖息地,不打扰就行了。”说完,身形一晃就不见了,不远处一只浑身雪白的狐狸灵巧的跳跃着,消失在了融融的月色里。故事的结论就是:南山的最深处——狐子窝,任何人都不能擅闯,冲撞了狐仙儿是要遭报应的。我曾问奶奶,“你见过狐仙儿吗?”奶奶总是一脸严肃地正告我,“没见过,不等于没有。”十二、三岁时的我和邻家的强子才不信啥报应,我们曾在一个草枯叶落的初冬,偷偷的探营狐子窝,不仅看到了大大小小几十个洞穴,还有幸目睹了狐狸的真容:尖尖的耳朵、尖尖的嘴巴,一身蓬松的棕红色的毛发、一条漂亮的又粗又长的大尾巴,比小人儿书上的好看多了。我们还曾试图偷回一两只小奶狐圈养,结果可想而知,挨了一顿结结实实的好打。
南山是我儿时的乐园。春天,粉嫩的杏花,娇艳的桃花,一团团,一簇簇,零星的散落在银白色的山坡上,如锦似霞;秋天,南山变得五彩斑斓。最美的要数那些野酸枣,一嘟噜、一串串,通红棒硬、滴溜溜圆,挂在酸枣枝子上,像一串串玛瑙珠子。它吃起来很酸,但味道很正,老人们说是安眠的好药,我们就摘回家给奶奶泡水喝;冬天,一场雪把南山变成了晶莹剔透的童话世界,我们捉迷藏打雪仗,一步步爬上山顶再“嗖”地一下子坐着滑下来,虽然常常人仰马翻但依然乐此不疲;最最好玩的还是夏天。夏天的南山被深深浅浅的绿覆盖着,野花肆意的开着,金黄的,淡紫的,深红的、浅粉的,争奇斗艳。南山的最深处---狐子窝,有着齐腰深的青草和一人高的灌木丛,那是狐仙的地界、也是我们的禁地。星期天的晌午,我和小弟装模作样的躺在炕席上,只等着另一头父母屋里的鼾声响起,便拎着鞋子,光着脚丫,偷偷的溜出来,几声猫叫,强子带着妹妹英子、慧慧带着弟弟黑蛋就聚集在了大槐树下的石碾上,我们像出笼的小鸟一样向着南山飞奔。南山草丛中蚂蚱、蛐蛐、蝈蝈、螳螂有的是,我们捉住了用线草把它们串起来,比赛谁捉的多。有时肥肥的野兔会“嗖”的一下子窜出来,转瞬间又隐没在了深深的草丛里,高大的野杏树上扁扁的杏子已泛黄变软,但肉薄核大且酸涩,所以东沙河的杏、西沙河的桃就成了我们的目标。两个园子就在南山脚下,半人高的土墙、一人深的壕沟,对于我们这些没梯子上天的淘气包来说,实在是小儿科。三个小的在墙外候着,我们三个大的翻墙进园,既分工明确又密切合作。通常先由强子在矮墙上窥探,确信看园子的爷爷在窝棚里酣睡才开始行动,慧慧警戒,强子上树,我在树下扯着衣襟接,得手后速战速决、绝不恋战、更不多贪,那又软又甜的水白杏、酸甜可口的串枝红何止是芬芳了我的唇齿,更慰藉了我一生的梦啊。
南山是我心中的隐痛。30年前,我借出差之机回了趟老家,当我迫不及待的奔到南山时,看到的是一幅惨不忍睹的场景:野杏树没了,野桃树没了,酸枣棵子也没了,裸露的沙土疙瘩上被挖出了一个个深坑,两列土岗之间星罗棋布着大大小小十几个小炼油作坊,黑黑的油垢浸染着白白的沙土,散发着刺鼻的恶臭。我儿时的南山呢?我的东沙河呢?我的西沙河呢?我的狐子窝呢?哪里还有一点儿时的影子!只有那高高的烟囱冒着浓黑的烟雾向我哭诉着这里曾发生的一切。我有点后悔不听强子的劝阻了,“那些狐狸,不,狐仙们呢?”“有些被他们捉住剥皮卖钱了,有些跑了。”仿佛有一把锋利地刀子插在我的心脏,我听得见血流下来的声音:“滴答滴答……”我的南山没了,哪里还能安放我浓得化不开的乡愁!
几天前,我刚办完退休手续,就接到了强子的电话,“回来看看吧,咱们的南山比小时侯还好看、好玩。”
“真的?”
“真的。十年前,政府开始了美丽乡村和森林城市建设,取缔了小炼油作坊,关停了东、西河沙河那些污染企业,着力修复南山及周边自然生态环境,我和黑蛋参加了村里的合作社,承包了东、西沙河两个园子,国土自然资源规划局的领导专门请了林果专家来指导,根据这里的土质和气候,东河沙种了桃、杏,西沙河种了葡萄,南山整修后撒上了草籽,零星的种上了些枣树,原来狐子窝那块儿划成了禁区,闲人免进,尽力回复南山生物的多样性。我们南山生态采摘观光园已是第四年开园迎客了。”
“只是,我们的狐仙不可能再回来了”我兴奋之余有些伤感。
“本来想等你回来给你个惊喜的,看你着急也就不卖关子了,咱们的狐仙已经回来了几只了。”
“哇!原来它们也和我一样恋着故土呀.”
行走在故乡的土地上,心里格外的踏实、温暖,每一粒尘沙都给我无比热情的拥抱,每一滴露珠都向我诉说着无尽的思念。儿时的南山再现眼前,它依然向我敞开了无私而宽广的怀抱。
南山,我心中的神山,我儿时的乐园,我,终于回来了。
“你好——南山!我回来了……”
南山:“我也回来了……”
“你是自然之子,而我、我们,是你的孩子……”
南山:“我的孩子……”
“原谅我们的无知和狂妄,对您失去了应有的敬畏和珍惜……”
南山:“原谅……珍惜……”
“从今往后,我们会让你自自然然的生长,你会更加美丽……”
南山:“我会更加美丽……”
我相信我们的南山,你们的南山,我们所有人的南山都会越来越美丽,一直美丽下去。
作者简介:王英然,女,深泽县卫健局干部,河北省散文学会会员,石家庄市作协会员,曾经出版散文集《呵护真情》长篇报告文学《田野放歌》。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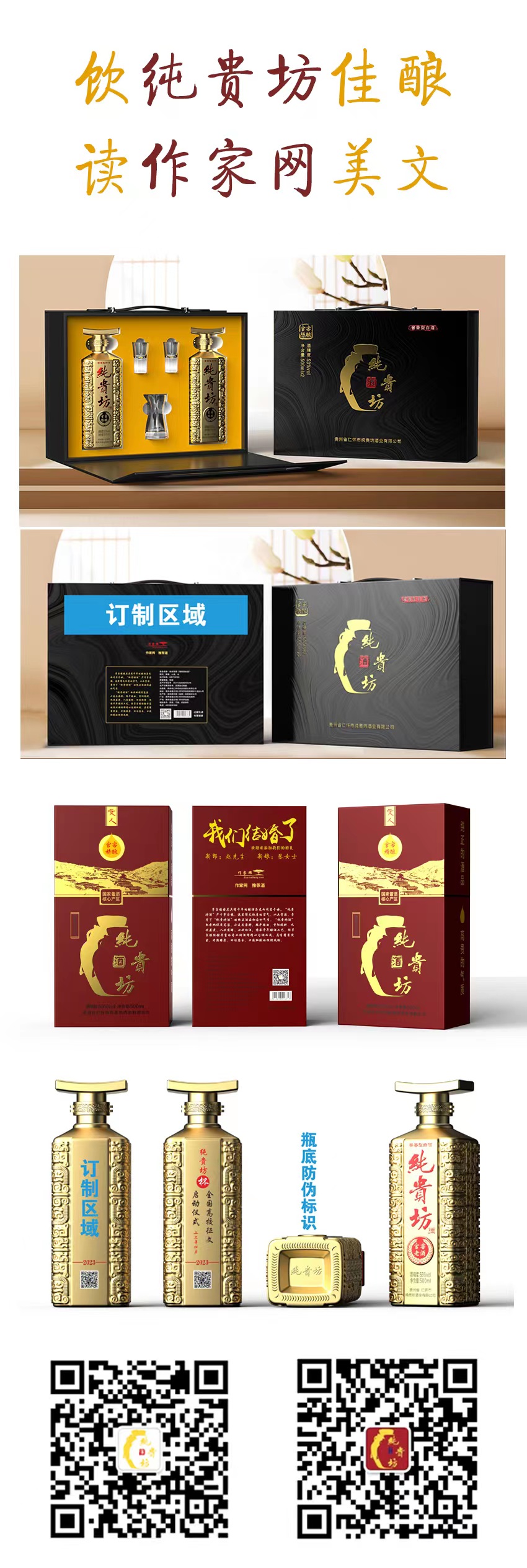


 纯贵坊酒业
纯贵坊酒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