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
作者:宇萍
近来生活的间隙,看到或听到初夏的某个场景或声音,仿佛有着与从前暗自相通的联系,便唤起一些和童年相关的细碎记忆。
读中学时,学校离家很远,俊英带我走小路,能近一点。要蹚过一条小河流,翻一座海拔相对高的山和六七个小山坡,再沿村庄与田畈夹拢的土路步行半个多钟头,才到学校所在的镇子,叫旗下营。学校地狭,我是如何考过去的早已忘却,只记得这是当地较好的学校,学生来自各处,宿舍就那几间,住校生多是高年级要升学的学生,其余诸生要走读。我和俊英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方能按时上课。许多时候我甚至起得更早,星子一颗一颗亮在黑漆漆的天穹,约摸三点钟的样子,我从坑上爬起来,准备草料,饲喂牛羊、马匹、家禽等。那时姥姥已八十余岁,逢上变天或四时变化,入秋入冬,她腿脚常常不好,家里繁重一点的活计需要我做。待忙完,天光像苏醒一般从东天露出来,渐渐有一种隐隐的透蓝。俊英在院外喊“燕子燕子,上学了”,我一边扣外衣的扣子,一边拎起书包跑着应声。
初一下学期,小河里的水刚刚融化,白日显出变长的迹象来。然而空气里寒气还未消尽,姥姥除了腿疾,另犯了哮喘。赤脚医生来医过三次,皆不见好,到了夜里像是病情加深了,一呼一吸非常沉重困难。我担心极了,想要留在家照顾她。她却执意要我去学校读书。如此几日。忽然有一天,她像是病好了一样,呼吸不那么沉重,腿脚也方便不少。我下学归家,听到她大声在说话,屋子里坐着俊英爸爸和同村另一位长辈。刚进房门,姥姥便喊我到外面去玩。我没应,那时正抄一本从同学那里借来的书,原来一道算术题还能这么解,有好多种解法啊!我的心充满着好奇,顾不得去玩,于是搬着凳子到里屋继续抄题解题去了。俊英爸爸走过来,摸着我的头,夸我考试又得了满分,然后关上房门在外间继续与姥姥谈事情了。我只隐约听得“县城”“好人家”“价钱”几个词,并不感兴趣,便继续专注于方程式的结构与算术题的解法了。也是从那日起,姥姥的病渐渐好起来,连腿疾也没有迁延太久,不几日就变回一个可以正常行走坐卧健朗的姥姥了。
那年,我们在村后的山坡种了十余亩田地,是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不用怎么灌溉,玉米、土豆都长得齐整,种下去的种子转眼即长出一拃多高的小苗,使人心喜。姥姥种田、放牧、做家事很在行,几乎从未失手过,我家的面点是村子里小孩子手上最好吃的,端午节的粽子也是包的最好看的,牛羊、马匹也是牧养得最肥美可爱的,甚至连我脚上的鞋子也是小孩子脚上最合脚、最端正的。我跟着她耕田、播种、除草、查看熵情、浇水,然后收割。玉米那么高一棵,掰下成熟的玉米穗,再几日,风把青棵吹得要干了,我们拿上工具到田里将秸秆砍倒,装车,运回家。最初的时候,小孩子的手拿不下锄头,兼力气小,常常她往返一趟了,我才向前走了半趟。而幼时的我较为淘气,又对事物充满着好奇,看到到处飞的蚂蚱蝗虫不免是要分心的,丢下锄头跑去捉;用锄头挖田里的土,挖成一个圆圆的洞的形状,将脚丫放进去。凡此种种。太阳升起来,升到头顶。姥姥却一直在忙,从田尾至田头再至田尾。偶尔直一下腰,拿毛巾擦擦汗,很快就伏下身劳作。她干活快,而这快的秘诀,不过是多忍耐、少直身罢了。只有腰身酸困的实在不能忍受时,才将身子直起来一会儿,和我讲几句闲话,并不嫌我慢,催促进度。因为流了很多汗的缘故,她总是脸色苍白。我看到大滴大滴的汗顺着她的脸颊滴落下去,便使我终究不忍心,赶紧扔掉手中的蚂蚱,学着她的样子做起活来。
农忙之后有个休息日,我赶牛到学校方向的山坡,这个方向地势高且远,放牧的人家总不愿意赶着成群的牛和羊过来吃草,因而草长得便高一些,密一些。我家耕牛往来田地频繁,是实在的苦辛,我便牵它寻一点好的草来吃。牛刚刚吃了几口青草,一辆农用三轮车就“突突突”翻过山岗开过来。被车惊到的牛,慌张间向后退缩,一只蹄子踩到我脚上,又立即把蹄子提起来,直到我走远几步,才重新将蹄子放到草地里。这时车子已停在不远处的大路上,有人喊我名字。是姥姥,她穿着惯常下田穿的那身蓝布衣服,站在车尾向我招手。我跑过去,俊英爸爸从车箱跳下来,扶我坐到了车上,又去帮我牵牛回家。
“我们要去哪里?”我问。
“城里。”姥姥说。
“远吗?”
“不远,就在前面。”
那是我第一次乘坐非人力驱赶的车子。上午的阳光强烈,风从远处高树的树梢吹过来,立刻把乘车人的头发揉成一团。我兴高采烈地站起身,听着盛夏的风声摇涌,风里是熟悉的青草和泥土的气息。天上的云像被扯得丝丝缕缕的棉絮,大朵大朵浮坠在蓝色的空气里。那天的场景,在我的记忆里从此保留下了夏日午后的风和云的色彩,明媚的阳光照得人睁不开眼。我并不知晓姥姥要将十岁的我送走或送去别的什么人家收养。虽然明白或出于自我保护的潜意识,顺理成章地以为如果没有坐上农用车,留在原地继续牧牛,直到太阳把天空的云和所有村庄都染红,再牵着牛回家去。然而,那日在草原小城的黄昏,姥姥带我去餐馆吃了不曾吃过的焙子和炒菜,买了人生第一件花裙子,嘱我站在路口第一棵国槐树下等她,她要去医院取药。我欢喜地抱着裙子,坐在马路边,将她放在我口袋的糖果取出来,那样一点一点撕开糖纸,露出小小一块透明的糖果,用舌尖小心翼翼舔食。糖果的甜是多么甜啊!
太阳一点点斜下去,车辆路过时会有尘土在阳光里高高飞起再落下,旁边有白发的老爷爷摆摊卖杂货,还有灰色的叫不出名字的鸟拍着翅膀飞过国槐树,飞到天空去了。天空被茂密的树叶分割成许多小小的圆点,投在地面上,我怎么数都数不清圆点的数量。我就那样抱着裙子坐在路口,把脚边的碎石子踢来踢去,把所有路过的蚂蚁都数个遍,姥姥还没有回来!路上的车少了,摆摊的爷爷收摊回家了,太阳沉到山的那边,姥姥怎么还不回来?我站起身,望呀望呀。天就黑了,人家的灯亮起来。我不敢挪动,踮起脚尖,望呀望呀。姥姥去了哪里呢?人家的灯又熄灭了,漫长且漆黑的夜开始了,姥姥还是没有回来!我开始害怕起来,漫无心思地坐着,风变得很凉,人语声也渐渐消失,夜向深了,半个月牙挂在天边,我忽然哀从中来,忍不住眼泪涌了出来。听到远方的响动,以为是姥姥回来了,赶紧站起身向马路中间跑去,远处一只流浪的花狗扑过来,一口咬在我的腿上,我却顾不得疼,也不呼喊,望着姥姥离去的方向,担心她回来找不到我。可是她终究没有回来。我一面落泪,一面用手捂着伤口,不舍得睡。星星在天上,一颗一颗闪着光。国槐树的边缘和叶面上集结着水汽,空气变得潮湿而寒冷,马路上有不甚分明的白,或许是月光。
不知过了多久,天亮了。我沿着记忆的路“回家”。行至一处有水的地方,不知谁家的鹅在水波上嘹呖,我用水清洗了脸和伤口,换上花裙子,坡着脚向前走去。草原的风恢复了它平淡无奇的模样,轻轻吹着。而十岁时的那个长夜,我的确有什么东西遗落在风里——大概是找不见回家路的小孩子一整个童年罢,又或者是没有家的小孩子最后的伤心。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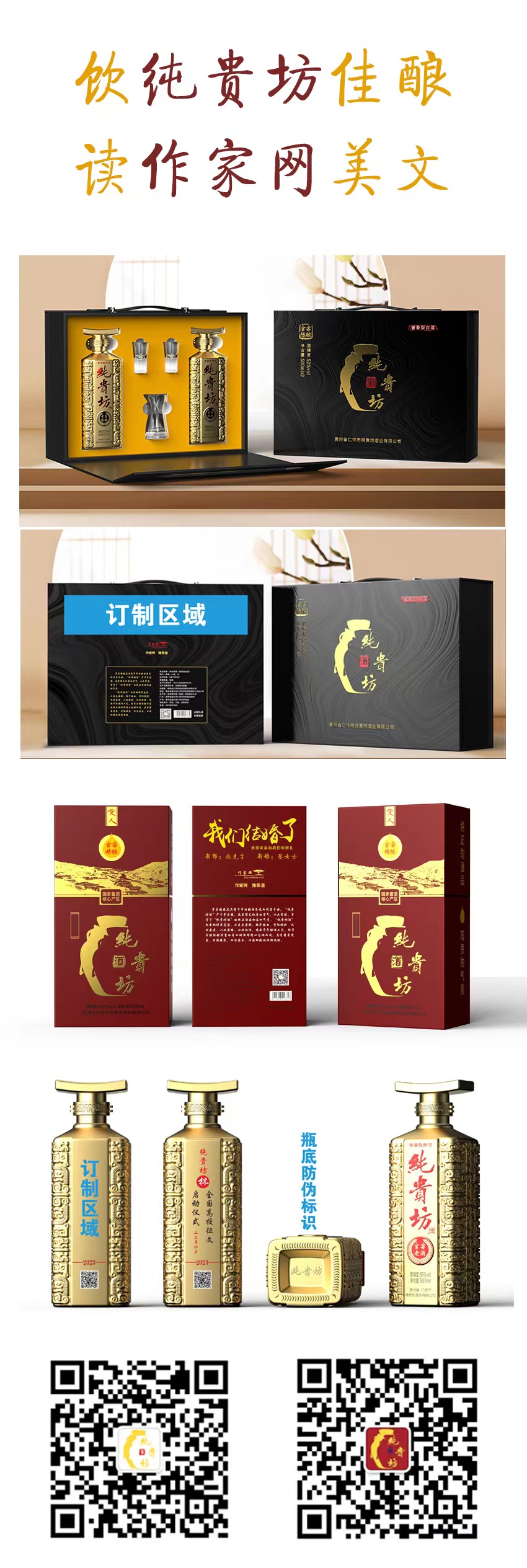


 纯贵坊酒业
纯贵坊酒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