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话剧史
作者:柳邦坤
一个人的话剧史,是一个普通人与话剧结缘的历史。话剧艺术,对我而言,和她是有一段距离的,但在我的人生经历中,又有许多时候,和她有着深深的缘分。
听话剧
话剧,是舞台艺术,需要走进剧场观看,但受条件制约,我年少时更多的是通过听,不能看到肢体语言,只能通过听对白、独白、旁白,来感受话剧的魅力,从这一点来看,话剧也可以称之为语言艺术。
对话剧最初的认知,是从收音机里。也就是我对话剧最初的了解,对话剧这个艺术形式认知,是通过听广播。
小时候还没有电视看,住在大森林里,也几乎与舞台剧无缘。
1970年代初期,家里买了收音机。收音机那时是紧俏物资,是“四大件”之一。说不上要等多久,供销社才进货,一次只进几台,无法正常售卖,担心挤破柜台,供销社就采用抓阄的形式,大人孩子起大早就到供销社门前排队,等到上班供销社开门后,开始抓阄,能抓到自然兴高采烈。说是抓,实际是抢,就是把阄抛起来,让它四散开来,然后大人孩子就连骨碌带爬地争抢。忘记我们家是怎么抢到的,那次总共进了四台,另外两台记得有同学照敏家、茂森大哥家抢到,还有一台记不清是谁家抢到。收音机是上海产的工农兵牌,大大的,外壳是木制的,但做工很精致。抓到阄后,再凭阄进店里购买,然后一家人像是得到个宝贝一样,前呼后拥着,都是由父亲小心翼翼地抱回家,不放心让孩子拿。到家后兴奋地拆封,进行调试。去山里砍伐一根又高又直的落叶松做天线,否则接收不到信号或信号差。
那个时候竟然可以收到好多电台频率,有中央台、东北三省的省台,还有几个当时分属黑龙江、吉林、辽宁的蒙古族盟台,距离虽远,但不知道为何信号特别清晰,如呼伦贝尔、哲里木等人民广播电台。信号最清晰的是苏联台,对华中文广播有莫斯科广播电台和红旗广播电台。后来到广电系统工作,听主管技术的人说,当时我们有采取技术手段进行干扰。但不知为什么,即便有干扰,还是那么清晰,信号极强,收音机稍微开一点音量,声音就特别大。当时都是偷偷听,因为那是敌台,就是在苏联的广播节目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巴金、老舍、曹禺、赵树理、田间等作家、诗人的名字,我上小学不久,这些人都已被打倒,打成黑帮、黑线人物,作品也都被打成毒草,我也就无法看到他们的作品,也别说听过他们的名字了。
那时播放最多的文艺节目是革命现代京剧、革命歌曲、广播剧、电影录音剪辑等,再有就是话剧的实况录音。
最早听到的一部话剧是反映南京长江大桥建设的,忘记话剧的名字了。当时的话剧,时代印记鲜明,会有表现两条路线斗争的内容,人物里会有反革命分子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
“文革”结束后,听到的话剧逐渐多了起来,有“文革”前的作品,如《霓虹灯下的哨兵》,经常播放,听过好多遍。有新排演的话剧,如《丹心谱》《报春花》《救救她》《于无声处》《血,总是热的》《陈毅市长》《姜花开了的时候》等,其中《丹心谱》是北京人艺新时期恢复话剧演出排的第一部作品,是一位酷爱话剧的医务工作者苏叔阳写的剧本,由郑榕、于是之等表演艺术家演出,我听了多遍。《于无声处》是上海业余作者宗福先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于无声处听惊雷”,这部话剧是振聋发聩之作。《陈毅市长》《假如我是真的》是沙叶新的作品。依稀记得《姜花开了的时候》,是表现解放战争的话剧。
北京人艺复出后,那些“文革”前、新中国成立前创作的经典剧目陆续都复排了,有曹禺的《雷雨》《日出》,老舍的《龙须沟》《茶馆》《骆驼祥子》,郭沫若的《屈原》《蔡文姬》,电台都播放了实况录音。播放次数最多是《蔡文姬》,这也是我最喜欢听的话剧,诗人郭沫若创作的话剧台词也如诗一样优美。人艺的那些艺术家的把声音演绎的那般炉火纯青,惟妙惟肖,听了真是享受。当时广播电台是播放演职员名字的,某某角色由某某扮演,因此记住了这些艺术家的名字:郑榕、刁光覃、朱琳、蓝天野、董行佶、于是之、童超、苏民、英若诚……记得《蔡文姬》里的蔡文姬是朱琳扮演,刁光覃扮演曹操,董行佶扮演的是曹丕。刁光覃和朱琳是话剧伉俪,朱琳年少时曾在我后来工作的城市淮安读书学习。导演最初是大名鼎鼎的焦菊隐,“文革”结束后复排是由演员改行做导演的苏民导演(其子濮存昕堪称子承父业)。朱琳、刁光覃等艺术家的声音如同有一股魔力一般吸引我,让我沉醉期间。也是在收音机里听到由董行佶朗诵郭小川的诗歌作品《团泊洼的秋天》《昆仑山的演说》,百听不厌。当时听到董行佶朗诵《昆仑山的演说》,感觉他就是站在昆仑山上朗诵一样,俯瞰八方,心怀宽广,声振寰宇。
说到话剧,北京人艺不能多说两句,以后他们陆续推出《狗儿爷涅槃》《天下第一楼》《小井胡同》《窝头会馆》《玩家》《绝对信号》《北京大爷》《鸟人》等话剧,有的成为经典,经久不衰。现在,还有了中国国家话剧院,因为是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和中央实验话剧院合建而成,也是有历史渊源的,欧阳予倩、廖承志、吴雪、舒强、金山、孙维世等艺术家们为剧院发展奠定了基础,合并前的两个院团和合并后的话剧院,也上演过许多经典剧目,如《抓壮丁》《李双双》《枫叶红了的时候》《离婚了,就别来找我》《生死场》等,排演的国外剧目以苏联的话剧为多。国家话剧院也有名导如《白鹿原》的导演田沁鑫、《恋爱中的犀牛》的导演孟京辉等,许多当红影视演员都出自这里。
国外的话剧听到的少,话剧本来就是来源于西方,考入师范后,听刘淳老师讲《外国文学》,知道了西方的许多经典话剧如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莎翁的三大悲剧、三大喜剧,莫里哀的喜剧等,当然这是后话。广播里听到的最多的国外话剧是《伊索》,也是北京人艺排演的,1970年代末,广播里经常播放,我也就听过许多次,有些对白都记得清清楚楚,如伊索说的“去把大海喝干”,还有他讲的狐狸与葡萄的故事等等。这个剧1959年首演,导演是陈颙,主要演员有吕齐、顾威、苏民、吕恩等著名表演艺术家。1979年复排,我听到的应该是复排的录音。听那精彩绝伦的声音真犹如听觉过年一样,让你无法想象艺术家们是怎么通过声音就把人物的性格刻画的入木三分,让人沉醉。
还听过几部当时名字很有浪漫色彩的话剧,如《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双人浪漫曲》,当时好像有实验性质,觉得耳朵一新,喜欢这种探索,与以往的话剧形式不太一样,比如《双人浪漫曲》,是一部只有两个人表演的话剧。
最初听不惯话剧,特别是“文革”期间的话剧,比如前面提到听的第一部关于南京长江大桥建设的话剧,觉得话剧基本靠喊,吵的特别厉害,听不清个数,乱糟糟的,没有什么审美享受,及至听了北京人艺的话剧后,才真正体会到话剧的艺术魅力。现在想来,喊也正常,那时音响设备差,没有胸麦,不大声喊,下面的观众特别是后排的观众怎么能听清?
不知从什么时候,收音机听的少了,后来就基本不听了,也许是电视的出现与普及带来的冲击。这样,听话剧就成了往事。也不知后来广播电台里,还播不播话剧了。
看话剧
第一次看话剧,是在大森林深处,那是“文革”初期的一个冬天。黑河地区文工团来林区演出话剧《槐树庄》,这部话剧也是“文革”前的创作,但也许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没有被打入冷宫。
也没有像样的剧场,是在条件简陋的职工大食堂里演的,与城里的剧场不可同日而语,也没有大幕、灯光效果,道具也摆不开,可见专业文艺团体下乡演出,是要克服许多困难的。当时年纪小,别的内容没怎么记住,倒是记住了剧中一位叫崔老坤的人物,然后小伙伴把这个名字安在一位高一年级的同学头上,并且一直被叫了很久。
第二次看话剧是1975年或是1976年,当时我正在县林中上高中,林中设置在古驿道其中的一个驿站二站,演出是在三站,当时那里有驻军部队。沈阳军区政治部宣传队(1977年7月撤销宣传队,成立沈阳军区政治部话剧团)下连队慰问演出,当然也演给老百姓,这样就在三站的一处空地搭了简易舞台。学校组织集体去观看,班主任杨小慧老师带我们班,蔡建铮老师带另外一个班级。师生坐两挂马车,赶了三四十里路去观看话剧。
话剧的名字还记忆犹新,叫《苹果树下》,是表现辽沈战役期间,战士们路过苹果园,又饿又渴,但就是没有一个人摘下来吃,表现当时的东北民主联军战士秋毫无犯、模范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故事,诠释当时我们熟知的一段毛泽东主席的话: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可打辽沈战役的时候,我们的战士一个也不吃。
应该是独幕话剧,记得这是一部男人戏,好像没有女性形象。戏里是否有表现军人与百姓的鱼水深情、老百姓送苹果给战士们的情节,忘记了。用两台打开车厢板、衔接到一起的解放牌军用卡车做舞台,舞台高,虽然由部队指战员和当地老百姓组成的观众人数多,但不存在遮挡视线的问题。
看完话剧,我们依旧是坐马车,再赶几十里路返回,到学校已是午夜了。
这是第一次看到较为高水准的话剧演出,不是在剧场里,是在露天观看,因此难以忘怀。
粉碎“四人帮”后,在黑河工人文化宫看过一次话剧,是《报春花》,还是《救救她》?记不太清楚了,是黑河地区文工团排演的,这是第一次在正规的剧场里观看话剧。
再一次看话剧,是在北京。是1990年代初,当时在地委宣传部新闻科工作,一次去京参加新华社《半月谈》杂志举办的通讯员培训班,学习之余的一个晚上,杂志社安排我们一行坐车到了一个剧场看话剧。事先也没有明确告诉我们去哪里,看什么剧目,进去之后才知道,我们来到的是著名的北京人艺剧场,在这里观看我向往已久的北京人艺的精彩演出,让我兴奋莫名。当晚演出的是《李白》,是刚刚推出不久的一部话剧。我在收音机里熟悉的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就这样神奇地出现在我面前,在人艺剧场观看北京人艺艺术家的演出,这对于已习惯了在广播里听他们演出的我来说,简直如同梦里。
从剧场里发的一个宣传折页上得知,《李白》是郭启宏编剧,苏民导演,是北京人艺重点打造的剧目。由濮存昕主演,他饰演李白,剧中演员还有当时尚不出名的陈小艺。濮存昕把李白狂放、浪漫的诗人气质,呈现的淋漓尽致。我是第一次在剧场里,享受了一次高水准视听盛宴。
为了纪念北京人艺建院65周年,话剧《李白》于2017年(适逢中国话剧诞生110周年)4月12日再登首都剧场,依旧是濮存昕主演,主演还有龚丽君,不过苏民导演已于2016年8月28日辞世,父子搭档演绎同一部话剧的佳话已然成为绝响。《李白》首演是1991年,到今年4月14号的演出,已经上演200场,我当年看到的不知是第几场?《李白》成为《雷雨》《蔡文姬》《茶馆》后,北京人艺当之无愧的看家戏。
此后,就再也没有机会走进剧场观看话剧,因我在的小城,地区文工团早已改成市民族歌舞团,以演出歌舞节目为主,不再排演话剧,后来又改成人民艺术剧院。有一年倒是排了一部话剧《北疆哨位》,是表现“黑河好八连”指战员戍边的故事,不过编剧、导演、主演都是外请的,是为了评奖而创作,好像是要冲一冲国家的文华奖,最终也未能如愿。当时我在电视台工作,台里派卢卫国去给录制视频版,制作完成后我看了一遍,但也没有留下深刻印象。
收音机里听不到话剧了,但随着电视的登堂入室,通过电视,观看话剧成为必然,在电视上看过《茶馆》《雷雨》《日出》《万水千山》《霓虹灯下的哨兵》等话剧。不过,现在电视上也看不到播放话剧了。
时隔多年,这年的4月,再度走进剧场,是刚刚落成不久的大剧院,看了开心麻花剧团演出的舞台剧《李茶的姑妈》,属于喜剧或滑稽剧,宣传推介说它是爆笑喜剧。舞台剧和话剧应该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吧,不然它为什么不叫话剧?我理解话剧是以对话为主,舞台剧侧重表演,除了对话,还可以歌、可以舞。不管怎么说,这是继话剧《李白》之后,我第一次到剧场看剧,一转眼二十五六年了。次年,又看了开心麻花剧团演出的舞台剧《羞羞的铁拳》。我所在的运河城市的大剧院,堪称高大上,归属北京保利剧院旗下,经常会有音乐会、歌剧、话剧、戏剧等高雅艺术演出,这是送到家门口的艺术演出,有机会还真得多进剧院,多看看话剧。
演话剧
曾经演过两次话剧,都是做主演。
排节目次数已经无法说清,那时各单位都有文艺宣传队,从小学到中学再到高中毕业参加工作最初的几年,也是文艺宣传队的一员,演过无数次节目,节目多是表演唱、三句半、对口词、山东柳琴、天津快板、小合唱、大合唱等形式,排练和参演话剧的机会较少。
第一次是在童年时代,林区排演一个控诉旧社会的小话剧,我上小学二三年级,被安排扮演话剧小主人公。同学刘志坚的父亲刘锡坤是副书记,他在抗美援朝时,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一个师演出队的队员,他扮演我父亲,我演的是一个叫占魁的穷苦孩子。当时正搞“不忘阶级苦”活动,记得一位叫×占魁(姓什么忘记了,山东、河北哪个省人也忘记了,记得是关内北方的一个省份)的人,在报上发表了他童年受苦受难经历的文章,也被编入学习材料里,我们都学过,故事感人,看了让人无比痛恨万恶的旧社会。林区里的文化人把这一真人真事改编成小话剧,同学志坚的父亲是林区主管宣传方面工作的领导,自然是组织者,加上他在志愿军做过文艺工作,是内行,负责话剧排练,用今天的话来说他应该也是导演。依稀记得他指导还不到10岁的我,怎么来演好小占魁。话剧的具体情节都记不大清楚了,但第一次登台演话剧而且还是个悲剧,还是有一些印象的。
第二次演话剧,是上九年级(即高中二年级,当时是九年一贯制)时,剧名是《抗寒的种子》,表现江南一带的一所农业院校培育良种的故事,是紧跟当时形势之作,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提倡开门办学,剧中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我扮演主人公,是按照当时的“三突出”创作原则塑造的一位“反潮流”的大学生。导演是才华横溢的吴守垣老师,他当时教我们物理和化学,也是一个文艺青年。酷爱摄影的他还拍了剧照,多年以后在一位女同学那里见到过,把我拍的又高又大,大家众星捧月一样把我围在中间,我在那里慷慨陈词。只是遗憾,又过了几年,再去找这张照片,想要来留存,结果照片已经丢了,不由得扼腕长叹,再后来问询吴老师和其他参演话剧的同学,都没有找到这张照片。一个少年时代参加话剧实践的历史瞬间的凭据找寻不到了,有点小遗憾。
《抗寒的种子》的话剧剧本,发表在当时出版的一本硕果仅存的文学杂志《朝霞》上,杂志主办地是上海。学校订了《朝霞》,老师们就是在其中一期杂志上看到这个剧本,就下决心排练出来,那时我对话剧表演,可谓一窍不通。
以后粉碎“四人帮”,话剧舞台异彩纷呈,文艺宣传队成为过去时,我就再也没有登台演过话剧。
前些年,黑龙江的话剧在全国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不少作品还在全国获奖,有《地质师》《半江瑟瑟半江红》《淘金大船》《风刮卜奎》等。其中大庆的杨利民编剧的话剧作品获奖最多,《淘金大船》是从黑河考入省艺校编剧班的上海知青梁国伟编剧的。哈尔滨话剧院还是很有实力的,排了很多大型中外话剧,还出了杜雨露、程昱、彭玉等后来在全国有影响的话剧表演艺术家,不过后来他们都转行拍影视剧了。
有一年,哈尔滨话剧院排演索福克勒斯的戏《安提戈涅》,从中央戏剧学院请来了罗锦麟老师来给导演,他是坐火车由京去哈,我恰巧与他在一个卧铺车厢,而且是对面铺,从上车到车厢熄灯,与他聊了很久,获益匪浅,他也对我颇多褒奖,我还跟他提出考他们学校读研的请求,当然一面之缘,不免唐突。第二天清晨到哈尔滨车站后,他被哈尔滨话剧院的人接走了。到哈是来导演《安提戈涅》,也是随后在《黑龙江日报》看到该话剧的演出广告才知晓的。后来再一次去北京,到中央民族大学看我的同学张林刚,晚间在他家小聚。那时他家住筒子楼,邻里相处和谐,同学请来邻居一起喝酒,邻居女主人与我同学夫妇是同事,邻居女主人的夫君刘伟老师在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任教,教学之余也导演过电视剧、话剧等,记得他告诉我他导演的作品有《单家桥的闲言碎语》。席间我跟他说起此前在火车上与罗锦麟老师的邂逅,他告诉我罗老师是他们系主任,罗主任的父亲是莎士比亚翻译大家罗念生先生。那时没有百度,对人的了解渠道少。原来如此,我在火车上巧遇的是名门之后,中戏重要系的领导。罗锦麟本身也是戏剧导演艺术家,戏剧泰斗,特别擅长导演古希腊戏剧,被誉为“希腊文化大使”,当然,这些荣誉头衔是近些年才了解到的。
这一次邂逅,也是我萌生专业去从事话剧之梦想的由头,当然由于种种原因,最后没有痛下决心奔话剧而去。
话剧,虽没有改变我的人生,但通过听话剧,使我感受到了话剧独特的魅力,给我带来许多艺术的启蒙。话剧,可以说给我的人生提亮了色彩。
我恍然走进剧场里,观赏话剧《人生》或《平凡的世界》,坐在座位上,静静地等待着开演。
大幕徐徐展开……
(本文选自作者的散文集《分界》)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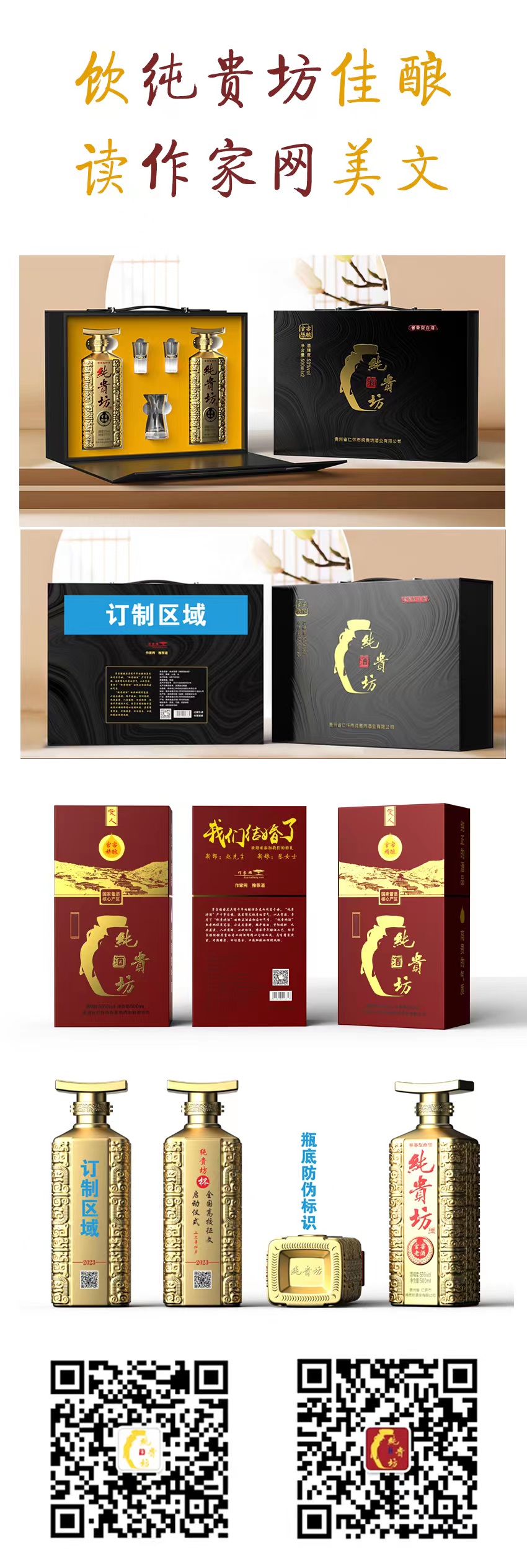


 纯贵坊酒业
纯贵坊酒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