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芷叶集》
江少英
摘要:作为福清的本土作家,念琪的自选文集《芷叶集》探索的是关于“福清元素”的话题。文章对文集中现实的地理空间的建构、想象的地理空间的建构、超越的地理空间的建构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在当前区域文化研究兴起的背景下,《芷叶集》对福清地域文化的建构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值得借鉴和弘扬。
关键词:《芷叶集》,念琪,福清元素,建构
《芷叶集》是福清作家念琪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一部自选文集,包含小说、诗歌、散文随笔、电影评论等四个部分。该书由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题名(包括作家苏童、格非也都题写了书名),并得到文艺理论批评家童庆炳先生的好评。
“芷”是《离骚》中的香草名之一,用外在的香草比喻内在美好的品德与执著追求的理想。看来,这是念琪先生很喜欢的一种植物,其千金的小名就叫做“叶子”,谐音倒过来刚好是“芷叶”(或是暗含“子夜”之意),即是香花美草之叶,这是很有意思的。而文集中大量的插图亦是由在中国美院就读的“叶子”的写生之作,图与文并茂、画与词同步,增添了文集古朴的厚度。
文学地理学的批评方法是近年来学界评论文学作品的一种新兴方法,是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交叉学科。这和念琪先生在其《芷叶集》中所探索的关于“福清元素”的问题是不谋而合的,评论者与创作者的不约而同,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当然,也与中国当代文学中关于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探讨是相契合的,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苏童的枫杨树系列、贾平凹商州系列、格非的江南系列……
故乡是作家创作的重要原型地,作家生活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是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念琪是位挚爱家乡的作家,其作品主要是对福清空间文化的呈现,“福清元素”是其诗意灵魂的栖息之地。
首先,现实的地理空间的建构:包括风物、人、习俗等。丹纳认为,“作品与环境必然完全相符”, ①指的是作家所描绘的事物一定是他所熟知的,只有这样才是自然与社会的映照,这样表现出来的才是充溢着积极健康的人性与生命力的艺术。福清沙埔是念琪的成长之地,这里是他开启人生转折点的重要港湾,这里有他挥洒汗水付出艰辛劳动工作卓有成效的美好的回忆,《福清沙埔印象》之一中用“花生”、“海带”、“目屿岛”等沙埔镇特色的地理风物,展示在这海天尽头难得尘静的港湾;之二中用“沙滩”、“飞燕狂风”、“野菊花”、“高山羊”等显示了在台风来临时大自然的力量;之三中富有海洋特点的“赤礁”、“紫菜”、“海蛎”、“蛤苗”、“鲍鱼和海参”等地理文书彰显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耕海牧鱼”的愉悦心情。作家用独到的视角饱含深情的语言抒写了“沙埔”之歌,表现了人与大自然互为一体的谐和,物是一道道观赏的风景,而人亦成为大自然的一道美丽风景线。亦如童庆炳先生在《芷叶集》的序中所说的,“他(念琪)写得很真,很自然,无矫揉造作之态,但篇篇都灌注诗情画意……”
《超越梦想》中表现了作为一个福清人的骄傲,因为这里有福建的“小台湾村”——洪宽工业村,福清还有全世界最大的显示器生产基地之一——冠捷电子,有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生产商之一——福耀玻璃,此外还有江阴新港、核电厂、风电厂等。除了这些现代的文明之外,福清还有悠久的文化,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有唐代的“天宝陂”、有宋代的 “龙江桥”、有元朝的 “弥勒佛”、有明代的“瑞云塔”、有清朝的“东关寨”、有东渡创立日本三大佛教宗派之一黄檗宗的“隐元禅师”……福清的华侨遍布全世界115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共同构成了“福清哥”的地理空间元素。对福清这一片土地及土地上生活的民众保持着敬佩,也只有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作家才会感到充实与幸福。
因而,《芷叶集》更多的是展示了生活在福清这一区域空间中“人”的状态。《一个老人的教育》中的印尼第二代华侨何文金先生情系桑梓,兴办教育,不仅在东张镇办了华石小学和幼儿园,而且在印尼也兴办了一所有幼儿园小学中学的学校,其办学校之热诚、考虑问题之细致、对家乡文化之热爱皆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悼吴兴》中表达了对福清敬爱的文化工作者吴兴的深情悼念。文中对吴老的创作以及文化工作(特别是积极推动福清电影评论的发展)进行了总结,让人忆起“肝胆豪爽,廉洁奉公,清贫乐道,甘为人梯”的良师益友——吴老。吴老可以说是笔者认识的第一位福清的文化人,其曾热情邀请大家共同去攀登龙山公园,然后齐聚一堂行酒令,吴老的豪情壮志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吴老的音容笑貌,一举手一投足,宛若就在昨天……《山前姐夫》表达了对勤快、慈爱的大姐的感人记忆。《一起做慈善》中通过带着孩子等全家人去南岭做慈善的经历,让接济者与受济者共同感受到人间处处有真情,亦可见作者的正直与高洁,令人感佩。
还有对习俗的描述,《石竹解梦》是对“春情荡漾”之石竹湖、“静默地守候”之鲤鱼岛、道教祈梦解梦的诗意呈现。而《石竹仙道》以随笔的形式描述了印尼华侨蔡云辉拜山祈梦、“我”读中学年幼无知玩签的故事,从而道出石竹梦文化习俗之“道无道而非人之道”的思想意蕴。《初二的困扰》中亦是对福清正月初二不能拜年的传统习俗文化的思考。
其次,想象的地理空间的建构,这是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徘徊的作家内在的地理空间。对熟悉事物的呈现即可以是田园风情现实状态的,也可以是内心的隐匿与精神的需求。作家善于观察生活的环境状况,抓住事物的特征,运用夸张的本能与思维的活力把其反映在作品中,他所描绘的物体被赋予了精神上的特殊内涵。
其诗作《一个人的寂寞》中运用“海浪”、“台风”、“秋叶”、“秋阳”、“麻雀”、“阳台”等富有福清元素的意象传达出“我”的精神特质想要远离城市的喧嚣,思维始游走于乡下,想象着到那享受着 “一个人的寂寞”:生活状态若是可以与树同呼吸,可以与鸟共命运,这是多么幸福的事呀,作者在尽情歌唱着生命的咏叹调……可是理想很美满现实很无奈,最后一节作者笔锋一转,黄昏时节“我”依旧蜗居于城市的“阳台”之中,诗歌的艺术张力自然得以形成。2012年的5月5日,作者对其诗歌创作进行了一个凝练的概括,在《季节的诗歌》中多处用了拟人、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用丰厚的想象力,对虚构中的“那一年”的“诗歌”从正月、腊月、春天、夏天、秋天、冬天来到“我”的身边进行时间上的“丈量”,把握住了“诗歌”创作的特性。正月由于受到诗歌“抚摸”的关爱喜欢上了诗歌并逐渐形成腊月诗歌“昂首挺胸”的稳健;而春天的诗歌是羞涩的,“追逐着风翻掀诗人的裙子/偷窥属于我的春光”;夏天的诗歌是热情万分的,各派纷呈比武论剑,“各种流派蜂拥而至/华山论剑/光明顶滋事”;秋天的诗歌是幸福的聚会,“在仲秋之夜吟哦人间团圆”,嫦娥和吴刚“赶赴青春诗会”;冬天的诗歌是捡拾“丝绸之路”的历史,追寻着海子的足迹。
《山居的脚步》在虚像与实体间游离,于午后阳光照耀下的草地上仿佛看见“童话中的人鱼小姐蹒跚地走来/她用哑语表达着对王子的爱”,可是“倏忽又化为泡影消失”了。小说《五叔阿来》通过一个讨海为生的瘸子五叔阿来艰难困苦依然故我坚持维持生计抚养痴儿的想象的故事,展示了生活在海边的人顽强生存的意志力,情节曲折感人肺腑。《窗外》清新温和,表现了对逝去的美好清纯事物的找寻。《休宁论道》用“水墨沾湿”、“烟雨柳巷”等词句表现了对充溢着“绿水”与“负离子”的如梦如幻的古蕴江南水乡生活的向往。
作品的创作就是在不断地用丰沛的想象与虔诚谦逊的态度来阅读自我,因而懂得文学的人生命必定精彩,懂得文学的人内心也必定强大。考察这方心灵空间的栖居之地,建构文学与地理之间的框架,丰富作品的共时性,深化了解作家的主体,从而架构作品与地理空间之间的审美关系。
最后,超越的地理空间的建构,包括对文化、时间、哲学的思索。当然,作品除了表现日常的生活状态、活力四射的梦想之外,还包括充满玄妙的哲理意味的思考,作家王小波在其杂文中曾表述过: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写给端午节》诗人在品尝着“粽子”,抓到了文化的原点,抓住生活的“片片化石”往历史回溯,希望人们记住中华的文化根源是从中原文化而来的。而同样是2012年写的关于端午节的诗作《端午,端午》中却是别样的风采,展示的是一个异化了的端午。这是一个“血腥和龉龊”,“阴暗、潮湿、发霉”充斥着的端午,在这样的端午,“大地发霉、空气发霉、天空发霉/衣服发霉了,头发发霉了,内脏发霉了”,踉踉跄跄的屈原无以为生。诗作表现了对现代异化生活的不满,诗人想要超越于当下的状态。
《醒》全诗共三节,展示了诗人对时间的思索,对生命哲学的探求。第一节用“碾过”、“流过”说明了时间消逝之快;第二节用“克隆”了的“我”和“以后的日子”表现了人生之虚无缥缈;第三节“我顺着时间而走/就是逆着时间而行”,有哲学的意味,忙忙碌碌的众生顺着自己的生命轨迹往前行走的路途,从时间的角度来考量,实际上亦是时间表的倒计时。在这生生不息的宇宙洪流之中,时间在飞速往前,大浪淘沙,如何成为一粒粒灵动的沙子,放射出智慧与思想的光芒指引着人类心灵的航标,这是诗作探求的问题。
《福清武术》对福清南少林、詠春拳、宗鹤拳等福清武术文化进行了弘扬,《让艺术离我们更近些(序)》弘扬了福清的美术,《文明赶考,在路上——与石智勇的邂逅》对福清创建全省文明城市的路上邂逅了石智勇,表达了争做城市文明主人的渴望心情。《寻访外婆的澎湖湾》、《日月潭水深几许?》《台湾行之“金门记忆”》等是对两岸文化的思索。
现代法国思想大师列斐伏尔的名言是:“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往往蕴涵着某种意义。”②列斐伏尔将空间作为社会存在的本体,而文学中的空间描写是具有审美特性的。对于福清地域性“地理空间”的描述,构建“福清元素”是作家念琪“精神”之所在地,这是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元素。当然,也正是区域内的这种独特的自然与人文形成了念琪先生特殊气质的元素,构成其文学创作的原点。
对于地理空间的认识,对于所经历的自然与社会的观察与表达,能够改变作家的观念与视界,并且往往体现于其作品之中。《芷叶集》对福清地域文化的建构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在当前区域文化兴起的背景下,值得福清作家借鉴和弘扬。福清历史悠久,开拓多元而包容,这方土地上的文化值得有志之士共同去耕耘,我们期望更多的作家共同来探讨富有福清特色的文化元素。
在这科技信息为潮功利主义思想越来越盛行而精神生活越来越萎顿,“狄更斯已死”,灵魂缺乏重量的年代里,念琪先生通过他的《芷叶集》告诉人们说,放慢你的脚步,等一等你那被落下的灵魂吧!
参考文献:
①丹纳.艺术哲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71
②转引自刘怀玉.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解释:以列斐伏尔为个案[J]河北学刊2005(3): 116
③念琪.芷叶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
④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⑤刘小新.引言:文艺学的空间转向[J]学术评论,2012 (6): 4-6
⑥刘小新.文学地理学:从决定论到批判的地域主义[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0): 115-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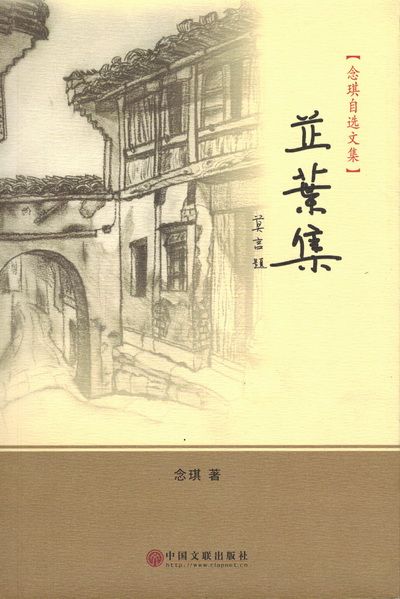


 纯贵坊酒业
纯贵坊酒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