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眼里出情人
——读莫沫的小说《理想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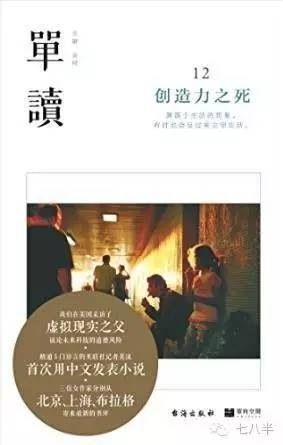
读莫沫的小说《理想情人》和读当代中国很多年轻写作者尤其是女性作者的作品一样,首先想到的还是经验化的问题。虽然莫沫本人在小说中试图以叙述者的口吻不无调侃的自我解构道,“我坐在电脑前,突然觉得写的这些越来越像报告文学,越发像那个讨厌的‘非虚构’。或许是因为写作总是一个暴露自己的痛苦过程,大声描写脑子里装的东西,不能耽于幻想,总想接触实际。”但小说文本自身还是让人不由得会把其内容与作者本人的经历联系起来。比如,同样是以一个外籍人士的身份自小生活在北京,比如游学美国然后又以某外媒记者的身份回到北京工作等等,这些小说中人物的生命轨迹都与作者本人的生活履历相似度极高。
所以,不管作者本人愿不愿意,都很难避免读者会将其与小说主人公画上等号。那么,这里问题的关键倒不是可否如此去画等号,而是经验化写作本身的合法性问题。
大概是从玛格丽特·杜拉斯开始,一般女性写作很容易会陷入一种自传式的眺望和追忆,正如《理想情人》这个篇名所昭示的其与杜拉斯的《情人》之间的遥相呼应。杜拉斯的成就已然举世公认,其在文体的开创和透视生命的深广上都引领着后来者竞相模仿,其间当然有成有败,具体到莫沫这篇《理想情人》来看,我认为当属前者。
首先因为足够独特。写作中的经验传达最忌讳的就是雷同,这种同质化导致的千人一面自然很难具有发现的意义。以一个外籍女孩的视角来看一个外籍女孩与一个中国男人的情感纠葛,这样的故事本身在汉语写作中当然具有某种天然的奇观化效果,很容易对汉语语境中的读者构成某种新异感,或者说猎奇也不为过。因为我们虽然看过不少以中国人的视角来描写这样一种异国恋情的故事,但是翻转过来的视角却并不是十分常见,从而在经验的陌生化上,让作品具备了更多被期待的看点。毋庸讳言,这是莫沫进行中文写作的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更何况,这种异域文化视点带来的还不仅止于异国恋的想像和替代性满足,而是还有更多的北京友谊宾馆里那些外国专家楼生活的揭秘性质,比如每天晚上和中国老百姓一样守在电视机旁收看新闻联播的老外,还有那些平反的老外,诸如此类,大概都是我们之前无法想象的一种因其疏离而造成喜感的陌生经验吧。
另一方面,如果说跨国恋情在杜拉斯那里只是一个叙事外壳或线索,那么在《理想情人》中也同样如是。“情人”只是一种泛指和象征,其隐喻的对象则牵连众多,至少在莫沫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对国家,或者对国与家的某种指称。
正如莫沫在小说中写道的,“时常有人问我北京是不是我的第二个家,这个问题我回答不出来,因为离开秘鲁之后就没有任何地方能唤起类似的联想。不要说第二个家,就连第一个家,也没有。”“就在那些年,我把北京的事情抛到了九霄云外。纽约意外地带给了我某种新鲜而无法完全理解和承受的自由感。有时在全城走了一天之后,我坐在楼顶上,看着傍晚变红的天际和那些密密麻麻的高楼,觉得生活好像就是一系列意外事故,犹如一段可以随时变化的即兴爵士乐,没有秩序。但爵士乐也有一个周而复始的原调,换算在生活中,或许就是‘家’吧?”
这些文字让我们看到一个自认“总觉得自己漂浮在现实的水面上”的漂泊者对自我身份的某种模糊、质疑和确认。作为一个自幼漂泊异乡的“老外”,《理想情人》的倾诉容易给人一种“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般的无助感。这种无助不仅源于身体的迁徙,同时更多还是文化上的隔膜,或者干脆就是语言上的失语。
“……让我用任何文字写作文我都会觉得恐惧。写出来的东西像小孩子写的,看别的学生的作业,觉得他们的西班牙语比我强一百倍。我好像没有语言上的母亲。”这种非母语环境中的寄人篱感,恐怕是作者最为沉重的一种痛感和负担吧?正如莫沫本人呈现给我们的,她可以用如此地道的中文写作,但是当用口语交谈的时候,还是能够感受到某种力不从心,这里面含有某种永恒的悲剧,几近一种无家可归的宿命。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秘鲁、北京、纽约虽然都可谓不是她的国,但却有可能是她的家。因为与国的外在界定不同,家更多的是一种主观认知,是一种情感和文化认同。有情才有家,所以家即情人,那么在众多的情人中,必然有一个是最理想的,而这个理想情人就是中国,这是我理解的莫沫小说中的“企鹅”情人所能引申出来的家国同构关系。
“‘因为你有翅膀,不会飞,你像条鱼,但害怕深水。’企鹅,我的水陆两栖动物,我想念你。”这就是小说中主人公对理想情人的理解。这个理解里有无限的深情,但同时也充满着无奈和怜悯,当然还有一种源于误解和一厢情愿的不自知,仿若少女般的一往情深和沾沾自喜,虚妄而动人。
作者:刘兵
来源:七八半


 纯贵坊酒业
纯贵坊酒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