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肯谈李浩:他开始向上,让身体有了信仰、天空

宁肯(作家,十月杂志常务副主编,本文为其在李浩诗集《还乡》发布会上的发言)
李浩诗集《还乡》出版,这个对李浩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始,一个诗人能够结集出版一本诗是个标志性的事件。这里应特别感谢我们的出版社,诗集的出版不是一个赚钱的生意,出版社着眼于诗歌和诗人,着眼于这种在当下非常重要的才华,表现他们一种自己的职守,值得尊敬。
诗集出版之前,他就把部分的诗歌给我看了,对于李浩这样一个80后的诗人,我觉得他的特点还是非常的突出的,我读他的诗歌里面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是他打开了自己的身体,这个身体在李浩的诗歌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身体写作前些年并不陌生,我们知道诗歌有一个流派叫做下半身写作,也是强调了身体,那个身体我觉得代表那个时代的特点。身体写作经过这么多年发展沉寂之后,由李浩重新强调起来以后,显示了一个非常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在于李浩更多强调的身体是上半身,不是下半身的写作,下半身走向不是朝精神方面走,是朝着生活中的非常边缘的方向走,甚至是一个惊世骇俗的、非常震惊的方向,到了李浩的身体写作,则有了另一种精神的表现,他摆脱了90年代以来形而下的一种趋向,他开始向上,让身体有了信仰、天空。
我们知道下半身写作,当初经常攻击诗歌写作的一点是,诗人人们只强调精神、理想、心灵、灵魂,他们正相反,现在李浩回过头来再次相反,再次强调灵魂,这个时候李浩强调灵魂和过去下半身诗歌写作攻击的灵魂已经不同了,我觉得是一个否定之否定,有一些事情在你否定了之后再去肯定才能显示出价值,我觉得李浩重新肯定了身体写作,或者身体和精神方面的写作,这个是李浩诗歌的特点,也是一个他的意义。我没有想到这么一个写作由他这么一个年轻的青春的身体来完成这样一个形而上的身体写作,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读李浩的诗,感觉李浩的由诗歌构成的身体感觉像一个乐器一样,这个身体好像布满了笛子的孔,每个孔都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在他的不到10首诗里面用了和身体有关的词语,我罗列了一下,就有这些:肥胖、身体、灵魂、脑子、手、衣袖、嘴唇、喉咙、心,甚至包括智齿都写进了诗歌里,还有耳朵、头顶、头颅、眨眼、鼻孔、心肠、胸口、下跪、叩头、脑门等等。我们不但可以听到李浩演奏的声音,甚至我们还能看到他诗歌内部的构成,他如何敲打词语,就像我们听到钢琴一样,我不但看到他的手指在演奏,我们还看到琴盖后面的木捶在敲击,就是他的身体整从里到外都是个开非常好的打开的状态,那么这个状态又是而上的打开和发挥,某种意义上讲,实际上李浩还是受到了整个身体写作的影响,只是他的导向、朝向是往上的,这个是李浩诗歌非常重要的方面,所以我觉得上天创造了李浩身体性的音乐,这音乐性的身体来为我们演奏生活、演奏灵魂,这方面我觉得是李浩的词语非常大的有特点,是李浩诗歌的一个标志。
另外,李浩的另一个特点,他这么年轻,他有一种信仰,这个信仰涉及到了宗教。我们过去的诗歌里面一些诗人也会经常涉及到一些宗教的词汇,但是没有像李浩这么坚定,这么扎实,这么诚恳。宗教、信仰和他的身体,和他身体打开的状态结合在一起,是李浩特别明显的一个特征。按理说,一般来讲宗教和信仰是排斥身体的,甚至身体和精神和宗教是一个矛盾,是一个对立,是一个冲突,过去我们表达这方面的冲突比较多,而李浩的诗歌使这些是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他的那种和谐、洞穿,他的浑然一体,你可以感觉到他就在他的教堂里面一样,在演奏自己的圣歌。
再有,还让我惊异的是,李浩这样一个敏感的身体和灵魂,他不仅仅关注自己的内心,他偶尔也关注身体之外的事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李浩诗中有一个写北京的场景,写鼓楼的那首诗,那首诗描述生活场景,都市、时尚的拼接,信手拈来,类似于摇滚性的结构感,场景让扑面而来。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李浩这样一个灵敏的身体有时候就应该放在那些喧嚣的都市,让他去感受,去反映,去演奏,反而对喧嚣更有一种特别的把握。什么东西对岩石的感觉最强烈?我觉得应该是蜗牛,最软的对最硬的感觉最强烈,蜗牛当没有人的时候,当它的身体出来的时候,它在贴着路走的时候,对外界的敏感性是最强的。所以我觉得像李浩这样极其柔软敏感的身体当他写北京鼓楼都市那种喧嚣的时候,可以感觉到他的灵敏度已经达到了蜗牛的那种触感,反映出来的都市特别有特色。所以我认为李浩除了他的敏感,我觉得他的敏感可以继续表达他身体之外的世界,通过他的己有特点的来感知外部的世界,因此我看到李浩不仅仅是一个灵魂的诗人,一个身体向天空打开的诗人,他还是一个可以关照都市、可以关照大千世界的诗人,而他会给这样的世界带来了他的身体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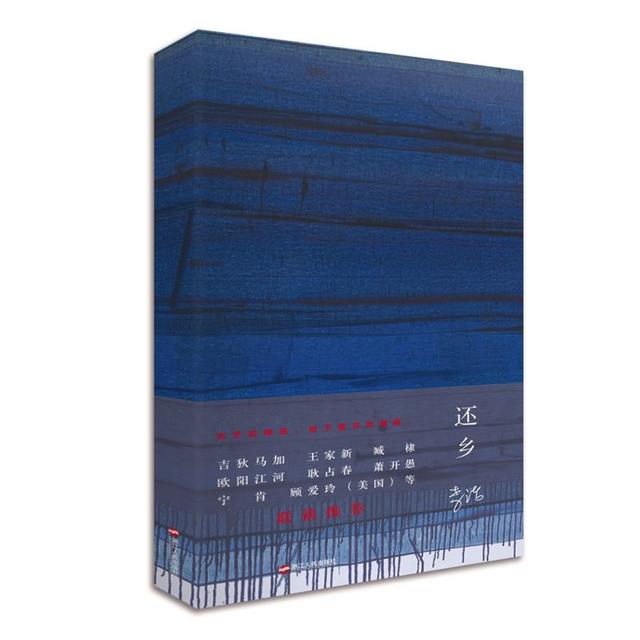
《还乡》,李浩 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魏冰心 PN070
作者:宁肯
来源:凤凰读书
https://share.iclient.ifeng.com/shareNews?forward=1&aid=cmpp_060220000078681#backhead


 纯贵坊酒业
纯贵坊酒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