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瑟瑟:为炊烟袅袅的大地守灵
作者:林忠成
海德格尔认为“诗人的天职乃还乡”,随着现代化的演进,推土机的霸权话语深刻改变了乡村面貌,那些坚硬的钢铁试图驯化当代人的精神,把故乡从当代人记忆中抹煞,让人类被技术主义驱逐出家园。很明显,这个精神上背井离乡的趋势有越来越强烈的势头,在第一故乡上帝灭失、第二故乡人性消亡后,当代人第三次被驱逐出故乡,物理学的故乡,发生学上的那个故乡,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轰鸣的推土机前面,人们哀叹——那个“小桥、流水、人家”“屋中春鸠鸣,树边杏花白”的故乡再也回不去了。卢梭对文明进化非常怀疑,他觉得“历史进步同时也就是退步的过程,技术和科学的进步必然伴随人类关系的退步”。在乡村分崩离析的现实语境下,基于故土的本土性写作便成了一种招魂、守灵式的努力,为渐行渐远的田野牧歌、为炊烟袅袅的大地送最后一程。
周瑟瑟便是这人迹罕至的招魂者之一。近年,他的诗歌写作大规模地转向胞衣地、故园,从2010年左右开始,故园在他的诗歌题材中的比重越来越大,至2016年2017年这两年,已经占到全部题材的80%以上。他的精神本土性诗歌,一种是历史语境再现式的,一种是地方性嵌入式的,还有一种是吊亲思情抒怀式的,以及山川物候拟像式的。此外,还有少量的是本土故人摹传式的。
再现历史语境 重温慷慨任气
周瑟瑟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在湘北南洞庭湖流域的湘阴县柳庄、栗山长大。他的部分故土诗歌再现了那个特定年代历史语境,兑入童真记忆,在两个维度上展开。这两个维度互相渗透,形成互文关系。比如《潭水脚里》《栏家龙》《斗地主》《肩扛粪勺》《打游击》《梦见郎猪》等。《打游击》一诗写道“我的哥哥高大,嘴上长了一小圈绒毛/好像他获得了父亲的授权,领着我们去打游击”,相信50年代至70年代出生的看了这首诗能唤醒潜藏很久的“集体无意识”。他们的童年时代,“打游击”是男孩子最主要的娱乐与游戏之一。那个时代,占据荧屏的大部分电影都是革命战争题材的,如《铁道游击队》《地道战》《平原游击队》等,连环画也以革命战争题材为主,农村孩子黑天野地地模仿那些八路军、游击队,折木为枪,捡土坷垃为手榴弹,用剪刀石头布等方式决出胜负方,决定谁当白军,谁当红军,互相打仗,从田野杀到山坡,天黑了才回家。《文心雕龙》说“各师成心,其异如面”,作者以赤子之心,场景式再现童年时期的纯真无邪,往后折射四五十年,把作者的部分本性给透析出来了。
《斗地主》同样强烈地凝固焊实了“历史独断论”的那个特定情节:“在批斗会上,我因喝牛奶而下跪/在接下来的游街中,我学了一路的牛叫”。这首诗从另一个角度楔入狰狞的历史,历史往往像十二级台风一般把一切裹挟进去,包括阳光灿烂的童年、旋转的木马、蜻蜓栖落的秋千,往童年的天空降下可怕的硫酸雨,在幼小心灵铺上乌云。所幸,60年代那批人受到的污染或者说心灵戕害并不严重,一阵东风很快就吹散乌云。
周瑟瑟勾芡了童真记忆的诗,更多还是以打架、掏鸟窝、爬树、偷地瓜等常规童年价值体系为主,在《谁偷了我家肥肉》一诗中,作者把那个年代贫穷的酸涩以儿童漫无边际的耗散式想象力作了记述,“邻居家的脏猫偷了我家的一块肥肉,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我昨天在打谷场看见它嘴唇上的胡须闪着油光”。《打架》对此进行了回味“在放学的路上我们可以干很多事/打架是我们最爱干的一件大事情……”。《文心雕龙》第6章《明诗》中觉得诗歌写作就要“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杜甫曾豪气冲天地总结李白“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打架斗殴、飞扬跋扈、任气耍泼本身是儿童价值谱系里最常见的,无可厚非,这样的童年才是酣畅淋漓的。最关键的是,这一切发生的背景是乡村,不是城市。只有乡村,只有大地,才能为童真铺展开辽阔的叙述空间,为人性无遮蔽、零距离返归大地,吸纳地气提供条件。
嵌入地方风物 抵御全球同质
叶芝认为“我们所做所说所歌唱的一切,都来自同大地的接触”,周瑟瑟本土性写作的第二“症候”是嵌入了地方性。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用诗歌语言记录、传唱故乡的风土人情、民风民俗,在近年的本土性写作里成了罕见品质。近年的土地写作,大部分是伪浪漫主义的幽灵复活,用现代语言的瓶子盛装唐诗宋词的旧酒,复制陶渊明、王维的花花草草莺莺燕燕,清逸、散淡,千人同腔,万人同调,看不出福柯的“位所”关系与地域特征。而地方性就是往本土写作里打进特殊品质的一枚楔子,它强化了故土的本体性,亚里士多德主张“本体亦即怎是”,它怎么会是此在的、排他的、充满个人DNA和遗传密码的,必须要用语言使之澄明,把那些语言到达之前的黑暗本体呼唤出来。故土的本体性千百年来一直存在在那里,在袅袅炊烟的上升与花桥的喧闹里,在神秘的祖牌和庄严的仪式中。古希腊的巴门尼德早就说过“存在者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问题在于人能不能用语言把存在对象化与物理化,进而历史化。
周瑟瑟作了良好的尝试,为湘东北那一带的部分本体性作了“呼唤”。《艾蒿》一诗写道“老屋门楣挂艾蒿/黄牛拴在地坪中央/蚊子包围了它/木桌摆放好/一钵麻花炖肉/一碗辣椒/竹筷清清楚楚”,把湘东北一带的民风民情折射出了,他们有好吃辣椒的饮食习惯,还有往门上挂艾蒿的风俗。民谚说:“清明插柳,端午插艾”,端午节挂艾蒿的风俗据说最早起源于荆楚一带,为除湿气、避邪魔、逐虫蛇,后来随着人口往闽粤赣等南方之南迁移,这个风俗才渐渐扩散至开来。“清晨他们/开车从长沙出发/来吃杀猪饭/屠夫卖完肉/六点钟就过来/杀解年猪……我们吃完杀猪饭/再去湘边江/面对平静的江水/狂拍了一通”这些句子来自《他们来吃杀猪饭》这首诗,这首写于2017年12月,说明吃杀猪饭这个习惯至今还保留在湘东北一带,而福建大部分地方没有这种习惯。本人记得,小时候杀猪会给邻居端一碗猪肉汤,给亲戚送一两斤猪肉,从来没有召集族人或亲朋聚集一起吃杀猪饭。现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连端猪肉汤和送猪肉都取消了,什么都没有了。而周瑟瑟的故乡还保留着那个古老习惯,说明那里对传统文化传承得更深刻,人性中最古老的泉眼还没有被现代性这架水泵抽干。
奥登认为“由于通天塔的诅咒,诗是所有艺术中最具有地方性的。但是今天,当文明在整个世界上一天天变得单调时,人们感到这与其说是诅咒,不如说是祝福,至少在诗中不会有什么‘国际风格’”。故土的本体性,就是抵制现代主义的侵蚀与篡改。海德格尔把进入现代以来的存在称为“世界之夜”,美国的理查德•沃林在《海德格尔与后现代》一文中觉得“海德格尔追随荷尔德林,将当代视为一个‘完全贫乏的时代’,一个诸神已去和新诸神尚未到来之间的被遗弃的时期。在《克服形而上学》一文中,他把现时代的特征描述为‘这个世界的崩溃’‘大地的荒芜’‘现存一切无条件物化’”。海德格尔悲叹:对于存在我们太早,对于诸神我们已太迟。诸神远逝的现代主义像一股刮遍世界的超强台风,横扫一切,给世界带来可怕的同质化,消灭文化差异与地域风情。欧阳江河在《电子碎片时代的诗歌写作中》批判“现代性已经丧失了哀痛和抵制,变成了资本和大数据的庆典”。现代主义与全球化浪潮加速了方言、小语种、小众式图腾、边远地区小宗教、民间伦理、地方风俗、传统习惯等的瓦解消亡。在推土机的轰鸣声里,高速公路开进了人类内心,钢筋水泥丛林强行在枯萎的心灵构筑起冰冷干燥的盛世图像。高速公路和铁轨铺到哪里,就把现代主义的同质化污染到哪里,也就把千差万别的地域文化、民族风情、本土气质摧毁到哪里。推土机蛮横的霸权话语,阻断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天地互文性,也打破了“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世界共生性。
本土性写作作为人类抵御全球化浪潮的最后屏障之一,理应受到重视。周瑟瑟2017年年底写的《寒食》《蛇》等作品,为精神的故土作了挽留,“今天不要吃鱼肉/今天不要骂人/今天不要生火做饭/今天不要游玩/今天去后山/坐在父母的坟边/做一个饥饿的人/今天你是晋文公/呼喊介子推/介子推背着母亲/进了绵山”(《寒食》),这首诗打通了遥远而古老的传统,2600年前的寒食节(清明节的演化源之一)食冷食,不生火,纪念介子推。现在,许多地区仍然保留在那天吃冷食的习惯,保留用生冷肉食祭祀祖宗的风俗。《蛇》这首诗写道“下午就要离开家了/我收拾床铺/伸手摸到软软的蛇/它蜷曲的身体突然散开/哦妈妈/我摸到了你的皮肤/另一个世界的凉爽/蛇通人性/妈妈生前在衣柜里/与一条更大的蛇相遇/她认定那是父亲的化身……/他说留下蛇守屋/不要让它走了/家蛇是自由的/它可以在屋里/自由进出”,这首诗凸显了泛神论、循环论以及“齐物我、同生死”那套古老价值体系。
泛神论或者泛灵论在现代主义视域里正是地方小宗教、小众式图腾,是边远落后地区以及古典主义时期的“落后宗教”,在宏大高迈繁华的基督教、天主教、佛教等看来,它就是个农耕式宗教,甚至还不能称为宗教。在中国古典主义时期,或者在当今许多边远农村地区,仍延续这个小众式图腾。它的主要特点是万物有灵,草木山川皆有神祇。所以,屋里溜出来的一条蛇会被当作寄托祖魂的动物,甚至直接被当作祖先的化身或者视为先人的使者,不能惊扰它。有泛神论思想的作者摸到了蛇,自然而然联想到摸到了妈妈的皮肤。诗中结尾称这条蛇为“家蛇”,说明泛神论者已经把它当作灶神、土地伯公等同等看待,是家的护佑者,而不是别的什么。毕达哥拉斯认为“凡是存在的东西,都要在某种循环里再生,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新生”,这可以作为泛神论的注脚。
泛灵论在中国农村地区有着强大生命力,直到今天,在福建客家人聚集区,那些中老年农村妇女,仍然是泛神论的信仰者。孩提时期,春节晚上吃团圆饭时,笔者家里常常蹦出几只草蜢、螳螂,跳到桌上。我们小孩惊声尖叫,要找东西把它们拍死。母亲喝止道,是你们的爷爷回来了,不得乱动!你们爷爷在世时,过年吃团圆饭必定要在桌上留一副空碗筷、空酒杯、空椅子,酒倒满,菜挟好,这是留给祖先的。2017年8月,笔者一家人上山祭祖,在某祖坟边窜出一条蛇。其中一人抡起锄头就要追,被二哥厉声喝住,不能打!这是灵蛇,祖先或寄生其上,打了就要遭受不祥。
朱大可在与北村的一篇谈话录《地域文化与人类精神及其他》中过于敏感地判断:“它(地域)把一切属于全球的思想扼杀在有限的风景里,民俗、风情、习惯,这些地域意识形态妨碍了个体精神的生长”,这句话要是放在晚清,用来批判官方意识形态主张闭关锁国那套价值也许有效,或者用来抵消某个历史时期狭隘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的论调可能更适当。但今天,历史语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主义骑着全球化这匹马,踏进世界每个角落。全球化已经成长为浩浩荡荡、风卷残云的最强悍意识形态,它不容置疑、荡平一切,把人类的穿着品味、审美尺度、饮食习惯、建筑风格、工业生产、流行时尚等统一纳入到“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式的大一统结构里,进行千篇一律的改造与消化,弊端日益明显。在这种语境下,本土气质与地域叙事,恰恰是张扬个体精神的一种载体,是狙击同质化、全球化的坚强堡垒。所以,当代语境最迫切的不是全球化,而是“化”全球。
痛抒逝亲之哀 回归古典人格
吊亲思情是周瑟瑟近年比重较大的一个题材,《诗经》里对父母的恩义这样写:“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母慈子孝乃人类最温暖的价值。周瑟瑟的父母于近年去世,他用诗歌写出了对亡父亡母哀哀欲绝的泣血之痛。通过吊亲思情的抒怀,把对乡土的眷念升华到滚烫、沸腾的精神高度,是周瑟瑟诗歌的另一重特色。对故乡的眷恋与对父母的怀念形成复调结构,两者互文,互相浇灌,共同生长,最后枝繁叶茂。
以赛亚•柏林认为“乡愁是所有痛苦中最为高尚的痛苦”。乡愁是本土写作的永恒主题,“愁”从何来?以何寄托?很多人无病呻吟,心中无愁,硬生生地把愁发明出来。明明浸泡在蜜罐里,假装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坐在大都市阳台上,抚摸着日益肥腻的大肚子写出“想起故乡啊,我泪流满面”“悲痛万分啊,梦中还乡”之类连自己都不相信的句子。茅台喝着,中华抽着,桑拿洗着,名牌穿着,豪宅住着,宝马开着,舞厅泡着,您也没病找病地假思乡、假忧愁,鬼才信呐!这样流出来的泪水也不含盐。目前,诗坛上盛行的大部分是这种缺乏痛感的作品,住在黄金屋里闲得慌。
乡愁之“愁”必须要找到载体,也就是说,诗人们必须找到盛装“愁”的容器,对亡父亡母的凭吊哀思就是其中一种容器。“一个人死后,他的气息还会存在三年/姐姐说这是父亲生前告诉她的”“我的老屋空无一人,父亲的遗像在客厅端坐/‘让他守屋’母亲说,院子里一棵老桂花树/在静寂的夜晚散发植物的清香,我怀念故乡/的树木在黑夜里发光,像我的赤脚踩进雨水”,这是《栗山》中的句子。《寒食》中这样写“父亲消失了/母亲也消失/我回到栗山三天/只为独自一人/度过漫漫长夜/风吹落叶沙沙滚动/风吹铁门在地面摩擦/没有人在夜里回家……父母的坟边/等待众鸟醒来/等待爱像白云飞翔”。《蛇》这首有这样的句子“妈妈生前在衣柜里/与一条更大的蛇相遇/她认定那是父亲的化身/我要离家了/这条温和的蛇/向我抬起头/我哇地一声哭叫妈妈”。
故土故土,必须在泥土里融入亲人的呼吸,托付亲人的魂魄,胞衣植入其中,祖先埋葬其内,泪水滴过,血流过,这样的土地才是故土,这样的泥土才是熟土。否则,你寓居的钢筋水泥与他乡异地,只是生土,是旅馆,物理上的住宅。作者回家三天,也许是替父母扫墓,也许仅仅是看一看老屋。父母离世往往能强化“噬心”的乡愁,把人由于忙碌、由于生计应酬导致对故乡的疏远、隔膜,重新唤醒,把人性中古老的“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式的情感进行强化。周瑟瑟常年奔波在外,父母离世这件事,把他那颗像风筝一样四处飘的心,往故乡方向扯近。《荀子•礼论》写道“过故乡,则必徘徊焉,鸣号焉,踯躅焉,踟蹰焉,然后能去之”。丧考妣后,作者必定经历了许多独自徘徊在故乡的小径,独自在夜色里散步,独自且无言地听故乡的晚蝉,观看故乡的晚霞等。这种时刻,人最能变成哲学化的人,他往往会对自己的前半生进行总结、反思,那个很久没有思考的永恒之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在那个时刻往往会重现人们的大脑。人在这种时候,也常常会对大道、无常、天命、生死、古今等问题作形而上的透彻拷问。其实,这类拷问,古人也发出过。贺知章在《回乡偶书之二》里写道:“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高尔基有个观点“一个老年人的死亡,等于倾倒了一座博物馆”,在周瑟瑟这里,父母离世,可能就不仅仅是博物馆倒塌了,可能他灵魂中的一部分都被父母带走了。博物馆倒塌带来精神的短暂空白,一部分灵魂被带走,则能加重作者的人生迷惘感,被抛离感。比如,《蜜蜂》《谁在故乡的下半夜》等诗就透露了迷惘与抛离——“妈妈的卧室/保持她去医院/看病那一天的情形/蜜蜂/很多年来都会进来/今年的巡视/只看见陌生的儿子/躺在妈妈的床上/仿佛蜜蜂/迷失了方向”(《蜜蜂》),“谁在故乡的下半夜说话/谁在啼哭/谁在辗转反侧/我在故乡的下半夜/睁着眼睛/听见父母在老屋/念叨某一件事情/听不清最后的结论/少年的我趴在蚊帐里/渐渐睡去/三十年后/我在故乡的客栈醒来/一身的汗”(《谁在故乡的下半夜》)。这种迷惘与抛离,很容易诱发作者感时伤逝,把平时被压制的某些情愫唤醒,如孤身在外奋斗个人事业的艰辛之感,紧张激烈的现代主义节奏给人带来的不安、疏离以及异化感,衍生出渴求内心安定、平稳的精神倾向。人过中年之后,随着年岁增长,身上的现代主义人格会逐渐隐退,古典主义人格日益生长。也就是说,入世人格的暗涌与出世人格的汹涌将会有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出世人格将促进人们抵制紧张激烈、尔虞我诈、声色犬马的现代主义,转而退回内心,寄希翼于炊烟袅袅、牧童骑牛、晚蝉轻鸣的古典情怀。海德格尔有过同感“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骛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内心,转回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田野牧歌式的家园能安抚现代人惊悸惶恐的情绪,舔舐精神上的创伤。德国的诺瓦利斯有相似的看法,他说过“乡愁源于对异乡的不安,家园消解了乡愁的不安。”这种不安与疏离,严重时可能还会导致人们抵制他乡异地,在精神上融不进都市,发出“遣怀常作登楼望,万户千灯不是家”的感慨。
周瑟瑟的吊亲抒怀诗,确证了他重人伦、担孝义的品格。孟子对尊老孝老的重要性说过“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气是也”。
拟写山川物候 构建本土气质
山川物候拟像式的诗,是周瑟瑟本土性写作的另一种常态。山川地理、气候物产等是文学写作波澜壮阔的题材。土能生万物,地可载山川。大地与四季催生一切生灵,孔子谓之“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文学像蘑菇、青草一样从土地里生出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曾提出,支配人们的东西有许多,气候、宗教、法律、政府的准则、过去的榜样、习惯、风俗,但只有包括土壤肥瘠在内的气候带才是支配一切的东西。弗罗斯特觉得,人的个性一半是地域性。《礼记•王制》里说“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黄文焕《自课堂集序》云“地有南北之分,北方风气高劲,不坠纤丽,本属诗文之区,空同、于鳞均擅北产。然南方唱和,习所渐染者多,至于以时论之,则宜少宜多又各分焉。”这些先贤之言,都在强调地域、气候等对文化以及风俗的影响。梁宗岱也说过“我们最隐秘和最深沉的灵魂都是与时节、景色和气候很密切地相互纠结”。
周瑟瑟的诗与时节、景色、气候、山川有哪些纠结呢?《火烧云》里写道“池塘滚烫/如母亲/烧开的一锅白云/晩霞自投栗山塘/若干年前/我们在傍晚/跳进了池塘/母亲的呼唤并不能/让我们爬上岸”;《湘临一站》一开头就这样“湘临一站/堤上人家的灯亮了/夕阳穿过湖泊/照在远去洞庭的湘江支流/江上浮来一条机船”。水、江河、池塘、湖泊等词像在周瑟瑟的诗里大量出现,与他出生、成长的湘东北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湘阴那一带,拥有丰富的水资源,湘江自南向北贯穿全境,小溪小河像毛细血管一样密布山丘平原,湖泊、池塘随处可见。滨湖、江河、溪谷3种平原共占湘阴县总面积的44.4%,当地人总结为“一山四水三分田,二分道路和庄园”。很明显,平原广阔,江河纵横,山坡少,这种地方熏陶的文学气质肯定不同于高山高原地区。比如,笔者生长的闽西地区,地理特征为“八山一水一分田”,放眼四望,全是山,高山会囚禁一个人的想象力和灵气,造就压抑、敏感、神秘的气质。周瑟瑟的这类故土诗,受到江河湖泊滋养,被平原撑起辽阔的骨骼结构,画面壮大,意象疏朗,把故乡的常态生活建构起来。
周瑟瑟直接把故乡的一座山、一个坝、一个塘、一条沟等搬进诗里,直接进行地理学写作,这样的作品有《樟树镇有多神秘》《潭水脚里》《拦家龙》《蓖麻长在上寺塘》等,这里提到的“上寺塘”“拦家龙”等,都是他家乡的某个地名,诗中写到的个人事件与历史图景,都发生在这些地方,能够一一对应起来,樟树镇就是行政区划上他的故乡。周瑟瑟把乡村影像、个人历史、本土气质、地域精神牢牢结合起来,把精神本土性写作铸成地方志、个人史、方言录一类的东西,实像、本真、物化,不是那种凌空蹈虚的“乡愁”,那个毫无实体支撑的空洞“乡情”。周瑟瑟的乡愁,都附着在实体、实物上。特别是“栗山”这个地方,笔者大略统计了一下,这个词在作者近5年的诗中,至少出现了100次以上。栗山是周瑟瑟老家的一座山,他的父母、祖先都长眠于此,是令作者魂牵梦绕的一座山。作者不厌其烦地抒写它,是想把它铸造成寄托故土魂魄的地理坐标,一个存放乡愁的精神灯塔,在他漂泊他乡时,提供源源不断的族缘伦理动力,鼓舞他昂然面对人生风雨,在受伤后舔舐其精神创伤。许多伟大作家都有自己的精神地标,莫言的高密乡,沈从文的湘西等等。作家建立自己的精神地标,便于在茫茫大地找到归宿,助于在凄风苦雨的人生里把内心风帆停靠在温暖的港湾。栗山就是周瑟瑟不断出发,不断归来的福地。
湘东北那一带的物产、方言也经常进入周瑟瑟的诗中,他有一些诗写家乡特产辣椒、橘子等,比如《橘子为何如此甜蜜》一诗写到:“我回到家乡/发现家家种橘/门前屋后果树飘香”,《青橙》写的是另一种特产“茂密的叶子/像一个人的激情/在我家老菜园里/橙子树正是壮年/果实高悬/枝干挺立/我抚摸青橙/使劲闻它自然的青香”。这些地方物产,仍然是盛装乡愁的器皿,它们是促成作者建构精神地标的附着物。俗话说,百样米养百样人,千差万别的物产肯定滋养缤纷的差异性人性,从而形成文化的地域“症候”。《淮南子•形训》里说:“土地各以其类生……轻土多利,重土多迟,清水音小,浊水音大,湍水人轻,迟水人重,中土多圣人。皆象其气,皆应其类……是故坚土人刚,弱土人肥;垆土人大,沙土人细,土人美,秏土人丑。”笔者判断,地域性物产对一个人的味觉、嗅觉、饮食倾向会起到终生的主宰、引领作用,奠定一个人切入世界的色彩与味道。
周瑟瑟有一首《方言》的作品,把方言的神秘与在当代的失落感写了出来:“一个中年妇女/在窗外用方言回答/另一个人的询问/她说出了我小时候/常常说出的话/声调平和/四声上扬/她的舌尖上/保存了故乡的秘密/我知道就在唇齿之间/但我已经丧失/不是所有的方言/都能从故乡带走/我开门追随她/这楚国的妇女/她在地里摘辣椒/她骄傲地说出了/楚辞的语气和音调”。海德格尔有个著名的判断,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方言是承载一个地方日常生活的最重要价值系统,它能替一个族群保留古老的民俗民情,与众不同的生活习惯,这个族群千百年来的呼吸节奏与阐述世界的语法特征。
一个地方所有形而上的东西,鬼神、小宗教、地方伦理、宗法制等,以及形而下的婚姻、饮食起居、生老病死,都离不开方言这个载体。地方人就居住在方言里,方言是一个地方宗法群体的共同住宅。方言是实现一个地域、一个族群区别于其他地方的最强烈识别物,是维持语言价值体系丰富、差异、互补、增值不可或缺的营养。方言的危机就是语言本身的危机,进而演化为存在的危机。上帝早就看出了这一潜伏的语言危机,《旧约》记载,在古巴比伦人们使用统一语言,试图构建通天塔,耶和华敏锐地察觉到了语言统一的可怕,于是更改了人类的喉舌与发音系统,令各地方的人群操持不同语言。
在现代主义卷起全球化浪潮铺向世界之际,方言再次危机四伏,通天塔摇摇欲坠。英语、计算机语言系统随着全球化浪潮推进,逐村逐族地取消方言,在经济利益与社会发展的诱惑下,同质化的英语与计算机语言统一了人类的喉舌与发音系统,构建通天塔的威胁变得越来越明显。方言承载的那一套地方性价值谱系也变得岌岌可危,取消一种方言意味着消灭一种生活习惯、消灭一种风土人情,世界将陷入千人同腔、万人同调的可怕深渊,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将在全球化语言同构下变成一片沙漠。方言取消后,故乡必将取消,乡愁再也找不到载体。形而上的、精神上的故乡消失后,人类再也找不到归属感,找不到对大地的认同感,从而开启精神上的新一轮流亡。当全球化消灭了所有方言,大地将沦为纯物理学住房,人类内心将被钢筋水泥焊死。最近四十年来,有一个普遍现象未引起足够重视,学校与家长都向子女传授普通话与英语,排斥故乡的方言,潜意识里沦为消灭方言的帮凶,使得80后、90后、00后那三代人几乎遗忘了方言,成为全球化的语言同化里的“夹生饭”,还未融入世界,已经丢失故乡。很明显,周瑟瑟跟那些敏锐者一样,意识到方言的失落,他才会说,那个操持方言的妇女,舌尖上保留着故乡的秘密。
剪删丰腴之辞 排除纤秘之巧
庞德在《回顾》一文中认为“不要用多余的词,不要用无法揭示任何东西的形容词”,他公开反对语言的修饰功能,他甚至非常忌讳地为现代诗订出写作原则“我与理查德•奥尔顿经协商同意以下三条原则:1,直接处理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的事物;2,绝对不用任何无助于呈现的词……”周瑟瑟最近几年的作品,越来越倾向于直接处理事物,取消修饰性,不采用或者说极少采用形容词、副词,语言表现为单刀直入的状态。比如《蛙鸣之夜》这首“白天的喧嚣/在某一个时刻/突然消退/我来到室外/栗山模糊/匍匐在大地/夜鸟收紧了翅膀”;《黄牛》也是这种写法“我回家的第一天/它就在栗山塘的/电线杆下咀嚼/黄泥似的浅毛/肮脏又零乱/像我弱小的亲人/默默忍受着什么”。这样的语言,比较接近生活中的元语言,周瑟瑟近年提出了“元写作”方式。他在重建当代诗的语感、语调与节奏,被批评家陈亚平称为“简语写作”。他创造的是一种全新的具有个人气质的现代性诗歌语言,“诗歌现代性启蒙”也是周瑟瑟近年反复强调的,他把诗歌语言引向现代意识,但完全是建立在本土化与个人化的写作之上。
也许,作者已意识到《文心雕龙》提醒的“腴辞弗剪、颇累文骨”,丰腴的修饰将压垮文章结构。当代诗歌,正深陷在刘勰所指出的写作症候深渊里“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过度追求文雅与修辞。有时候,一首诗读下来,除了修辞技艺,什么也看不到。有些人甚至主张,诗歌就是要从修辞开始,到修辞结束,把方法、手段当作写作的终极价值。周瑟瑟显然对这样的写作保持警惕,他的写作资源从早年的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一路走来,那些通感、隐喻、复调、戏拟、互文、拼贴、畸联等现代诗常用手法,他早已写得精熟。只是人到中年以后,写作内部会进行自我调整,他更倾向以“随性适分”的自然状态切入写作。现代主义主张,写作就是要重新发明语言,鼓动诗人们坐在书桌前来临时发明语言。法国的吉尔•德勒兹有一种观点,认为:“作家在语言中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类似一门外语的语言,令新的语法和句法力量得以诞生。他将语言拽出惯常的路径,令它开始发狂。”周瑟瑟已经过了重新发明语言的历史时期,他跟其他采用现代写法的诗人一样,在写作的早期阶段,在青春汁液汹涌澎湃的时候,也曾在写作内部高喊打倒什么、推翻什么,令语言越出常轨,在脱轨的快感下撒野。周瑟瑟近年的诗歌,主要是及物、实景、白描等手法,结构呈现为单弦、一元制,语言放射出能指蓝幽幽的光芒。
重新回到常态语言,诗歌列车重新驶回常轨,是很大一部分诗人在中年以后的自然选择,这跟古典主义人格在诗人体内的苏醒有关。古典人格的主要特征是心平气和,言从字顺,就像华兹华斯说的“诗起源于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
到了这个阶段,写作已进入“造怀指事,不求纤秘之巧;驱辞逐浪,唯取昭晰之能”(《文心雕龙》)的境界。在这样的状态里,诗人对题材的选择不再刻意,对语言的雕琢不再叛逆。一切都“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这个阶段,语言是不是完全成了清水?一览无余?并非如此,早期的现代主义修辞强化训练会在作者笔下留下痕迹,比如《栗山》那100首短诗组成的长诗集,就还残存着复调、互文、畸联等现代写法的体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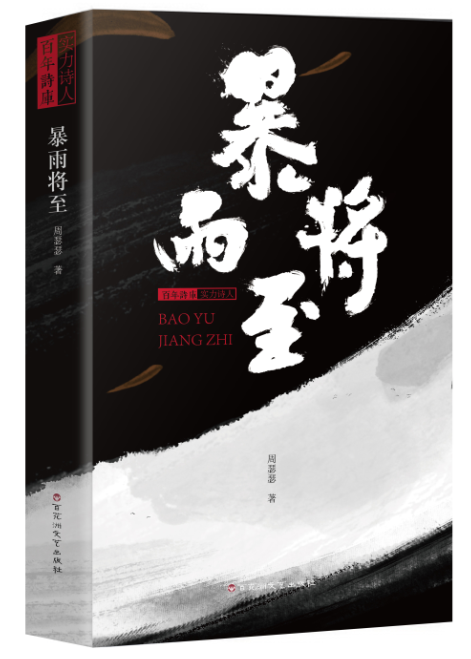
《暴雨将至》 周瑟瑟/著
——————————————————————
作者简介:
林忠成,生于七十年代,长于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土楼所在地永定。作品刊发于国内外报刊,部分诗歌翻译成英语、德语,编入近100种选集。2014年在福建召开个人作品研讨会。文学刊物《土楼》副主编。

林忠成近影


 纯贵坊酒业
纯贵坊酒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