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进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光怪陆离的中国诗歌充斥着“下半身”写作、垃圾派、“羊羔体”、“梨花体”时,诗歌群落中形成了一个影响逐渐扩大的北漂诗人群。这些诗人从大江南北、天涯海角来到首都北京,分布在北京不同角落和各行各业。作为高速流动时代的特殊社会群落,他们的出身不一、素养各异,社会名气和经济实力也各有不同,但却有着身历地理与精神流动的共同身份:北漂诗人。尽管审美趣味和诗学追求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是在异地异乡写作,在一种“无根”话语的包围中用自我生存体验的个体写作。很大程度上说,他们所置身的境遇和面对的问题却又大致相同,这种境遇就是肉身与精神的双重漂泊,而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安妥生存和灵魂的漂泊。师力斌、安琪主编的《北漂诗篇》正是北漂诗人诗歌的首次集结,既是诗人们想象北京的“北京志”,又是真实反映北漂人的文化想象和心理诉求的最佳诗选。作为异乡人的存在,北漂诗人将时代的驳杂现场与心灵的深度体验融合,使这部诗集不仅能窥探到北漂者的生存境况和时代的精神图景,而且还展现出新世纪的漂泊诗学以及诗、史与思兼备的多重品格。
一、时空地图:身份与“北漂”流动脉络
北漂是指来自非北京地区的、非北京户口的,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人,包括外地人和外国人。这个漂泊的群体来北京初期都很少有固定住所,给人飘忽不定之感。如安琪所自述的,她“北漂13年,把北京的东南西北中都住过,搬了10次家,筒子楼也住过,塔楼也住过,蜗居也住过,办公室也住过,摇摇欲坠的小平房也住过”,“每搬一次家都很仓皇,东西基本都丢在原地”。到北京从零开始的北漂人虽有着异乡人的迷茫,但他们怀揣梦想更有理想抱负和拼搏精神,尤其是对北京这个古老城市和现代都市的向往和不懈抗争的毅力和豪气。《北漂诗篇》的“辑一”恰好收入了现居住在北京的98位优秀北漂诗人的诗作,展示了近百种北漂人生样态。诗集的“辑二”收录的是曾经在北京生活而后又离京的“前北漂”,包括梁小斌、程一身、布非步、天岚等26位诗人。在这场充满诗意的交流与对话中,共同展示了124位北漂诗人心中形态各异的北京想象。
从身份来看,这批诗歌写作者中有学者、作家、画家、出版人、电影人、艺术家、企业家、自由撰稿人和打工者等。其中,有朦胧诗代表诗人梁小斌、文化画家和诗人车前子、文化批评家叶匡政、打工春晚创办者亦是北京皮村打工艺术团团长孙恒、歌手许多、12岁的网络元气少女李圆圆,还有艺术成就令人瞩目却又为人所不熟知的宋庄艺术家群体包括李川、石梓含、朱子庆、阿琪阿钰、沈亦然、王顺健、马莉、邢昊、潘漠子等。单从传媒行业来看,北京就聚集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诗人,如“影视行业的周瑟瑟、老巢、宋咏梅、才旺瑙乳、李成恩、刘不伟。编辑、出版、网站等行业的沈浩波、白连春、娜仁琪琪格、安琪、王秀云、不识北、黑丰、孤城、林茶居、李兆庆、林平、星汉、谢长安、刘傲夫、苏笑嫣、于丹等”。这些诗人创造力旺盛,活跃于北京和国内诗歌界,他们不约而同地用诗歌记录着北京的发展变迁,以及对北京生活的认知和体验。
《北漂诗篇》是按照写作者来北京时间的先后顺序来编排的,一定程度上搭建起了北漂诗人的历史链条,用诗语记录了北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入选者到北京的时间来看,现北漂诗人最早到的是1991年到京的潇潇,最晚近的是2016年到京的许烟波、小海、杨泽西、叶上达等诗人。前北漂诗人中最早到京的是1993年到的刘不伟,2016年离京的有郎启波等;逗留时间最短的是2008年3月至9月在京的陈波来和1996年秋至年末短暂北漂的王寒山。恰如安琪在“后记”中说的,这些诗人进京和离京,“有一种前赴后继感,也是一代代人北漂的明证”。在26位前北漂诗人中,年龄最大的是1954年出生的梁小斌,最小的是2005年出生的李圆圆,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诗人有12人,“70后”诗人有10人,“80后”诗人有天岚(刘秀峰)、陈波来、七月友小虎(李源)等2人。而在98位现北漂诗人中,除北京皮村打工诗人无法确定出生年月外,“50后”诗人有2人,“60后”诗人有29人,“70后”诗人有28人,“80后”诗人有20人,“90后”诗人有11人。由此可见,不论是现北漂,还是前北漂,这一诗歌群落的主体都是“60后”和“70后”诗人。但引人注目的是作为青年诗人的“80后”和“90后”从2008年开始逐步增加,日渐成为北漂诗人群落中的主力军。
从空间流动来说,以首都北京为中心,这一迁徙与飘移的诗人群体从小区域走向大区域,或者从大区域再转回小区域,一切都行动了起来。若按照生活的空间线索,可以清晰地看到,北漂诗人的生活经历和流动区域又是纷繁复杂的。从流入北京的情况来看,流入省份(自治区)前三位的是河南(13)、安徽(10)、山东(8),随后依次是河北(7)、辽宁(6)、福建(6)、湖北(6)、甘肃(5)、浙江(4),湖南(4)、江西(4)、江苏(3)、内蒙古(3)、吉林(3)、广东(3)、黑龙江(3)、山西(2)、陕西(2)、四川(2)、贵州(2)等。不难发现,来自河南、安徽、湖南、湖北、江西、山西等中部六省的北漂诗人占据总数的比例达41%之多。这些诗人走向北京这样的大都市,构成了人生走向上远离家乡故土的流动轨迹。从北京流出返乡情况来看,流回省份(自治区)分别是浙江(3)、广东(3)、江苏(2)、湖南(2)、湖北(2)、内蒙古(2)、贵州(2)、四川(1)、河北(1)、河南(1)、云南(1)、安徽(1)、江西(1)、海南(1)、广西(1)、山东(1)、福建(1)等。在这里,从北京返回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流动最明显,可以见到,大多数诗人都选择返回原籍生活,从故乡到异乡再到故乡构成了地理上循环的流动圈。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北漂诗篇》在时间先后编排与区域空间流动的交织中构成了时空的坐标系,这种时间的推进移动和空间的故乡/异乡的循环,既形成了一张彰显北漂诗人身份和流动轨迹的时空地图,同时也揭示了时空流动的经纬与血脉。
二、异乡/故乡:城乡中国语境的乡愁书写
如今,现代人的流动愈加容易和频繁,这种时空流动和生活变化导致人的心理结构和精神状态发生了很大变化。曾经赖以生存和熟知的故乡逐渐变成追忆怀旧和情感寄托之所,正如歌手李健在《异乡人》中写的:“近在眼前的繁华/多少人着迷/当你走近才发现/远过故乡的距离/不知不觉把他乡/当作了故乡/故乡却已成他乡/偶尔你才敢回望/曾经的坎坷/现在不用讲/异乡的人有着相同的惆怅。”然而,这种把“故乡”当作“他乡”的异乡愁体验,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国家想象和乡土中国的情感投射,而是在“城乡中国”语境中富于反思自我和他者关系的“乡愁”。对大多数北漂诗人来说,他们“一方面抒写了某一地域文化所传递的信息,无形中渗透了该地域的地理景观与人文特色;另一方面又通过诗歌创作影响了这一地域的文化基因”。事实上,《北漂诗篇》对于“异乡/故乡”的双重互动书写也促成了诗歌和文化之间的转换和融合,催生了新的诗歌特质。
北漂诗人对北京有着极其复杂的感情,《北漂诗篇》在每位诗人的介绍中特意附有一两句感言,这些风格迥异的感言在一定程度上恰能窥见北漂诗人们的空间感知和情感态度。不过,不同代际的诗人又提供了不同心灵感受。“60后”诗人李飞骏坚信:“北漂的际遇,恰是诗歌的际遇,也是时代的际遇。我手写我口,做时代的证人。”王迪说:“是因为北漂,激活我又重新写起诗来。北漂,谢谢北漂!”杨北城感叹:“北漂,即使在地下室匍匐着前行,也要保持飞翔的姿势。”叶匡政则意识到:“北漂像贱民的胎记,藏得再深,都暴露出一个时代的耻辱。”再看“70后”诗人的感受,许烟波认为:“背负理想行走远方。”赵天鹏说:“在一座希望、失望、欲望并存的城市漂泊,是一种选择。”冰凌感慨:“北漂的生活让我成长。”鲁橹则轻描淡写地说:“北漂,落脚而已。”相较于“60后”诗人“飞翔的姿势”和“70后”诗人的感恩“成长”,“80后”诗人则表现出一种“在路上”的姿态。朱翔宇满怀信心:“希望在路上。”小海也相信:“无论是辉煌的还是暗淡的。既然北漂,就不怕嘲笑。”三四则期盼:“漂久了,也会生根。”可以明显看到的是,“90后”诗人并不如上述诗人那样积极乐观,孤狼坦言:“北京这片土地,我不知道它有什么好,我只知道从我来到北京以后再也离不开了。”杨泽西则带着些许无奈地说:“活着,就好。”这些北漂诗人的感言既是向着个体的北漂人,也是向着北漂群落和不同代际的北漂人提供的认知指南。
从入选诗作名字来看,《北京、北京》《家与远方》《北京印象》《这里是北京》《在北漂的日子里》《哦,北京》等,北漂诗人们深情关注作为异乡的北京与处在远方的故乡,极其敏感地书写着在北京漂泊的生活。有对故乡的怀想和留恋,“伸手/抓一把四环的空气/盛进袋子里/干巴巴的叫作北京/⋯⋯昨夜又是谁扔的理想/谁捡起来的故乡”(叶上达《干巴巴》);“无家可归的孩子,你的眼泪流进了潮白河,异乡的游子,只有在梦里是你踏上回家的旅途”(常文铎《关于北京的诗》)。也有对故乡和异乡关系的深度体悟,“十三岁/醒时是家/梦里是远方/三十一岁/醒时是远方/梦里是家”(冰凌《家与远方》);“家乡,其实/不/远/只有两小时的高铁/一个追梦的少年/冲破黎明的地平线/就出发了/惊慌中没带一件行李/鲁西南平原的纽扣/就淡成/一首无题的朦胧诗/从此,金乡成了我的/远方”(李飞骏《诗与远方》);“而我又没有钱/而我又一个人在北京/漂泊/⋯⋯只要房东把门锁了/我就无家可归/实际上我本身就没有家/关于未来/我没有未来”(不识北《你们思考人类我思考我自己》)。还有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与期盼,许多最初所体验的北京是:“北京好大好大/北京好冷好冷好冷/北京也好热好热/北京没有我的家”,此后感受到“北京好大好大/北京好冷好冷好冷/北京也好热好热/北京也有我的家”,最终接受这样一种生活与存在,“北京好大好大/北京好冷好冷好冷/北京也好热好热/北京就是我的家”(许多《北京、北京》)。可以说,从最初的迷惘和感伤,到幸福与希望的唤醒,写出了北漂人奔波挣扎的处境和心态。
在乡愁书写的情感序列上,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有:家、故乡、根,与此相应的漂泊体验是:外乡人、异乡、还乡。有对身份的纠结与确证,“没有人能够识别我们的身份/我们只是微不足道的生活的一小部分而已/每天,城市都会高速运转/仿佛,一掺及乡愁和孤独/你这个微小的零件就会卡壳、损坏/迅速被城市换上新的一个”(杨泽西《北京地下室之蚁族》);“外乡人染着尘土的馨香/很容易在人群之中辨别出来//外乡人一般粗胳膊粗腿粗脖子/眼光如炬一语不发//外乡人离去之后,空空的/房屋,落满了灰尘//风的前面是风/风的后面也是风//风从风中吹出风/外乡人走在回乡的路上”(张后《外乡人》);“我怀念异乡 我将去往异乡 我还未去//⋯⋯陌生人 我热爱你/以水当酒 来 我敬你伴我这一程//我会去往更远 不想停下 亲爱的陌生人/那驾载着我的马车 是异乡 是我怀念的不死地”(鲁橹《怀念异乡》)。还有上升到乡愁文化价值和形而上高度的书写,“我们徒劳地从城市回到乡村/深入大地/寻找藏在种子里的声音/以此抑制说话的冲动/直到我们从泥土中生根/我们已无家可归/我们注定一无所成/因为每一个决心出走的人/都会死在半路”(左安军《归途》);“回到一个叫金乡的县城/我成了有根的人/作为四世同堂的一分子/辈分又升了一级”(李飞骏《回乡记》);“现在我在故乡已呆一月/朋友们陆续而来/陆续而去。他们安逸/自足,从未有过/我当年的悲哀。那时我年轻/青春激荡,梦想在别处/生活也在别处/现在我还乡,怀揣/人所共知的财富/和辛酸。我对朋友们说/你看你看,一个/出走异乡的人到达过/极地,摸到过太阳也被/它的光芒刺痛”(安琪《极地之境》)。显然,城乡中国语境中的“乡愁”很大程度被赋予了更具普遍意义的还乡、寻根等认同内涵。
三、漂泊诗学:个体生存体验与灵肉安妥
21世纪以来,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那种寄希望通过还乡体认“根”的存在已经很难获得,反而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在异乡与故乡交错中的失根体验。在诗人安琪看来:“一个没有离开故乡的人不能称之为有故乡。”潘漠子也坦言:“无处不故乡。”既然“离家多年 才发觉异乡也是故乡”(苏忠《在异乡》),那么恰能做到如诗人杨炼说的:“你是奥德修斯,就注定得漂流,甚至为自己创造一个大海。”从肉身来说,漂泊是一种沉重负累和无法言传的孤独,但从精神来说,诗人的漂泊体验毫无疑问又是意义非凡的写作财富。北漂诗人们所创造的“大海”就是通过城市来把握个人与生存环境的互动,基于灵与肉的生存体验去感受并试图描绘出复杂的时空关系和心理的触动因子,自觉不自觉地将“漂泊”上升到作为生存和生命体验的高度,从而赋予了“漂泊”新的诗学意义。
地铁、车站、雾霾、沙尘暴、城管、户口、圆明园、巴士、地下室等,诸多关于北京的意象建构起了北漂诗人用身与心所体验到色彩斑斓的北京。在交通出行体验上,“在一座古老的城里/列车在地下穿行//所有乘车的人,都默不作声/轨道上咣嚓交错的声音/惊扰了在地底沉睡的灵魂//每停一站/我都会惊恐地看着上车的人”(许烟波《北京地铁》);“我们搭坐地铁和公交几个小时,来到公司/习惯性地刷卡、微笑/打开电脑,开始一天的工作”(杨泽西《北京地下室之蚁族》);“一米内。我们盯着对方/⋯⋯事实上,我瞳孔散光。迎着她/像迎着镜子里另一个赶早的自己”(花语《地铁。打量》);“它只是一辆开往旧址的巴士,808路或1路/感谢宽广,他也许还拥有806种路线去逃避//⋯⋯‘东门西站到了,下一站北门南街,去中心车站请转1路’/感谢宽广,他还有无限多的方位可以任意游移”(潘漠子《808路巴士》)。在生活环境的体验上,李飞骏感受到的是“皇城根的霾/也大大//正能量的天安门/负能量的大裤衩/都隐身了/皇霾深深深几许/紫禁城的底色/是灰的”(《北京现场:皇霾》),而“雾霾。覆盖了盘古创世时留下的那片天空/我们,即已成为离天空愈来愈远的一代人”(向与《一代人》)。
在生活与生存的体验上,诗人黑鸟之翼直言:“未来,博物馆,玻璃柜里/放着一块砖,见证了这个城市发展的历史/雾霾颗粒物织成的一块砖/是警醒后人的,一座耸立的纪念碑”(《我的城市病了》)。在这座“生病”的城市,有的忧心户口,“我在这里把诗句写下来/很像写在贫瘠、干旱的土地上/衰老的眼泪。她,长长的生命历程/很像对岸的一条大河。在版图上没有户口”(姜博瀚《户口》);有的成了房奴,“就在售楼部的那个下午/穷人的孩子掷金30万/首付买下城市一套60平米的房产/也一并买下父母一辈子的血汗/还要分期偿还”(屈磊《买房》);有的住在潮湿的地下室,“我们住在北京城的地下室里/日复一日地为生存而奋斗着/我们活过,像从未活过一样”(杨泽西《北京地下室之蚁族》);有的苦于抢票,“离过年还远呐/大家回家的心动了/一大早爬起来/坐在电脑前/等着放票//八点一到/赶紧刷票/屏幕上一个小圆圈转啊转的/票没了/这什么破网速/看到有票就是抢不到/同事骂骂咧咧走了”(李若《抢票》);隔着墙壁邻里却陌不相识,“楼上/住着两家//拆了这道墙后/只剩下一男一女”(王迪《墙》)。对于北漂的生活,冯昭有着极其深切的感悟:“五年来,北漂们的欲望/助长了房价和通货膨胀/他们把青春、喘息/掩埋在林立的写字楼里/又把自己挤出京城//北漂五年,我迟疑的手射下九个太阳/而诗歌依然在血脉里延承”(《北漂五年祭》)。
在北京这座大都市,北漂人会在意个人身份。牧野宣称:“我们并没有身份/我们也并不知道——我们/终于可以将时间——拒之于门外”(《身份》)。这里有北漂人找工作的艰辛,“在去通州的公交车上/开始于陌生的首都交流/梦想从干瘪的烧饼上开始/商场排骨摊位上的台秤/淘汰了我不精密的数学/又悻悻来到昌平/报刊社临杂工的美梦也破灭了/最后一站 租住在房山区/一家药店接纳了我/谋了个驻店‘导医’的差事”(王寒山《大雪中的北京》)。
撕开生活与生存的本相,《北漂诗篇》真切地记录了充满生活质感的北漂经验。我们很容易看到,快递员“奔波,快餐/地下室和蜇入心中的孤独/在北京,7年了,他跨不过这篱墙/但仍没有离开,黑暗里的一口井/一盏灯似的光亮中,他像风中的芦苇/金灿灿的暮色里,倒下又扬起”(蔡诚《快递员速写》)。清洁工,“傍晚/伴着渐渐亮了的街灯/你那弯曲的背影/古铜色的脸庞/和我们诉说着你的一生/最美的人哪”(寂桐《清洁工》)。在躲完城管后,卖花的春燕在“这个情人节,男友不能和往年一样送她浪漫礼物/她把最后一朵玫瑰;留给自己,留给爱情”(黑鸟之翼《把最后一朵玫瑰留给爱情》)。北京皮村的孙恒高呼:“你来自四川,我来自河南,你来自东北,他来自安徽;无论我们来自何方,都一样的要靠打工为生。你来搞建筑,我来做家政,你来做小买卖,他来做服务生;无论我们从事着哪一行啊,只为了求生存走到一起来!打工的兄弟们手牵着手,打工的旅途中不再有烦忧;雨打风吹都不怕,天下打工兄弟姐妹们是一家!”(《天下打工是一家》)。然而,这些在北京坚守的漂泊者们有着生存的困局,正如雪婷所看到的,“这里的朋友有的是工伤,有的是意外受伤,有的是他人伤害。门前挂号的人越来越多,排着长队。亲人家属陪着病人在这里过夜,每人带着毯子或睡袋,在走廊里小睡,不敢睡深,深怕夜里病人突发情况,突然离世”(《脆弱的灵魂》)。但即便是灵与肉沉重的生存,“不管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的世界里/依然坚守着这一盏破旧的灯光//虔诚的守候是我不灭的灵魂”(娜仁朵兰《我依然虔诚守候》),这大概是北漂人最淳朴的坚守,也是他们最初的梦想和信念。
四、结语
《北漂诗篇》给读者提供了什么?漂泊使北漂诗人们获得了什么?答案可能是诗歌写作的题材和主题、写作的空间和心态,等等。然而,归根结底还是北漂诗人获得了个人化的体验和生存感受,见证和体验了一个群体性和持续性的漂泊时代,写下的是属于北漂人和感知北漂人的个人诗篇。还应该看到的是,《北漂诗篇》对父母、夫妻、情侣、儿女等人的感情抒发,形成了强烈的情感冲击力,显得波澜不惊而又刻骨铭心。牧野的《母亲母亲》中,“病床上的母亲/只记得骂自己的儿女”,朱翔宇则看到,“妻子吃药,丈夫递水”的细节,感叹“已经有好多年/没见到这样的情景了/向来单身的我/心突然咯噔了几下/像是‘幸福来敲门’”(《中年夫妻》)。李若惭愧地对儿女说:“宝贝,现实有很多阶梯/把我们相距两地/我也常常问自己/是什么不让我们在一起”(《宝贝,对不起》)。应该说,这样的北漂体验以一种集体的残忍方式触动了每个人的内心柔软之处。
北漂诗人杨泽西在《苦难》中写道:“当父亲谈及因此病突然死亡的同伴时/建筑工人、服务员、农民工、搬运工⋯⋯/这三十多年来陪父亲一同受苦受难的称号无一幸免/都随着父亲的一声‘老了’而一并逝去”。左安军献给《父亲的诗篇》中写道:“现在父亲头发稀疏,两眼疲惫/我却不能代替他老去/有一些父亲在我体内尘封但我们素未谋面/作为他们的遗物我将被重新分配。”而三四(崔庆凯)《父亲》则写着:“日子没有边界,日子是宇宙/和加粗的历史/你的一辈子,是月光硌疼了脚背/记忆深处供着一把刀子。”更要看到,祁国在《祭父》中写的那句:“我拿起电话/没拨任何号码/轻轻喊了一声爸爸。”在这里,一方面,这一声轻声呼喊,正是一代代现时寻梦的北漂人的心声,真情意切又感人肺腑。既打开了北漂人孤独密闭的心灵,又产生了个人/群体的情感和身份认同;另一方面,这种内在情感与生存体验的对接,并不断地在自我之中将情感的阀门敞开,很自然成为北漂诗人创作的精神源泉。这也是北漂者对漂泊命运的一种反抗。
2018年。

作者简介:
陈进武,男,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兼秘书长、湖南大学中国全民阅读研究中心研究员、《江苏区域文学研究》副主编。入选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等。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出版著作1部,主持省部或市厅级项目多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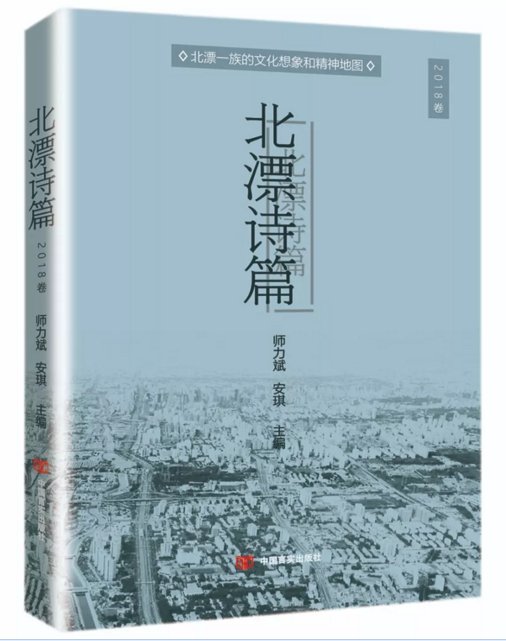
注:本文为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期文学批评的人性话语研究”(2016SJD750005)与江苏教育科学研究院2015年度博士专项(JSNU2015BZ24)成果。本文收入《北漂诗篇》2018年卷,师力斌、安琪,主编,中国言实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北漂诗篇》2017、2018、2019卷各大网站有售。亦可点击阅读原文直接购买。
作者:陈进武
来源:作家网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MDY5NDU3Mw==&mid=2247491420&idx=1&sn=e6d5caa24b92949ba985cef6c0c0d9f4&chksm=fa4cb79ecd3b3e88c81289436c3474d53b2a3421250fd683216fa36963f97c623619ba8a43cc&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76908885199&sharer_shareid=614c27d356f5211ee6b595b7918f01b5&exportkey=A6%2FIrT%2B%2FFXApo2%2BJRL7f4Js%3D&pass_ticket=N%2F%2BMS6J%2FbcGcLm%2BaEY5IkhXQOriZX8Ed1paYqHCNneX4yr7ons8fj%2BiXqIlDTK%2B%2F#rd


 纯贵坊酒业
纯贵坊酒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