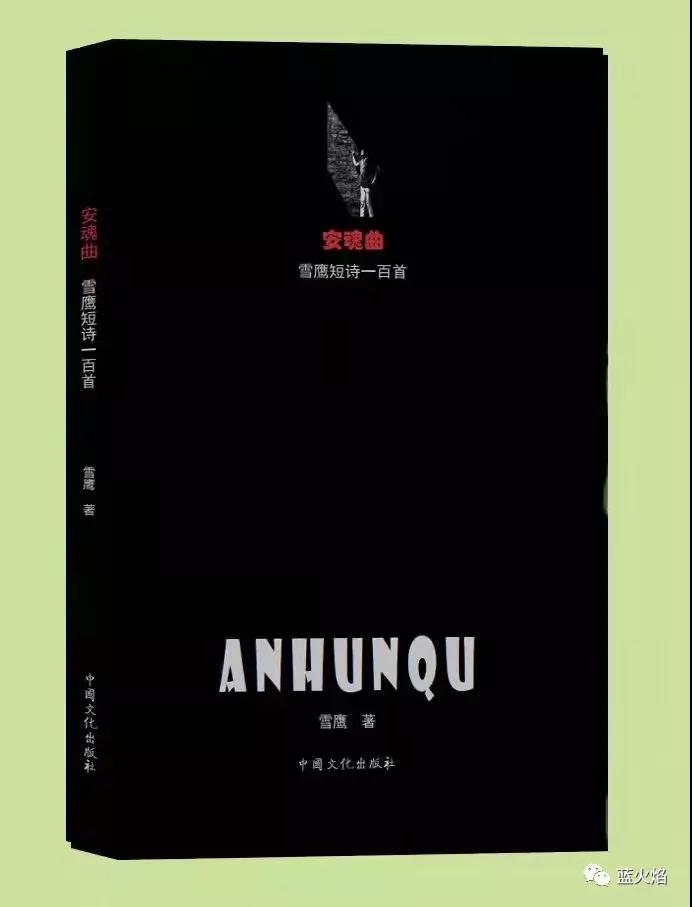
雪鹰诗歌点评专辑(23位诗人、评论家最新评论)
当代著名诗人、评论家百定安 陈先发 戴潍娜 方文竹 宫白云 海男 胡弦 敬笃 罗振亚 李樯 李云 刘斌 刘川 梁晓明 林荣 马永波 沙马 汤养宗 汪剑平 汪剑钊 杨四平 赵思运 张德明(按姓氏拼音排序)等,23位诗人、评论家对雪鹰诗歌倾情点评。
雪鹰新诗集《安魂曲》
评论专辑——
雪鹰的诗以前给我的印象是装在布袋里的锥子。他经常喜欢使用铁、鹰、刀、乌鸦一类的意象为自己的思想塑形(正如他使用的笔名”雪鹰“)。以我多年的阅读经验,一个人诗里簇集的某种(某类)意象,正是散落于诗中的意义密码(也可称之为“词汇学线索”)。久而久之,就会成为一种集合的象征物。然而,读完《安魂曲》,我们却感到,雪鹰在一直提醒我们,在硬度意象之外,完全可以以另一种语态表达刚性、理智以及思想的深度,传统的咏物与情景交融之法并不过时,思想完全有可能通过正确的修辞,将之建立在意象与叙述之上,从而不至于突破诗人自己所说的诗的底线:要有“回味”。思想绞合意象,与单纯的思想绞合思想,正是诗与非诗的分界之一。
——百定安 诗人、评论家(选自《诗歌是对“在境”的诗化处理:从雪鹰诗集<安魂曲>展开》,原文附后)
雪鹰是生于淮水之滨的一个诗歌莽汉,近年来为操持诗刊或举办跨区域的诗学活动,四方颠簸,为此吞食的各类委屈必不会少。与此形象相映成趣的是,他在创作中也力图展现一种曲折、回旋的审美倾向,在同时熟知他的生活与文字的朋友看来,也算件颇有意味的事情吧。
——陈先发 诗人、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安徽省文联主席
雪鹰的诗中,那些镌刻的文化记忆的“词”一粒粒像雪一样落下来。正义之血和现世之泥在胸怀中激荡,撕咬,较量。诗人抱着最初的真挚,写出宜古宜今的好诗——古典情韵内化中,又有一份现代的兴奋和冒险。雪鹰写诗,犹如“抱沙而沉”,始终用那些极其精微却分量沉重的词,去辨析世界的清浊。
—— 戴潍娜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新诗形式在雪鹰的手上成熟起来,回荡着古典与现代的交响。对于雪鹰来说,诗歌是一个巨大而神秘的容器,自我与世界、天地神人的全息性因此吐纳不息,内蕴丰厚。同时,对于世界万物,以诗赋形而终归心灵,体现出诗人超众的表达的繁殖力。可谓当代汉语诗歌地形图上一道弥足珍贵的风景。
——方文竹 诗人、评论家、《中国诗刊》《长淮诗典》编委
雪鹰的新诗集《安魂曲》共分五辑:在江南,纯色,折叠,真相,刀锋。分别体现出他诗歌的五种元素:浪漫、纯粹、深邃、力量,锐利。他在行走中开阔自己的视野,“心里喜欢,就张开笑脸”;在万事万物中安放自己的心灵,“词语里有清晰的风向”;在现实与历史的长河中穿梭与思虑,“与黑夜达成共识”;在日常中摸爬滚打、揭示、披露与批判,真理的寻求过程更“需要一种仪式/安顿灵魂”,而刀锋实际上是诗人把现实与生命切入更深的深处,刀锋下的悲欣交集像一道道裸露的伤口,但诗人仍是“自由的植被”,“每一寸肌肤”保持“永不消逝的青绿”。总之雪鹰的这部《安魂曲》是生长在现实主义根基上的诗歌集,既是他对社会人生行走思索的根本感受与真相探求,也是对自己灵魂的找寻和心灵抚慰。“安魂”一词囊括了他所有的心曲,在“安魂”中万物长存,无生无死,它给予生命本身的是一种内在的信任与热爱。他对现实的反映,不预设,不强调,不做所谓的铺垫,自然呈现中清晰地触及事物或现实的本质。他敏锐的反应使那些转瞬即逝的东西无处逃遁,瞬间现形,表现出他洞察世界与掌控语言的不凡和雄心。他使自身与万物合一,骨子里的悲悯情结旨在恢复对现实的关怀与自身生存的守护,诗歌中的多重承载布满鲜活深厚的能量。《安魂曲》将现实、生命、人生的种种境遇全都包含在内,它奏响的是浪漫、情怀、悲悯、担当、启悟的交响。
——宫白云 诗人、评论家、中国诗歌流派网副总编、《长淮诗典》编委
雪鹰的短诗百首,写于不同时间,带着一个诗人的命题,去考证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书为《安魂曲》,在变幻无穷的语言面前,时态就像旋律,忽儿汹涌,忽儿平静。唯有语言可以让诗人寻找到安魂之乡。
——海男 诗人、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一个书写生活的人,仿佛很自然地写出了丰富性。也许是写作在拓展他的人生,目击成象,发而为诗,分行,分出了语言另外的触觉,并进而辨认外在于现实的自己。雪鹰正是这样的诗人,他是温和的,也是锋利的,他是质朴的,也是敏锐的。我向在他诗歌里相遇的另一个雪鹰致意。
——胡弦 诗人、学者、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扬子江诗刊》主编
长期以来我都在阅读雪鹰的诗歌,从早期的凌厉、锋芒到今日的厚朴、稳健,能看出一个诗人的变化,也能看出一个人的心理转向。毋庸讳言,《安魂曲》证明雪鹰的诗已经形成了“近期风格”。他有自己的诗学信仰和追求,总是在不断地探索中,获悉某些未知的事物,藉此来承载其“内心世界”。他尝试着改变词语带来的固化思维,磨平昔日的棱角,以“圆润”的姿态,重新找回汉语的气质,打开了诗的方便之门。
——敬笃 诗人、评论家、文学博士在读(选自《风格的转向与无限的可能
》,原文附后)
雪鹰是方向感极强的自觉写作的诗人,他在延续中国诗歌的“载道”传统、讲究精神担当的同时,更坚守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穆木天、梁宗岱等人倡导的“纯诗”主张,注重艺术品位,诗性与情怀兼具的文本,人诗一体,情思和技术共生,在当代诗歌史的版图上留下了不可忽视的深刻印痕。
——罗振亚 南开大学穆旦诗歌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雪鹰的诗深入山河,土地,草木的内部,从中打开万物与诗人隐秘而忧伤的联系。他以邻水而立的游子姿态,用词语巧妙缝合了生活,理想与人世蹉跎带给心灵的滋养,“以寂静与沉思相互沟通”的方式,完成着一个孤独赤子的抒情。
——李樯 诗人、小说家、《青春》主编
显然诗人雪鹰先生在蜕变,我说的是他的思想和诗艺,这来自我对他的新作《安魂曲》的研读,他的思想性变得要为深邃、犀利,诗艺变得更加成熟、纯正,有了成为一位大诗家的显象和应有的文本气质。
《安魂曲》在我读来有五个异质的艺术特色,即:一是多姿多变的形式感呈现,他有编年史诗体(2016一2020年)、社科类诗体、史记类诗体等,这些组诗给人既有新颖多变之美,又有个体矗立之势。使诗集的诗歌各自为阵,各自为战,各自有自己应有的外在冲击力和内在差异感。让读者每每读来如步入他诗歌的后花园,每朵花是不一样的,每首诗的是各露各自的惊艳。而这种多变的形式感又很体贴的为每个主题揭示服务着,没有无端的搞怪卖萌,取宠与诗坛的流俗。二是从对现实诗性塑造和发现中,不忘其对历史经验的钓沉回望的启示,和异域人们生存和意识的渗透和影响。在他诸多诗歌里,他总是能机智的从现实中发现历史,用历史的过往功过得失照应当下,启发当下,并反之,以当下反衬历史和过往,发出呐喊和叹喟,同时,他还从中国当下人普遍精神经验呈述时,不忘对异域他国人们精神经验的对照和比较,这种在三至四维的多向度的交叉写作,使其诗文本有了复合之美和复调构筑 。三是其诗文本的中强烈表现的批判性,他用一个思想者清醒之思、勇敢之心,无畏之笔,用诗的分行文字,既写出对假丑恶的抨击,也写出对专制无人性的声讨的檄文,更写出对体制和独裁者的批判。他的诗非同寻常的一般性抒情诗,是有战斗力,冲撞力,破坏力的诗,是有钙质有重量有骨感的诗。四是诗歌的智慧语词呈现,他喜于捕捉平常象里的诗意,又有着对这种诗意独特呈现的技法。比如,“茶”,这个普通具象到了他笔下却表现为揭示爱情和人生遭际的情感表达的一个介子或道具。“恋爱时,那是一口浓的/结婚了吗,喝一杯是淡的/离了呢,咽一口昨日的”。这杯茶水的浓淡冷暖的演变其实是人生之爱的哗变。五是他的诗歌有着雄极、阳刚的基调,有着血性贲张的诗风。他的诗中有侠气和书生负剑走天涯的果敢和绝决。他的诗让我感到在读边塞诗和李白、元稹的《侠客行》。这样的诗读来有借他者之语,浇自己心中块垒之快感,这样阳刚之诗的出现难得可贵,因为当下诗坛的诗作不少诗人的精神是被阉割的人的状态,他们在写着无个性、无操守的诗,诗调是不阴不阳,是捏着嗓子说话的,是假模假样的做人作诗的,甚为可怜和恶心。雪鹰诗的出现是对此现象的一种反动及批评,也是匡正诗风的一种切实的校正与修正。
雪鹰说:诗是哑语。我同感,诗与禅一样不可言。就乱侃到此,打住!
——李云 诗人、评论家、《诗歌月刊》主编、安徽省作协秘书长
诗人雪鹰多年来一直坚持“底线写作”。什么是雪鹰所说的“底线写作”?从我的跟踪阅读的经验看,主要指诗歌创作过程中两个方面的坚持或自律。一是坚决不写趋炎附势、无病呻吟、言不由衷、歌功颂德的文字,二是不写没有创作冲动、没有审美感觉、没有诗歌韵味或形式创新的文字。读雪鹰的诗歌,能真切感受到一个时代的痛苦、忧伤、焦虑与苦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情绪或感触,不是浮在情绪波动的表层,也不是借助特殊的行业或阶层那样一种类型化叙事,更不是找不到对应物的言语漂移或陌生化的绵延,而是源自雪鹰真实的生存,源自他一直真实而不屈地活在这个社会真正的底层,源自这种真实而几乎无望的生存赠予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源自这种生存教给他独立而深刻的思考、敏锐而犀利的观察和推己及人的巨大的悲悯与哀戚,以及不甘沉沦的内心的撕裂与奔突,源自这一切使得他和一种独属于他的诗歌语言得以完成美的邂逅与纠缠。因此,在他的诗中,你能读到沉郁顿挫,又能读到郁勃激越,同时还能读到哀愤悲凉。在他的诗中,一个时代的雪崩与一个人内心的孤寒互为映照,而卑微的个体的歌声又分明传达出某种群体的沉默与沉默中的倔强。雪鹰诗写的厚重与复杂还在于,他诗中强大的解构力量,那种怀疑精神与超越品质,那种不为权威与陈见所限的自由胸襟和开阔的视野,以及他对诗的言语可能性的无止境的探险与开拓,如此等等都使得他的诗呈现出有别于整个当下诗坛的气象与格局。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阅读雪鹰的诗决不能与他的“底线写作”理念相分离,因为这与其说是他的诗学理念,毋宁说是他的人生信仰,雪鹰的诗与人就是如此罕见地达到了高度的統一。正如列维納斯说的那样,我们不能把接收到的信息与作为必要的对话者的脸分开。实际的阅读情形将告诉每个读诗者,雪鹰的诗正是他最生动最真实的面容。
——刘斌 诗人、评论家、长淮诗社副社长、《长淮诗典》副主编
雪鹰的诗在日常的物象中建立思考、批判、诗意的多重价值,他能够超越一般性的意象建构,从而进入深层次的、通过小切口直击现实的能力;雪鹰的诗突出个人语言方式与表达角度,使他的诗时而澄明、时而缠绕、时而犀利、时而温存,具有着复杂性与丰富性。雪鹰的诗咀嚼生活、体悟存在,并饱含质问与反省,具有别具一格的人文气息。
——刘川 诗人、评论家、《诗潮》主编
雪鹰的诗歌写的干净,遣词造句都没有故意粉饰与形容的夸张和繁琐,显得很是简洁和准确。这一百首短诗命名为《安魂曲》,从江南写到色彩、写到地域与历史,从虚无到现实,从政治到性,到凌厉的刀锋,几乎是一部个人生命的精神历史与领略的经历,眼光清晰又保持着一种平视与客观的冷静,这些,都显出了雪鹰的诗歌写作已经到达了一种成熟的高度,他已经在诗歌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梁晓明 中国先锋诗歌代表诗人、《北回归线》诗刊创办者
雪鹰说:“这种在“艺术性”与“思想性”之间的拔河状态,是现代诗诞生以来的常态,原生态。”是的,对于诗,他有着客观理性的认知和判断。正是在这一理念的引导下,他的作品无限趋近于二者之间的平衡,用心的读者能够从他的字里行间,品味体悟到其作品的严肃性。用事实说话,用文字宣誓,雪鹰的诗集《安魂曲》再次证明,他做到了他所提倡的诗歌写作精神。他坚持认为:在把追求诗性放在第一的同时,还要承继中国文人的传统,写诗性与情怀兼具的诗。我尤其赞叹他的这一观点,这是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
——林荣 诗人、评论家、《中国诗刊》编委(选自《“原住民,我向你报到”
》,原文附后。)
雪鹰的诗中总有着一种淡淡的忧郁,他总是在与一些事物的不期而遇中,敞开自己的存在之思。在这种相遇中,又仿佛
总是有一些隔膜的东西存在,这也许就是其诗中忧郁的来源。探求存在真相的渴求,与人世间种种莫名力量的纠葛,
使得诗人的主体姿态摇曳生姿,我们很难用相对固定的观照范式去框定,这是雪鹰诗歌迷离恍惚又魅人的地方。
在人世遍历苦辛的经验中生发出的思想,时时又回转,在诗人更为隐秘的心灵图景中生成自身的另一重形象。
作为读者和朋友,我更希望这种情境仅存于诗中,这也许是诗人所能获得的最大的福分了
——马永波 诗人、翻译家、评论家、南京理工大学教授
阅读雪鹰的诗歌后,感觉有四个特色:一是雪鹰的诗,避免了“泛口语化”和平面化写作,而是将词语带入了事物的深度,继而挖掘、发现、揭示出新的存在,这种存在就是诗人内心世界的理想,或者本质性的呈现词与物的关系,通过这种揭示,不断接近世界存在的真相。这构成了诗人写作的重要途径。二是雪鹰诗歌中的“物象”在自然的审美中转化为诗性的“意象”。诗人注重词语与词语之间的内在关系,关注它们之间的隐喻、暗示和指向,然后再给予合理的运用,在修辞中艺术的显现出诗意的存在,这构成了诗人写作中多元化的风格。
三是雪鹰的诗在形象中呈现场面,在场面中突出场景,在场景中构筑诗意的栖住地,进而深化了诗意是境界,丰富, 内在意蕴,强化了阅读上的张力。诗人善于将语言进入思想渗透,再赋予其揭示事物存在的含义,这构成了诗人作品思想上的美学意义。四是雪鹰的诗注重呈现身边的现实事物,揭示人与存在的关系,人在现实中的生存境遇,有一定的时代感。同时他在自身对现实、语言、事物等的体验中,赋予诗歌内在的丰富性,强化了诗歌的表现力,以及语言在诗歌中的张力,给读者带来了阅读上的艺术感染力、
——沙马 诗人、评论家、《安徽诗人》编委
这部取名为《安魂曲》的诗集,安顿了诗人对自己心灵的归墟及江南这片精神虚土的关怀。在诗集里雪鹰把不但“江南”一词写出了少有的有风骨且有高逸与博雅的文义,更把儿女情,天地心这类自古在文人心胸中缠绵萦绕的苍茫人事,写出了个人的眼界,喜好,和判断。情怀高迈而行文真挚,是我喜爱的那种江南才士善用才识点拨与激活文理与事像的手段。何谓“江南文气”,诗人雪鹰笔下的这种文化精神与文笔气质,为人们筑起了一道值得仰视的诗意风景。
——汤养宗 诗人、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雪鹰的诗是关于人的自由与尊严的哲学思考。
在这个精神碎片化的时代,他借用丰富的意象,敏锐的视角,深刻的领悟加以解构和重组,呈现出一种多元的,复杂而清晰的文化现象。
雪鹰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他的格局决定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他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遗世独立的精神。作品涉及心灵和道德良心,涉及苦痛的人生,死亡的终极秘密,涉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他的诗歌即是写给当代的,更是留给历史的。
关于诗歌,他如是说:“你可以不叫它诗,可以叫它哑语。这个年代里,鸵鸟很多,有人用费拉骂人”
关于生存学,他如是说:“在常州,我潜伏于九楼,曾连续三天不出门,唯一的动静,是微信里的冒泡”
关于安魂曲,他如是说:“我们需要,这个曲子,需要安放你的亡魂,我的游魂”
最后索尔仁尼琴如是说:“文学,如果不能成为当代社会的呼吸,不敢传达那个社会的痛苦与恐惧,不能对威胁着道德和社会的危险及时发出警告——这样的文学是不配成为文学的。”
——汪剑平 诗人、独立写作者、电视台编导
雪鹰是一名热心公益,对社会有道义担当、对诗有审美追求的诗人。他最新的诗集《安魂曲》收录了100首作品,遣词自如,视野开阔,题材广泛,同时也散发着强烈的南方气息,仿佛有某种水性之灵在流动。它们“荡漾”、“涌动”、“游移”,诗人藉此最终向我们呈现了一颗被语言之水淘洗过的灵魂。
——汪剑钊 诗人、翻译家、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导
雪鹰的诗硬朗、冷峻,又不失暖色、柔情,有种向死而生的果决与力量。
——杨四平 诗人、评论家、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安魂曲——雪鹰短诗100首》充满了鲜明的历史反思意识和锋锐的现实批判精神,诗意成为灵魂的安魂曲,缓释着苦难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丝毫没有温情主义的陈词。雪鹰的诗克服了繁复的修辞,以富有转折色彩的诗语,营造峭拔的诗意。从淮水到江南,他抒写现实的捶心之痛和颓败的时代预言。他在“下坠的力的图式”中,深入黑夜,以良知之光去烛照真相。他的历史文化语码,犹如乌鸦的哑语,是时代的谶语,偈语,祷词,墓志铭,也是诗人的精神誓词。他在柔靡的江南诗风中,挺拔出一种“有骨的江南”。
——赵思运 诗人、评论家、浙江传媒大学文学院教授
雪鹰的诗歌所呈现的宽阔的观照视野和繁复的精神指数,实在远超于普通诗人。这里既有地域性风物的写照,也有人文化景观的描摹,还有耳之所听目之所观身体之所触的诸多具体事物的凝望与思忖。诗人的词汇量极为丰富,思维的锐度和理性的锋芒也尤其尖利,不少诗歌中都显示出开阔的生命气象,散发着哲思的炫目光芒,体现着某种知性诗学的精神维度。在雪鹰眼中,世间万物皆存诗意,似乎没有什么不能纳入诗性言说,我最欣赏他写下的《学科系列》组诗,光看这些诗题目:“传播学”“政治学”“动物学”“植物学”“性学”“生存学”“气象学”“人类学”“修辞学”,就能看出特别的情味和异趣,恐非市面流行那些“小情绪”“小感受”之诗所能比拟。正是有那些独特性诗章的存在,雪鹰的诗才塑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美学图式,彰显着某种难能可贵的艺术辨识度和个人化诗学特征。
——张德明 岭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南方诗歌研究中心主任
附三篇长文 ——
诗歌是对“在境”的诗化处理:从雪鹰诗集《安魂曲》展开
文/百定安
将自己的诗集取名《安魂曲》,雪鹰一定有自己的考量。它取自莫扎特,但又超越单纯用于超度亡灵的弥撒曲。这在其中的一首同名诗中已经有所显示。《安魂曲》一诗的时间背景,是“夜不是夜/昼不是昼”的“四点”。这个时间点颇有某种象征意味。而在“四点”聆听《安魂曲》,不仅是“安放你的亡魂”,也是安放“我的游魂”。这种游移性,表明精神常常展现出一种无枝可依的乌鹊的状态。它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如何区分一个人”身体在场“的”孤单“与精神游离于”群众“的“孤独”的问题。
当下诗歌的诸多严重分化,表面上看是修辞,实则是一种写作立场。它们不仅分化为米兰·昆德拉所说的“用美丽、动人的语言表达固有观念的愚蠢”的“媚俗”,也分化出无数像法国哲学家阿隆指出的那种精明世故、看似介入的“局外人”;不仅分化出许多“两面人”的表达方式——与世俗同流合污而又以反对者的口吻表达一次——,也分化出直面现实然而意气用事、观念统领的无修辞写作。诗歌生态在波诡云谲的诗歌观念与波澜汹涌的诗歌行动中被大肆污化。
“于是
缄默,便成了传统智慧
成了君子,或者蝉们
延喘的法宝。不知春风过后
六月里,是否
还有争鸣的声音”。
雪鹰的诗提供的始终是一种生存与精神的“在境”。但如何以诗的方式处理物象与人文之境,则需要诸多诗艺内外的能力。从其诗歌中,我们感受到了某种正直的力量,但正如许多直面现实的诗人一样,当下的这一类诗歌,不得不进入一种隐喻(曲喻)时代。一个诗人,如果摈弃使用明喻的抒情,那就只能进入隐性的叙述。在此,我想说的是,“笔墨当随时代”,不是追随时代,而仅仅指向我们与时代处于同一个时刻,然而并不一定要与时代同行。如果仅仅强调跟随时代,诗人的作品是可疑的,因为那样的“时代”是未被过滤、未被思考、未被沉淀的所谓“时代”。引用苏格拉底的说法:“未经思考的人生不值得一过”,同样,未经过滤与思考的诗歌,很可能由于缺乏本质的“真实”而不值一读。它们不过是堆砌起来的一堆原木。
艾略特在《玄学派诗人》一文中,将现代诗歌语言的艰涩归之于我们的”文明涵容着如此巨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而”诗人可能变得不得不艰涩“。也许艾略特是对的,也许我们可以将诗人对现实的理解力,理解为对现实的过滤与辨析能力,因而语言在抽象化中变得简括(正如古希腊人发明了数学的抽象一样),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因此不做出任何对于清晰写作的努力。我们读到的许多”艰涩“的诗歌,不少并非因为必需,而仅仅是因为自身的语焉不详而人为造成的艰涩。总之,过滤就是选择,就是重构,缺乏了这些,那些所谓”看得见"的事物,就不过是进入傻瓜相机、未经选择的一个原始画面。事实本身是没有诗意的,它具有直接、粗糙和原生的特征,而只有通过高超的叙述能力,才能提炼出事实中存在的诗意。
在《弧度》一诗中,大致可以认出雪鹰对于诗写现实的态度:“需要一种弧度/然后弹起”。“弧度”在此表达的是一种技术而非态度,其目的在于更加有力的“弹起”。这种“弧度”是由于两种无时不在的冲突造成的弯曲。它取决于诗人对“在境”的认识,从而在诗中对此进行重新“个人命名”。雪鹰的诗,有一种底色,即更加倾向于某种黑暗意识:
“你的睡眠,
你的眼里有同样的黑暗”
正如诗人在《转换》中所展示的,阿Q的时代过去了,但阿Q却一直活在我们中间,或许,我们自身——在身心两方面——脑后仍挂着阿Q的一根辫子。在这一点上,诗人对于社会进化的效果始终是持怀疑态度的。
然而这种黑暗意识,并不像有些人那样单纯以诗的色差辨别诗人对于生活是否热情,从而轻率地将其归入某种尼采式的悲观主义,反倒更加充满赤子之心。诗人似乎更像是站在暗处而心中藏着太阳画片的人。他们有不安、惶惑甚至惊恐的时刻,但却从不认为人会永久陷入至暗的时刻。
“而对于坐在黑暗中的人
有一颗星就足够了”
诗人的写作,不过是种种矛盾之间的相互对峙、彼此拔河罢了。诗歌亦不过是语言与精神撞击时制造的修辞罢了。具体于个人,则因品质不同——例如铁与铁,会爆发出铁铺里迸裂的火星,而铁器钻木,则只是冒烟——而显示出不同的效果。正如诗人在《左右》一诗中所写的
一生中,不知道给自己
出了多少难题“
左边在说服右,而右边在抵抗着左。诗人不过是在艰难地”从满脑的线头里“,试验性地“想捋出一汪清水”。这单纯的愿望,却“磨砺了我,整整一生”。诗,即磨砺,它的上一句是磨刀石,而下一句很可能就是刀锋。这也是现代汉诗的平仄之法。又或许,像本诗集的名字一样,希望通过艺术手段,使动荡归于宁静,像一对恋人的执手相握,五个手指是一首五言绝句、两只手写着同题之诗那般,最终达致某种和谐。
雪鹰的诗以前给我的印象是装在布袋里的锥子。他经常喜欢使用铁、鹰、刀、乌鸦一类的意象为自己的思想塑形(正如他使用的笔名”雪鹰“)。以我多年的阅读经验,一个人诗里簇集的某种(某类)意象,正是散落于诗中的意义密码(也可称之为“词汇学线索”)。久而久之,就会成为一种集合的象征物。然而,读完《安魂曲》,我们却感到,雪鹰在一直提醒我们,在硬度意象之外,完全可以以另一种语态表达刚性、理智以及思想的深度,传统的咏物与情景交融之法并不过时,思想完全有可能通过正确的修辞,将之建立在意象与叙述之上,从而不至于突破诗人自己所说的诗的底线:要有“回味”。思想绞合意象,与单纯的思想绞合思想,正是诗与非诗的分界之一。
我曾经在《作为持续性写作的诗歌》一文中,提及一个观点:一个诗人欲要保持可持续写作的能力,就必须置身于现实之中,并找到诗歌与现实的对立关系(其次是注意防范修辞力的弱化与重蹈),如同希尼夸奖奥登那样,“奥登给他那个时代的英语写作导入了一种对当代事务的关注,从前那是被忽视的。”艺术的庄重感在于其有良心的要求。我们不能不切实际地去幻想设定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存在,问题在于发现与表达。在这个意义上看待雪鹰之诗,我们就可以怀着坚定而欣悦的期待。
2021,12,29
“原住民,我向你报到”
——雪鹰诗集《安魂曲》中的传统文化精神初探
文/林荣
诗人雪鹰把他的新诗集命名为《安魂曲》,这是诗集中一首诗的题目。我想,这也是他对自己郑重提出的生命要求:正心才能吟出安魂曲。人心正,魂方安。我把手表放在耳畔咔,咔,咔,咔……这是你的脚步声?走过的人,被我系在这根针上不时回头看线的长度却没能搬回一秒,曾经的过去我终于明白,你早已走到了我的手表的外面——雪鹰的诗《手表内外》
岁月无情。当一个诗人清晰而深刻地意识到时间走到了“手表的外面”,他理应为自己的清醒和觉悟而深感庆幸。是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意识到这一点,也不是谁都能放下我执而抵达空性慧的高度。当一个人能够抵达这种生命境界,必然得益于他所持守的正知、正见、正思维,得益于深植在灵魂深处的文化根脉,得益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
博大精深的《易经》是中华古代先民的智慧结晶,后来的儒家、道家等思想都受其影响。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经典,《易经》不可不读。凡是用心研读者都会从中受益,哪怕从中仅仅有所小得,现实生活也会有大受益。诗集《安魂曲》第四辑中的《2016》《2017》《2018》《2019》等诗作,可明显看出雪鹰从《易经》中汲取到的智慧和营养。这些诗作能由诗人之悟开启读者之悟,引导读者经由思辨,看破表相,放下执念,回归到本真之心。诗人写到:“卦象都在心里/内行人从面部可以解锁/可以断出大势与走向”。寒来暑往,春夏秋冬,一路风雨走来,现实生活带给每个人酸甜苦辣咸的生命况味。人非圣贤,有几人能做到不为外境所动,个中滋味自会体现在人的面部表情上。诗人以年号为题的这一组诗,以简洁且富有诗性的语言写出了自己的观察和判断,写出了普适性,这是素养,是能力,是诗人艺术修为和文化底蕴的表现。鸟来了,人来了村庄来了,你始终在这里铺了砖,就扎进砖缝砌了石,根就伸进石底墙上也是家,小巷更幽静岁月的长卷,你用青绿记录细致入微。坛头有了村落你就是最老的村民 原住民,我向你报到——雪鹰的诗《坛头的苔藓》
这首诗被雪鹰收录在诗集《安魂曲》中,是我很喜欢的一首诗。“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不为外境所动的苔藓,无欲无求的苔藓,淡泊自处的苔藓,随缘不攀缘的苔藓。人若如苔,则堪称具有甚高的修为了。诗的结尾写到了“最老的村民”、“原住民”,增加了这首诗的厚度,寓意着不可或缺的根性。最后一行更是点亮了全诗,诗人向一直静默坚守的“苔藓”报到,其实也是在向自己素朴本真的初心报到。专注持守,初心不改。而这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
成其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也是人文主义的图谱和要素。通读雪鹰诗集《安魂曲》,看得出诗人深得传统文化的要领,他的诸多作品都彰显出他骨子里的人文主义情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动力。天人合一、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和内涵。理性精神、自由精神、求实精神、应变精神构。我最佩服的一个名词炉中火红的液体无人敢碰的柔软血性的柔软,比硬还硬离开火的铁用一身骨头,承担火的硬度千年不变——雪鹰的诗《铁》
“铁”,是诗人最佩服的一个名词。铁,百炼成钢。铁,有着无人敢碰的柔软;铁,血性的柔软比硬还硬。
这是诗人的自画像,也是自勉词;这是风骨,也是担当。这让人想起了魏晋名士,想起了“竹林七贤。”
主张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是中华传统文化理性精神的根本。一个优秀诗人的理性精神常常会有意无意地反映在其诗作中。一个理性的诗人不会把人从人际关系中孤立出来,也不会把人同自然对立起来。关于这一点,我个人认为雪鹰的《我是自由的植被》一诗是很好的、有力的证明。诗人写到:“我知道/我是自由的植被/是大山深处,静静生长的/香樟,红豆杉,抑或/山涧里的菖蒲,苔藓”, “我被天覆盖/又覆盖大地,覆盖你/包括视线,和每一寸肌肤/我保持自己的多样性/丰富性,保持我/永不消逝的青绿”。这些诗句是原则,是底线,也是包容和圆融,整首诗舒朗、大气、开阔,胸襟自现。
自由之精神、独立之品格。酷爱自由是诗人的特质。在《花的规则》一诗中,雪鹰写到“花有花的开法”,“花想开/她就开了。依着丑陋的/光秃秃的枯枝,在阳光下/风雨中,甚至苦寒里//心里喜欢,就张开笑脸”。这些诗句并不难理解,但却经得起一读再读,也愿意一读再读,为什么?因为它们弥漫着自由自在的气息!传递出来的是一种本真率性的气场!花的规则不是别的,是“心里喜欢,就张开笑脸。”不怕苦寒风雨,想开就开的花朵,是自由的化身,是自由精神的写照。
求实精神,强调知人论世,反对生而知之。同时,也意味着对于现实的关注,意味着对于正义的推崇。雪鹰的很多诗都是现实主义作品,他的笔下鲜有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他的关注点就在触手可及的人事物上。他的诗源自现实生活,不离对于人性的洞察,对于社会人生的观照。他的笔锋相当犀利,文辞冷峻超拔。有一定社会阅历和生命经验的人,从他的诗作中可以读到很多熟悉的场景和内容,会被一种正直的秉性所吸引。
在这里,我想说的还有一点:对于一个诗人而言,从诗歌艺术的角度看, “让诗说出那些只能经由诗才能说出的东西” (《中国诗刊》第十一期《月坛》栏目《“把诗当诗”与“鞭炮理论”》),这必然是出于对诗歌艺术的敬畏,对文字的敬畏。无疑,这也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求实精神。
以不变应万变。处变不惊,宠辱不惊,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精髓所在。雪鹰深得这一文化精髓的滋养。关于这一点,从他的《风不吹,就不是风了》一诗中,读者或可有所领略。“懂得这个道理/你就能懂得,五千年的/历史,是怎么来的//重复一个腔调,朝着/一个方向那是/信风。变着方向/时有时无,那是季风/那是阶段性的需要”。风,来无影去无踪;风,变幻莫测。诗人以“风”隐喻历史,隐喻世事……这首诗是诗人睿智的洞察力的结晶,昭示出来的是我自岿然不动的定力!若不是一个刚柔相济、能屈能伸者,如何能写得出这样灵慧的文字?!
雪鹰说:“这种在“艺术性”与“思想性”之间的拔河状态,是现代诗诞生以来的常态,原生态。”是的,对于诗,他有着客观理性的认知和判断。正是在这一理念的引导下,他的作品无限趋近于二者之间的平衡,用心的读者能够从他的字里行间,品味体悟到其作品的严肃性。用事实说话,用文字宣誓,雪鹰的诗集《安魂曲》再次证明,他做到了他所提倡的诗歌写作精神。他坚持认为:在把追求诗性放在第一的同时,还要承继中国文人的传统,写诗性与情怀兼具的诗。我尤其赞叹他的这一观点,这是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
行文至此, 正如雪鹰在诗中写到的那样,我的耳边仿佛也响起了一只手表“咔 咔 咔……”的声音,响起了一个诗人发自内心的声音:原住民,我向你报到!
——2021年12月27日晚
林荣,河北省枣强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出版诗集《攀到高处听月亮》等四部。认为写作首先是一种倾听,倾听自己,倾听那些发出光亮的事物;在一首诗中,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风格的转向与无限的可能
——雪鹰诗集《安魂曲》阅读札记
敬笃
长期以来我都在阅读雪鹰的诗歌,从早期的凌厉、锋芒到今日的厚朴、稳健,能看出一个诗人的变化,也能看出一个人的心理转向。毋庸讳言,《安魂曲》证明雪鹰的诗已经形成了“近期风格”。他有自己的诗学信仰和追求,总是在不断地探索中,获悉某些未知的事物,藉此来承载其“内心世界”。他尝试着改变词语带来的固化思维,磨平昔日的棱角,以“圆润”的姿态,重新找回汉语的气质,打开了诗的方便之门。
T.S.艾略特认为,“诚实的批评和敏锐的鉴赏不是针对诗人,而是针对诗歌而做出的。”从雪鹰的诗歌文本中,我看到了诗人的影子,但这种影子越来越不清晰,取而代之的是其诗的内核和“诗之本身”,这是走向成熟的诗。他的诗,较之从前,更加从容、自如,关涉的内容也更为广泛。
未成形的诗
有无数可能的意境
当初读你的时候
最渴望读到的是,今天这一节
但所有句子已经表明
当年闪烁的诗意
已被苍茫的岁月
消解
——(雪鹰《短诗一束10》)
他的思考,拒绝某些传统,走向诗的另一个敞开的界面,消解诗意贫乏时代的困惑。他意在从传统的经验中突围,将那些被格式化、类型化的诗消解掉,从而建构出一条数属于自己的“诗之道”,可能这条路很漫长,但雪鹰正在尝试以西西弗斯的方式,往前迈进。在我看来,雪鹰这种打破风格的诗,其实是在建立自己的另一种风格。
这个夏天,我总是陪着黑夜
度过一分一秒。我们以特殊方式聊天
以寂静与沉思相互沟通
你,讲述伸手不见五指的真理
和高居临下的黑暗,铁桶一样
盛满夜色,像波澜不惊的下水道
我将冥想的双目闭紧,在意识界
与你交流:讲述黑暗中美丽的林昭
我的姐姐,或姑姑,那颗最亮的星星的故事
你那有数的星光,是我永远
崇拜的,为正义赴死的灵魂。他们在天上看着
而那大块的黑夜,仍在努力掩饰,占据天空
卑鄙者早就拿到了通行证
而且还刻满了墓志铭,供桌上的泥像
依然压抑着冤魂。不知道到底
是圣人是伟人是小人,是救星是灾星是祸星
没有统一结论,我们以沉默
僵持。各守己见,相持不下
夜色越来越浓,星光微熹
我知道,你又要以下流的手段
制造云雾,屏避丑恶。但你无法遮挡星星的眼睛
下一步该如何交流?其实很简单
只要睁开黑色的眼睛,掀开一角
黎明就会讲述真相,我们有望达成共识
——(雪鹰《与黑夜达成共识》)
诗人延续北岛《回答》中的那句经典,“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在这里雪鹰却说,“卑鄙者早就拿到了通行证/而且还刻满了墓志铭,供桌上的泥像/依然压抑着冤魂。不知道到底”除了对经典的致敬之外,还有另一层意思,那纯粹的呐喊在当下已经无法适应,取而代之的是已经形成的“意识”,该如何表达才能恰切,成为了这一代诗人思考的核心命题。雪鹰以一个诗人的敏感,认领属于自己(个人主义)思想范畴的“黑夜”,至于如何达成一致、达成共识,这是一个运思的过程,也是一个作诗的过程,虽然在这里诗人给出了答案,但这个答案是开放的、不确定的。
《安魂曲》的章节安排,暗含着诗人的内在逻辑。在江南、纯色、折叠、真相、刀锋,五部分五种风格,层层递进,逐步深入,步步剥离出诗人的底色。他从具体的事物着笔,进而走向虚无的形而上哲思,获得真相之后,在独特地反思之中,他开始建构一套属于个体的精神话语,辅之以刀锋,来割开隐匿在现代社会和人心中令人作痛的“顽疾”。约翰斯顿曾这样认为,“现代人生存的最重要的事实是社会的空间差异,而不再是自然界的空间差异。”道出了现代社会的一种真实的生存之境,而雪鹰在尝试着从自然界空间内部寻找一种突破,这种突破不是工具理性的,而是诗意的,是自然的。他在这个陌生的、现代性的社会中,该如何安置自我,安置灵魂,成了一大难题。在隐蔽的词语中,诗人并没有听命于诗,而是努力对抗,力求从局限、逼仄的空间突破,只有这样才可能完成肉身与精神的双重超越。
今天,我终于找回
遗失于前世的身份,我的
天然属性,基因
骨子里的叶绿素,血液里
汩汩流淌的山泉
我终于透过层层遮蔽
看到了血,翠绿的
草木一色的血。我知道
我是自由的植被
是大山深处,静静生长的
香樟,红豆杉,抑或
山涧里的菖蒲,苔藓
我被天覆盖
又覆盖大地,覆盖你
包括视线,和每一寸肌肤
我保持自己的多样性
丰富性,保持我
永不消逝的青绿
或许,我只是
一块自由的石头
击水有声,落地生根
生硬,而棱角分明
但是,我始终被天覆盖
一生想突破无形的重压
而终究只能匍匐于大地
或曰拥抱,深陷于你噬骨的
诱惑,我的大地
山水,我的挚爱
——(雪鹰《我是自由的植被》)
或许在这个断裂的时代,人如何面对生存困境?是一个重要的命题。诗人应该如何书写这个时代?或赞歌、或直陈其事、或反思,怎样选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究竟是否真的洞悉了这个时代的内里。布莱希特认为,“以自己的经历来显示他的时代毫无价值。”那怎样显示他的时代才有价值呢?那就需要诗人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表达状态,以呈现他的时代。无疑,雪鹰也在探索,他用了这样一种表达,“我保持自己的多样性/丰富性,保持我/永不消逝的青绿”保持自我,坚持自我,以这样一种“不变”的态度,来面对世界的“变”与“不变”。
去庙里看看,那里
有神的模样,有信众的
颂词和抑扬的颂歌
有摇头摆尾,无骨的
蜈蚣
去江湖走走,不要担心
风雨飘在路上,夜
有夜的光,昼有昼的
黑。还要去史书里
转转,翻翻旧帐
看那些债主,如何
尸骨无存,欠债人却
烟火胜于鬼火,千年不绝
还应该听听歌,或者
放开嗓门吼几声
歌唱天亮,也歌唱天黑
甚至不日不夜的五更头
还要写几行字。做为
偈语,祷词,墓志铭
或者誓词。天黑后
要见证自己的姿态
蹲下可以,但绝不能
伤害膝盖,躺下可以
一定要眼望天空
趁天还没黑,一定还有
发亮的眼睛,看清
身边的面孔。或许
恶梦中你能认出几个
靠面具,慢慢醒来
——(雪鹰《趁天还没黑》)
怎么醒来?靠面具,还是靠眼睛。雪鹰是有答案的人,但诗中的问题,总是给我们更多地思考空间和答案的不唯一性。由是观之,雪鹰是一个有着理想情结的诗人,他渴望被理解,同时又不渴望被同构;他渴望找到一种个体情绪的抒发窗口,又不渴望被标签化;他渴望以自己的理想来完成对黑夜的书写,同时又不渴望黑夜被当成黑夜来肢解。所以他是矛盾的理想主义者,是有着双重人格的诗人。
从他的诗中,我们总能找到一条通往理想大门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他执著、自信、偏执,而又忧心忡忡,他似乎相信了现实,但又选择放弃现实,而朝向虚无,似乎只有在那里,他才会看到自己的精神之地。正是这样一种虚无之地,才让我们感知到诗人创造的那种无限可能性,正是这种无限可能性,给人一种着迷的直觉。
作为一把切割天空,切割思维的刀
犀利与光泽必不可少
黑是底色,融进去
你就彻底消失
疼痛,是你的存在
血,是明天的光亮
夜正在被你送走
却无法送走枪声,和受伤的灵魂
——(雪鹰《鹰》)
雪鹰写鹰,好像是在写自己,这受伤的灵魂何尝不是他自己?他的精神受困于思想的洞穴,受困于现代社会空间的逼仄,受困于自我意识的处境。鹰面对明天、面对枪、面对死亡,这也正是人所面临的问题。那么诗人所要做的就是将这些问题摆在明面上,供人类自己参考,鹰的困境是人类造成的,人类的精神困境同样也是人类自己造成的,该如何逃离黑暗、杀戮、死亡,这需要做进一步地深思。在这里雪鹰不再像从前那样歇斯底里、那样冲天怒喊,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压抑、低沉和隐忍,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摆脱悖谬与荒诞,才能摆脱晦暗的影子,回到光明的大道。
从雪鹰的《安魂曲》中,我愈发的确信——诗正在走向纯熟。他在现实与虚空之间,搭建一座词语的城堡,允许一切事物进入城堡之中,给每一个事物留足空间。他将那些归置的、刻画的、自然生成的诗意,摆在那里,等有缘人提取。这让我想起了罗兰·巴特的一句经典,“不是要你让我们相信你说的话,而是要你让我们相信你说这些话的决心。”雪鹰又何尝不是在这样做,他在自己所构造的诗中左右张望、窥探,在现代性的边缘不停地徘徊,在弥漫的情绪中踟躇,他没有让我们相信他的诗,而是相信了他诗中隐含的决心与勇气。
敬告:诗集《安魂曲》50元包邮,电话 19957951269
来源:长淮诗典
https://mp.weixin.qq.com/s/UpYbvqor3CQLsM9nQXc8eg


 纯贵坊酒业
纯贵坊酒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