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骇中的凝视
——谈作为一种现象的晓角
作者:赵卡
晓角出生在一个偏僻亦贫穷的小山村里,打小就饱尝了人世的艰辛,直到有天误闯入文学的天地,自此展开了她焕然一新却又处于不确定状态中的命运。晓角喜欢很多作家,尤为喜欢萧红,她喜欢萧红到了什么程度?举个例子,萧红小说里有一个未出世的孩子叫“晓角”,她的名字就取自那个未出世的孩子。乍听起来,有点残酷,有更多的暗示,却能激发灵感,还会给人一种血肉蓬勃的生命力启示。
2022年的第一期《草原》刊发了晓角的一组题为《瞧,这些人邻》散文,共5篇,包括《天上的大鱼》《雀大》《牛姐妹》《蚂蚱秋》《人邻》,那种未经深思熟虑却有着奇特的思维和很重的悲苦感一下就把我震惊了;这也有点像萧红,与现实平行的自传性文体意识非常强大。晓角的散文,包括她的诗和小说,句子很抒情,却都又富于直观性和重力感,属于主观主义那一路的;尤其是,以这5篇散文为例,你读后就会发现,她写的都是人类的邻居——小鱼、小鸟、牛、蚂蚱和猫等平常事物,但她以童年的代入视角发现了人邻之间非常紧张的关系(非诗意、情绪化倾向的),她仅仅是——如V.S.普里切特定义短篇为“路过时眼角所瞥到的”那一“瞥”而已,就瞥见了伤害的发生。晓角甚至还发展出了一套人邻之间相合又相悖的话语,事实上,她既重又钝的下笔是在寻求一种基于自身权利的心灵吁求,也就是说,她写的是自己,犹如感怀和咏物,但太绝望了——诸如这样的句子:“……还没立冬就这么冷,鱼怎么受得了,鱼会不会冷到哭泣?除了我没人知道。”(《天上的大鱼》)“那是一只鸟,很小,……身上颇有些肉,它灰灰的,丑丑的,眼神惊恐,发抖,在人手里挣扎,大声惨叫,像小孩子哭,很难听。”(《雀大》)“牛姐妹不仅耕地,还生犊,奶大了就被人卖掉,有时也会生死胎。”(《牛姐妹》)晓角在写一只蚂蚱的死亡时,细节逼真得令人发指,“……捉到了用柳条先狠抽几下,蚂蚱会心跳变重,瞳仁上翻,然后昏迷 ,也许它能感觉到痛? 昏死过去的蚂蚱放在阴凉处,五六分钟后会醒来,醒来时已经僵硬残疾,奄奄一息,但还会本能地想逃,用最后的力气跳一跳,蚂蚱很难死,就是再用柳条抽昏一次多等一会儿也还能再醒过来。后来我又想出一个新花样,先捉只无伤蚂蚱 ,折磨至半死, 再用树叶包住埋进泥土里,埋的地方做好标记,第二天抓只活蚂蚱,当着它面把死蚂蚱取出来给它看,活蚂蚱一时骇极,小的肢体会猛地僵住,一动不动,嘴会惊得张开。”(《蚂蚱秋》)在写到猫时,晓角又以超现实主义的比喻断定:“……这猫本不是猫,前世本是一个一生落魄,可能读过书,可能从过商,但都失败了最后漂泊到我们村里死去的人……”(《人邻》)
晓角是这一两年来被《草原》发现并发掘出来的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作者,她的生活经历限于篇幅,我在此不便赘言,只能简单谈她的写作。我前面说过,萧红是影响了晓角的作家之一,她们的作品风格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小说“散文化”、散文“诗化”,文本上给人一种感官丰饶的感觉。晓角在文体上是多面手,举凡小说、诗歌、散文甚至非虚构都不在话下,她尚不满20岁,却表现出了一种可怕的成熟,并且用这种可怕的成熟回应了生活的困境;
不言而喻,晓角的出现是当下文坛让人陌生、惊喜却又令我们措手不及的文学现象。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会出现晓角这样一个独特的作家?她这种写作的形式跟他人有何不同?从《瞧,这些人邻》这组散文里我们会发现晓角的角色代入感非常强大,她用移情召回了她的全部记忆。
不必讳言,晓角从前的生活是封闭的,也是有局限的,这种有局限所在的生活一旦灌注到笔下,她就要急于把某个方面的情境放大,比如《天上的大鱼》里的小鱼们,那是她投以巨大同情的对象,或者,以小鱼观己来建立代入或移情的均衡感;再比如《蚂蚱秋》里的蚂蚱,晓角投以的是一种绝情,她用经验细节来增强一种看似暴力快感的客观性。相合或相悖,仿佛是晓角此在凝视世界彼在的姿态;换句话说,如何显现移情的文字,是她给世界命名的一种方式。
我一直在研究文本之内的“民间暴力美学”这个概念(在这篇小文中,我希望这个概念是清晰而具体的,限制的,不会引起大家误读),作为一种风格性的“趣味”,晓角以此切入了事物的本质,不同于任何人所见,让细节也表达具体的意义,就是她对那些事物的看法,并能从中获得某种满足感。像《蚂蚱秋》这种将个人的乡村童年经验转化为一种残忍的视觉风景的动作定格,有点暴力,也很有趣,但充满了隐喻性。
我始终认为“趣味”对一个作家很重要,一个作家可以写出极有“趣味”的作品来也可以写出极无“趣味”的作品来,比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这确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不知道晓角是否预见到人们会对她这组作品有所反应,看着被作品裹挟进来的人们,她是否还会产生一种自鸣得意的幻觉——她的极端在于,她写下了与她年龄极其不相称且不祥的“趣味”(亦是死亡或重生的象征);鉴于她这种禀赋,说她是天纵奇才,肯定有点过了但又不能说不存在这回事。“趣味”的发生和来源有很多种途径,比如题材、人物、记忆或技术种种,我认为晓角的“趣味”来源于一种本能的心理情绪——这个断言的分寸感不够,我知道,但能赢得普遍的同情。晓角平日里寡言少语,几乎不怎么说话,还总是显得心事重重,她就沉默着。沉默虽然不能表示语气,却可以表示出一种(狭义的)语义来;沉默有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如晓角在纸上的作品,那是忧郁,或许是犹疑,是充满“少年创伤性记忆”的修辞性转化,也是命运之书的去蔽和深度解释,具有晓角本人的标识性。
2022-1-15 呼和浩特
——刊于《草原》2022年第1期
注:本文转发时,已征得《草原》文学月刊授权

作者简介
赵卡,本名赵先峰,1971 年生于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从事诗歌、小说、随笔和理论批评写作,作品散见于《红岩》《山花》《草原》等刊物。现居呼和浩特。
编 辑 | 塔 娜
初 审 | 高 阳
终 审 | 蒋雨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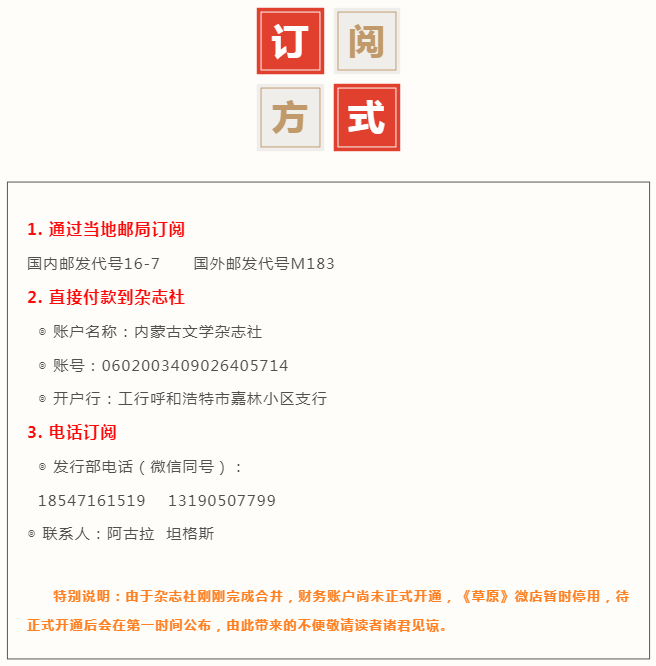

来源:草原文学月刊
作者:赵卡
https://mp.weixin.qq.com/s/UDIr6VJSt-hMBOXh8GuCRg


 纯贵坊酒业
纯贵坊酒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