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妈妈的怀抱
——浅析白庆国诗作《每晚我都睡在村庄的怀抱里》
作者:史映红
反复品读白庆国诗作《每晚我都睡在村庄的怀抱里》,就很自然地想起两位文学大师关于家乡的真切描述:一位是路遥,他在《早晨从中午开始》里写到:“我对沙漠——确切地说,对故乡毛乌素那里的大沙漠,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或者说特殊的缘分。那是一块进行人生禅悟的净土。每当面临命运的重大抉择,尤其是面临生活和精神的严重危机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走向毛乌素大沙漠”。
一位是陈忠实,他在《原下的日子》里写到:“新世纪到来的第一个农历春节过后,我买了二十多袋无烟煤和吃食,回到乡村祖居的老屋。我站在门口对着送我回来的妻女挥手告别,看着汽车转过沟口那座塌檐倾壁残颓不堪的关帝庙,折回身走进大门进入刚刚清扫过隔年落叶的小院,心里竟然有点酸酸的感觉”。从大师们的文字里,我们能看到家乡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是的,家乡是精神的依托,是心灵深处的依恋,也是疲惫身躯最好的依靠。
众所周知,随着都市化、城镇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很多村庄的荒冷与凋谢似乎已经不可逆转。近一二十年以来,孩子们上学,青壮年打工或创业,人们便不约而同地涌入城镇都市,无数座村庄就显得路冷人稀,门庭紧闭,荒凉萧条。屈指可数的老人们在光阴里风雨飘摇。但是我们深信,奔跑在车流人海里的绝大多数人,在内心总装着一个地方,一个累了困了倦了最先想起和最想回归的地方,那就是自己出生和成长的村庄。
在一二节的阅读中,能看到白庆国无限爱恋着自己的村庄,走亲访友,外出劳作,忙于生计,“无论我走多远/无论天多晚了/我都要赶回村庄/躺在家乡的夜里”;只有在属于自己的村庄,才有历祖历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劳作过的土地,土地上有他们曾经洒下的汗水;也有先辈曾奔走的脚印和躬耕的身影,有他们殷殷地嘱咐、切切的爱恋与无尽的期翼。
“安静地躺在村庄的怀抱里/安静地睡眠”,读到此处,不少读者应该与我一样深为感动,滚滚红尘,茫茫人海,芸芸众生,多少人为了高官厚禄,或虚名薄利,劳心劳力,四处打拼,有时甚至不择手段,左右逢源,见风使舵;其内心总是处于焦虑与惶恐,忧惧与惊愕之中,哪能“睡得踏实”?哪能“不做噩梦”?反观我等普通百姓,草芥布衣,无权无势,“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魏晋•陶渊明《移居二首》),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反而与人无忤,问心无愧,心安理得,总能“睡得安静”,吃嘛嘛香;谁说这不是另一种幸福?
“无论我遭遇怎样的生活变故/抑或狼狈不堪/村庄都慈祥地把我揽入怀抱/让我感到有一个坚实的依靠”,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曾有言:“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也不能使人脱离他脚下的土地,他终归要在自己的土地上扎根”。白庆国笔下的村庄,呈现出一种伟大的母性特质,沉淀和积聚了村庄特有的温馨与温暖,无论在村庄之外的地方“遭遇怎样的生活变故”,村庄都张开臂膀迎接我们、拥抱受伤的儿女,永远对我们不离不弃、相依相随;村庄有着神奇的魔力,像父亲鼓励的目光,像母亲温暖的胸膛。
“我时常在夜里,把村庄当作妈妈/把家乡喊醒”,诗作结尾溢涌和弥散着亲情的暖意,流淌和游弋着大爱和情感的涟漪;把家乡和村庄“当作妈妈”,再深情地“把家乡喊醒”,好让这些曾经可亲可敬的先辈在这片土地上再现,以文字的方式复活,陪伴诗人走过忙碌的白天和长长的暗夜。
这首诗与白庆国的很多作品一样,有一种来自内心的冲击力,一种来自大地厚重的征服力,一种诗歌艺术的感召力,让我们意犹未尽,让读者悠然神往。
每晚我都睡在村庄的怀抱里
作者:白庆国
无论我走多远
无论天多晚了
我都要赶回村庄
躺在家乡的夜里
只有这样
我才睡得踏实
一天的疲惫才能迅速恢复
才能夜里不咬牙,不做噩梦
安静地躺在村庄的怀抱里
安静地睡眠
我的亲人都在隔壁
他们与我一样睡得安静
有时翻一个身,继续酣睡
无论我遭遇怎样的生活变故
抑或狼狈不堪
村庄都慈祥地把我揽入怀抱
让我感到有一个坚实的依靠
我时常在夜里,把村庄当作妈妈
把家乡喊醒
作者简介:
自庆国:农民诗人,1964年生于河北新乐。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诗探索》《诗刊》《中国作家》《北京文学》《诗选刊》《星星》《中国诗歌》《河北文学》《山东文学》等刊发作品数百首;组诗《白庆国的诗》获《中国作家》首届郭沫若诗歌奖;组诗《干净的村庄》获河北省第十二届文艺振兴奖;出版诗集《微甜》,散文集《乡村底色》。
史映红:男,70后,甘肃省庄浪县人,笔名桑雪,藏族名岗日罗布。曾在西藏部队服役21年。在《文艺报》《诗刊》《解放军报》《青年文学》等发表各类作品1000余篇;出版诗集《西藏,西藏》等4部,传记文学《吉鸿昌:恨不抗日死》;评论集正在出版中;曾就读鲁迅文学院第19届高研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藏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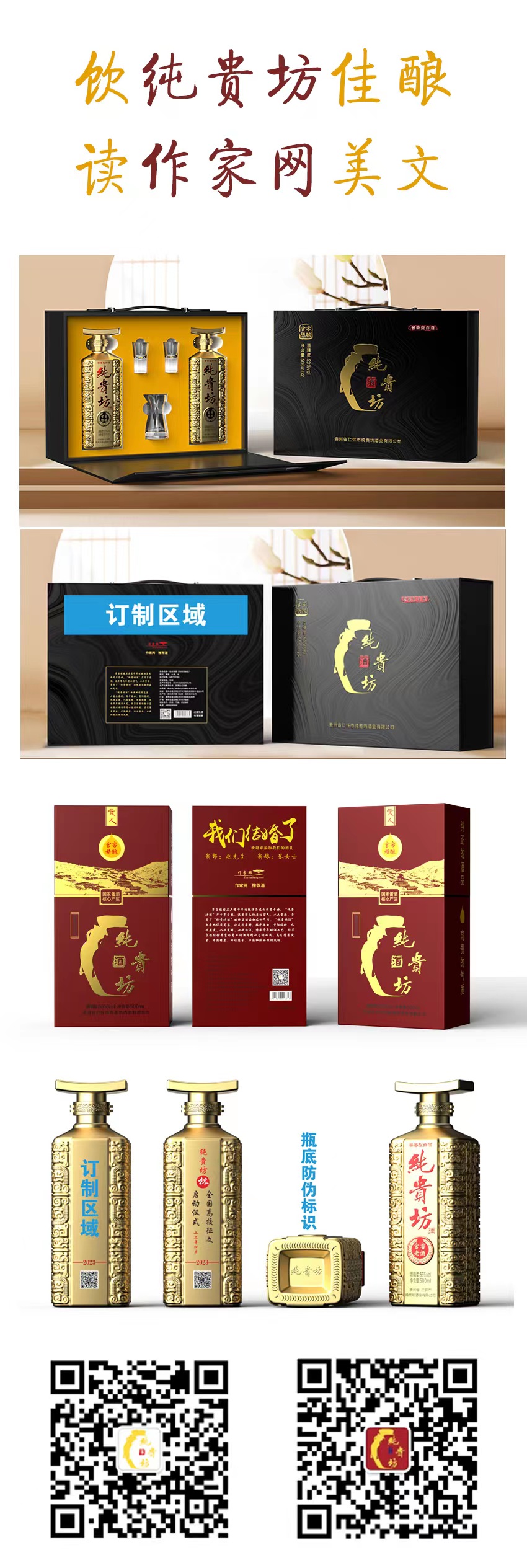


 纯贵坊酒业
纯贵坊酒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