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万物更加夺目
作者:李浩
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龙萨,“七星诗社”首要人物,我的记忆中他在他著名的《颂歌集》里,触及到了大量的关于魔神的秘传知识。这位诗人痴迷魔法,并在魔法中受到启示,他在诗歌中能够做到的是,几乎他的每一句诗都能释放出超验的、形而上的强大启示。这“启示”中的神秘,使人沉溺。提到这位诗人,同时也会让我想到爱尔兰诗人叶芝,因为有些学者的研究认为龙萨的那首著名的《当你老了》一诗,深刻地影响过叶芝。其实我想说的是,诗歌中能尽力呈现出来的东西,让我从中体验到某种灵的运行的奇妙经验,而人很难用他创造的新鲜语言完美、极致地捕捉到“他”,即使他能够和“他”进行交流。这个过程是参与启动一首诗诞生的密室游丝,也是诗人释放出另一个新生命的“圣迹区”。
从我将自己在诗歌写作中沉淀出来的这些脏腑中的感受,来理解这批写作者,我想也是可以提供一种进入他人文本的参照的。我总是对不同世界中陌生的文本产生好奇,这让我有幸在顾伟的诗中,读到“深黑的蓝比天空更加深邃”(《风尘石油路,泥火山》),“风雨同样不需要身份/见到我被它惊动”(《不偏不倚》),“漫山遍野的抽油机/如钢铁猛兽,狂奔在未来世界”(《同一个,另一个》)。这些诗句,让我觉得当人面对坚硬的现实时,“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哲思,贯连着微小生命的颤抖,就像诗人所言“日月反复路过的同一个地方”,我希望他能从这些诗句中出发。在王国良的“鸽子像一朵会唱歌的白玉兰/正在你的魂魄里掏心掏肺地咏唱”(《落在铁人肩头的鸽子》),“樱桃树就缀满了红宝石/仰望天空,就成了离我最近的星星”(《樱桃》),“一群用管钳拧亮星星的人/当我从蓝色走过,生命愈加通透”(《油田的蓝》)这些诗句中,其实,我更喜欢的是,诗歌给我们带来的告诫,那就是樱桃树上的红宝石闪耀着的像是灾难的预言,诗歌感觉中的不安,我认为这种不安的情绪才是更真实的个体。从布日古德的“五月的大地上,有他喜欢的/苣荬菜、柳蒿芽儿、婆婆丁”(《轧趟棉袄》)中,可以看出他在试图努力用诗歌唤醒自己沉睡的记忆。“我深知不能只做深夜里的烛火/它好像不能点燃任何玫瑰”(《我终不会点燃玫瑰》),“人们会点燃幸福的火焰/吹灭旧岁的烦恼/会把一袋袋水泥,送到空中/兑换星星”(《油建桥随想》),“小镇的夜色里,风在对峙/那共振如一方苦药”(《火车一路北上》),等等。曹向东的这些诗句,来自他经历的沉甸甸的时间,话语中透露出的光泽也是他对美好诗歌的盼望,他和他的诗歌正靠近,“完成一场告别和人间恒久的重逢”。
伊娃·达·曼德拉戈尔是华裔俄语诗人,她诗歌中的空间极其开阔,支撑她诗歌精神的来源也是异彩纷呈的,就像她能够告诉我们的那样——“一个试图穿过它的人/那是思想之物。用它的口吻命令”(《竹》)。她在诗歌中的这种断句方式,常常让我想起俄语中的另一位天才艾基,但不同的是伊娃·达·曼德拉戈尔在诗歌中,又站在汉语之中。她的想象力——更确切地说她从不同文化中提炼出来的诗歌感受,也是别具一格的,譬如:“太阳创造阴影,地球像滚烫的百吉饼一样燃烧。/鹰和喜鹊,/一起吃晚餐”(《知物》),“腐烂是时间的另一种生命”(《纸在指纹》)等,我祝愿她在诗歌的合唱队里,永远想着的是,“所有在你体内失踪的人”。孙大顺是一位在“身患忧郁症的大海”之中,“藏起宇宙的祝福”的人,这样的诗句让人身心深受感动。难得的是他的“每一个黑夜,都孕育着一块岩石”。张端端在近期的写作中,越来越纯熟,她的语言、情感、形式都能自洽地凝聚于一首活着的文本之中。她的这组《风和抬头看天的人》中,每一首诗都值得我们细细地品读,正是她在诗歌中触及到的柔软之心,撼动着人与人之间残酷的世界与那个始终存在的“四月是最残忍的季节”。譬如:“草坪还未干透,水珠低悬/仿佛它体内的深渊自带回声”(《雨天音乐课》),“多年前的雨夜,他刚失去一匹爱马/就在同一把藤椅,我陷落悲伤”(《藤椅》)等,这些诗句让我们体会到“寂寞的衣橱,悬空骨头”(《空衣架》)的诱惑力。由此在她们的写作中,让我们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是,诗始于纯粹的肉身存在——“我的开始之日便是我的结束之时”——最终却在另一种生命形态里胜利获得了永生,“我的结束之时便是我的开始之日”。
“只愿所有的人,在你拥抱世界时/能心怀柔软”(《咽下所有能咽下的坚硬》),这是诗人孙永云在钢筋混泥土的丛林中,面对他人的低诉。他依然保持活在肉身的现实之中。“每一场雨水/都拥有空灵的外衣/让我们足以释怀,然后去热爱”(《从端午开始》),诗人林烟在告诉我们,诗歌虽然无用,但是它在帮助我们如何去热爱他人和这个世界。诗人张显辉、蓝花伞、土圭垚、安扬,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都生活在一种及物的声音之中,用“榨取大地的赚钱机器”记忆着这座城市的历史,有一种从地下朝向阳光努力生长的毅力、经历,给人留下很多温馨的时刻。无论怎么说,我想诗人从世间的事物到成为他的艺术这一过程,渗透进来的神秘会越来越深。“但在思想向着无限的这一内在后撤中,在无限中,上帝已在各处留下了最明确的标记,以防任何优秀的思想迷失,以防人在其自身思想的使用中迷失,但每一次,他仍能够从中提取一个令其振奋的信仰行动。”这是我最近读到的几句话,我很珍视,我反复读了很多遍,对我启发很大。这几句话与我们的诗歌之间,密切相连,我想我们可以一起从这里去思考。
原载于《石油文学》诗歌锐评。

作者简介
李浩:诗人。曾获宇龙诗歌奖、北大未名诗歌奖、杜克大学雅歌文艺奖、谢灵运诗歌(双年)奖等奖项。出版诗集《奇迹》《穿山甲,共和国》《还乡》等。大益文学院签约作家,现供职于北京出版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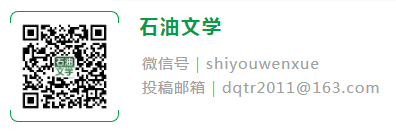
作者:李浩
来源:石油文学
https://mp.weixin.qq.com/s/Sc0Hhn9kXCKMXDn2U1bbrg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纯贵坊酒业
纯贵坊酒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