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子林最新学术著作《文学问题:后理论时代的文学景观》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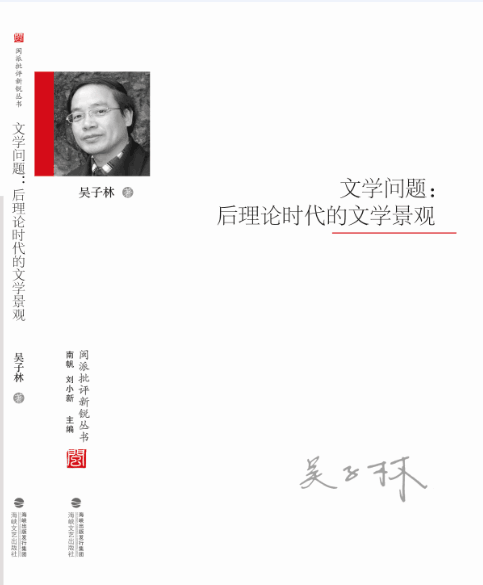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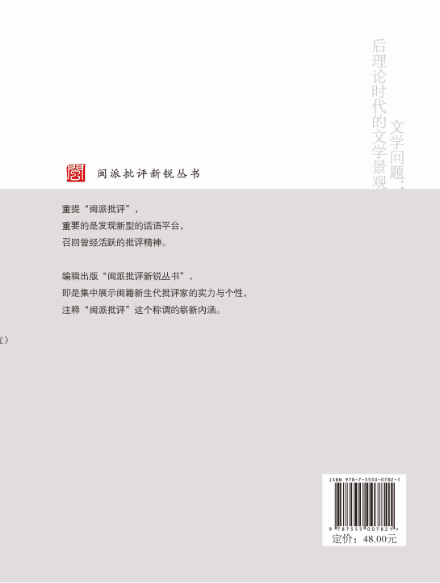

近日,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学者吴子林最新学术著作《文学问题:后理论时代的文学景观》由海峡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
本书为南帆,刘小新主编的“闽派批评新锐丛书”之一。
作者吴子林坦言,收入此书的十余篇文字,是完全按照我个人的喜好摸索而得的。不论是选题,还是文体,都不那么“规矩”,不那么“逻辑”,不那么“论文”;它们或迷离跳跃,或直率清淡,或慷慨激越,或静默低回……
[目 录]
总序 / 南帆
自 序
“文学的绦虫”
——当下文学创作、研究之去蔽或敞开
“唯一有价值的就是拥有活力的灵魂”
——讲述“中国故事”的方法或主义
“奥威尔问题”
——汉语文学之语言问题断想
“重回叙拉古?”
——论文学“超轶政治”之可能
“安尼玛的吟唱”
——《格萨尔》神授艺人的多维阐释
“你们信仰上帝吗?
——信仰与写作的质地
“不可言说的言说”
——信仰叙事的内在难度
“作家们的作家”
——当代作家原创力探源
“修辞立其诚”
——重建诚的文学
“明天会出现什么样的词”
——2030年中国文学的可能面相
“菲洛克忒忒斯的神弓”
——当代文学批评的歧途与未来
“用背脊读书”
——重构文学阅读的意义境域
“生命的学问”
——文艺学研究的一种可能向度
后 记
[自 序]
岁月在指缝间悄然流走,恍惚间从不惑之年起步奔五;牙床动摇,鬓发稀疏,皱纹加密,肌肤松弛,血压攀升……
——毕竟是岁月留痕了!
河畔,芦苇在微风中婆娑作响,晚霞晕染着齐唰唰的山林,叶儿旋着片片金光,空气中混合着青草和松木的味道。
沉浸在无边的寂静之下,我听到了自己的呼吸声。“人总要有点东西,活着才有意义”,阿城如是说。
文学是最公平宗教,不估量有多大的能力,也不计较有无成功机会;尽我心尽我力尽我份,如此而已。
虚虚复空空,瞬息天地间;本乎一己之心得,心不容已地撰为文字,将心智置于貌似捕风捉影的事业。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可自拔地写作,只是源于持久兴趣,以文字追逐那碎影流年,夯实贫乏之我。
在《人生之体验》的“导言”里,唐君毅先生坦言:愈是现代的人生哲学之著作,愈是让人喜欢不起来。何故?这些著作纲目排列整整齐齐,叠床架屋,除了可助教学或清晰些观念性知识,实无多价值;它们不能与人以启示,透露不出著者心灵深处的消息,且足以窒息读者之精神的呼吸。反之,中国先秦诸子典籍,希伯来之新旧约,印度之吠陀,还有古希腊哲学家断片式的箴言,其中自有著者的心境与精神、气象与胸襟,并以其天纵之慧,抉发人生价值,示人以正路。
何以故?唐君毅先生指出:
那些人,生于混沌凿破未久的时代,洪荒太古之气息,还保留于他们之精神中。他们在天苍苍、野茫茫之时间中,忽然灵光闪动,放出智慧之火花,留下千古名言。他们在才凿破的混沌中,建立精神的根基;他们开始面对宇宙人生,发出声音。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心境下,自然有一种莽莽苍苍的气象,高远博大的胸襟。他们之留下语言文字,都出于心所不容已,自然率真厚重,力引千钧。他们以智慧之光,去开始照耀混沌,如黑夜电光之初在云际闪动,曲折参差,似不遵照逻辑秩序。然雷随电起,隆隆之声,震动全宇,使人梦中惊醒,对天际而肃然,神为之凝,思为之深。
千祀之后,读者诸君遥念圣哲,诵其诗,读其书,不能不怀想其为人,直接感应其精神气象及著作方式,而景仰企慕,有以自奋,祈望向往,继发其潜德幽光。
可是,环顾当今之世,“唯物功利之见,方横塞人心,即西方理想主义已被视为迂远,更何论为圣为贤成佛作祖之教”。环顾当今学界,能践履钱穆先生所云学问之“四部曲”,学贯中西,融会百家,称心而谈,开拓万古之心胸,做到出才情、出见地、出思想、出断制者,又有几人?
凡能称得上“学”者,绝非一般领域,必是包罗万象,宏细兼容,有挖掘不尽之思想资源,能拉得住人心,重若千钧,是一片让人定气凝神、依枝栖息的精神家园。此“学”带给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与自己的生活融为一体,生命因之点燃的火焰永不熄灭。难道不是这样吗?
史震林(1692—1778)《西青散记》里有几句话:
嗟君何感慨,一往不可攀。仰视碧落,俯念苍生。情脉念痕,不知所始。醉今梦古,慧死顽生。淡在喜中,浓出悲外。
唐君毅先生的名著《人生之体验》便是在此种有所感慨的心境情调之下写的。“仰视碧落,俯念苍生。”上下无依,迥然独在;上开天门,俯瞰尘寰;既虔敬礼赞,又同情恻悯,其心灵是平静的、超脱的。因此,唐君毅先生说:“在此心境情调下,我便自然超拔于一切烦恼过失之外,而感到一种精神的上升。”由此心境情调而成之文字,于关节处解隙,于有碍处洞达,豁然醒目,畅然不隔,立意闳中,立论不移,而最为人所珍爱。难道不是这样吗?
然而,历史与现实赋予了太多背离学术自身发展的制度逻辑,几乎摧毁了人们对于学术的心理依存。在浮躁喧闹的边缘,太多的著述是“为人”写的,不是“为己”写的;远离本心,违背初衷。对自己不够诚恳,也就无法影响他人;除了形式逻辑,及纲目式结论,谈何引领思想之力量?既不能“度”己,更不能“度”人,纵使“著作等身”,又有何益?
张潮(1650—?)《幽梦影》有云:
文章是案头之山水,
山水是地上之文章。
又云:
有地上之山水,
有画上之山水,
有梦中之山水,
有胸中之山水。
地上者,妙在邱壑深邃;
画上者,妙在笔墨淋漓;
梦中者,妙在景象变幻;
胸中者,妙在位置自如。
如何绘出“胸中之山水”,每一个有抱负的学者都不能不加以思量。
人生之本在心,文章之本亦如是。朱子有诗云:“此身有物宰其中,虚澈灵台万境融。敛自至微充至大,寂然不动感而通。”文章的背后,是悠远寥廓、不可目视的人格、风骨和境界。人格修养的归宿即境界,“有境界则自成高格”(王国维语)。
毋庸讳言,许多问学者心智都败泄在了世俗人际关系上。他们苦心积虑地赚取、提升自己的声誉,实利成癖,虚荣入骨,总是以各种“幻影”——如科研课题、重大项目及其丰厚资金,还有名目众多的荣誉、津贴和奖项,等等——充当自欺欺人的逃路,从不再向上攀援,辟以蹊径,以克服现有研究之困顿、局促。
每个人都绞尽脑汁,为所欲为,每个人实际上也都难有所作为。不仅学养不足,不成格局,更谈不上“导夫先路”的创造。“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汪曾祺语),正是心智的坏朽,酿成了文章的邋遢不堪;对此,许多炮制为文者并未醒悟,仍我行我素地“任性”并“幸福”着。
作为一个终极眷顾,生命的境界是依次递升的。由于每个人的“才”“命”“力”不一,其所进益亦有所至而止,其文章精神层级之境亦自有其极限——或本能性表现身体欲望,处于不识不知的混沌状态;或满足于个体功利需求,以博取功名利禄为指归;或凝合为一道德主体,遵循特定社会标准、典范,满足于政教人伦驯化;或“上下与天地同流”,“参天地,赞化育”,臻于“自如”的“至乐”之境。
《金刚经》有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无所住”即不拘执某物,不思得失,不思荣辱;不媚俗,不媚权贵;祛除“计算”、“操作”和“规划”,是谓“出离”,是谓“得解脱”。宁神静气,气贯于一,则“生其心”,即无中生有,自由创造,生命精华自然喷薄而出。曾国藩诗云:“长将静趣观天地,自有幽怀契古今。”
我喜欢读书,沉迷于理智与情感交融的心境;
我喜欢思考,执著于精神的探险而无中生有;
我喜欢写作,陶醉于内在性灵的充盈或发现。
我的一点学术理想——
返回内在明镜灵台,与纯真的生命对谈,将理论研究变为自发性的创造,将理论研究转变为文学问题的专业性参与、学理性反馈;
带着斑驳的经验、琐屑的记忆,装着一个时代进入历史,直面中国的文化原典,从“小学”入,由“义理”出,在回归中实现超越;
以孤绝的勇气,鲜润的语言,开辟榛芜,不让外部世界压迫同情心、想象力和创造力,迈向更高的完善与存在,以克服自己的时代。
文学和艺术,始终面对、叩问人类永久的价值;就像随手撒下的花籽,不久便是漫山遍野的格桑花……
这部自选集收入了我近年来的十余篇新作,它们存留了我个人的某些思考,可谓探索性的“尝试集”。
是的,“写作,那是唯一填满我生命并让它欣悦的东西。我做到了。写作从未离我而去”(杜拉斯语)。
我的授业恩师童庆炳先生生前一直关注本书的撰写与出版,对于我的探索亦勉励有加。谨将此书敬献恩师!
是为序。
[后记]
一年又一年,周而复始。
仿佛可以荡涤一切前尘,从头再来,如同新生。
夜雨敲窗,山风滚落。
曾几何时,一个乡下来的孩子,站立在被风吹得发白的乡间路口,遥想壮丽原野,痴痴遐想:“远方有多远?”
几条路蜿蜒下来,一个清清瘦瘦的青年,驻足城市繁华街头,沉默而倔强,他的心里有千万种声音在轰鸣,在奔走。
再后来,步入中年,身居嘈杂而蓬勃的京城,无论是寻找迷失的自我,还是紧随命运的牵引,心头日夜不息的潮汐与风浪,总将自己推送到未知的海岸。
尽管贯穿脱胎换骨的痛苦,以及重获新生的喜悦,眉宇间目光清澈如故。
远方或许真的并不远,又或许,远方除了地平线,什么也没有。
如是而已。
日光之下,万物简单如初。
时光起伏、交错、交汇,文字炽热、瑰丽、浩荡;梦想因之掀开,骨骼血肉顿生。奔走在忙碌劳作的命途,我渐渐领悟了此生的宿命。
如果说生命的意义在于体验,写作则是极力拓展体验的边界;那一篇篇文字便是一个个生命的休止符,一段段悲欣交集之碎片的记录。
一切纷至沓来,人生真是丰富啊,就让一切都跟随命运去嬗变吧!
收入此书的十余篇文字,是完全按照我个人的喜好摸索而得的。不论是选题,还是文体,都不那么“规矩”,不那么“逻辑”,不那么“论文”;它们或迷离跳跃,或直率清淡,或慷慨激越,或静默低回……
这首先得感谢《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先生,由于他的热情与大度,这些文字以“文学问题”专栏形式一篇篇面世。
还得感谢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南帆先生,因为他的大力支持与帮助,拙著得以第一次在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最后感谢我的太太诗人安琪,她是每一篇文字的第一读者;倘若说这些文字有“诗性”,这多半归功于诗人的同化!
吴子林
2016年4月5日北京家中
作者简介:
吴子林,1969年生,福建连城人,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评论》编审,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文学基本理论、中西比较诗学及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研究与批评,已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小说评论》《文艺争鸣》等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著有《中西文论思想识略》《童庆炳评传》《批评档案——文学症候的多重阐释》《文学瞽论》《20世纪中国文学史通论》(第6卷)《中国现当代文学论争中的理论问题》《经典再生产——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文化透视》《自律与他律》(合著)等,另有《艺术终结论》等各种编著20余部,诗歌散文随笔若干。现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及巴赫金研究分会秘书长、叙事学研究分会副会长。


 纯贵坊酒业
纯贵坊酒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