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白话百年中国当代诗歌百人微访谈(二十七)
臧棣、刘立杆、黄粱、王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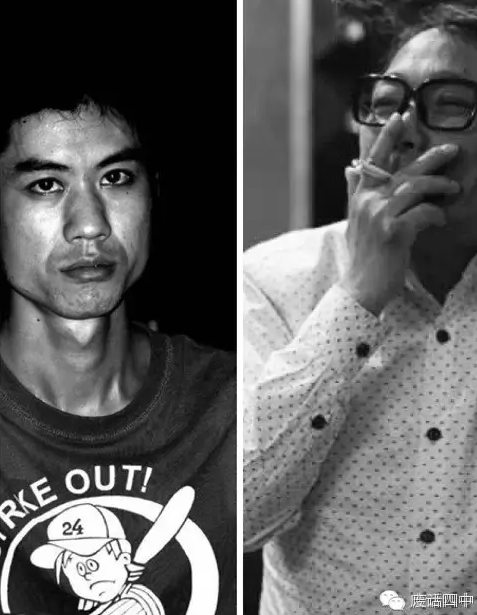
编按:
到今天这一期,白话百年中国当代诗歌百人微访谈就暂时告一段落了。部分受访者由于这样那样的客观原因,没有答完或者未能在截稿前回复,9月底是我们截稿日期,截止今天通过废话四中微信平台一共发表了82位诗人及诗评家的精彩回答,套句大俗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呵呵。
我作为问答微信平台的编辑工作也到此结束,后期工作将交给实体书的编辑,希望能尽快成书。
再次感谢所有参与微访谈的朋友。
几个月来,有好些朋友在后台留言,觉得看问答不过瘾,要看诗。这个愿望当然要满足!这段时间大家有什么好作品,自己写的,推荐朋友的,快快发到编辑邮箱来。
最后, 小长假过半,要抓紧玩乐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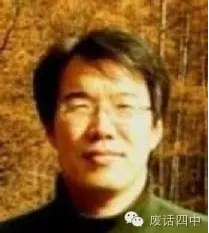
臧棣回答
一、你认为中国当代诗歌最大的成功是什么?没成功的话那最大的问题又是什么?谢谢你的支持,我等着。
成功或失败,这样的字眼恐怕不适合谈论诗歌。诗的问题,我觉得还是莎士比亚的感觉最接近一种真相;它就是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就文学现象而言,诗是一种存在,一种发生学的产物。成功也好,失败也罢,对于诗的这种神秘的存在性而言,都是很外在的角度;倘若能得出什么结论,也必然是很浅薄的观察。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新诗,中国的当代诗,取得的最大的成就是,历经百年的实践,它已赫然存在在那里。这种存在性,既基于古老的诗性的表达的冲动,也源于多变的顽强的现代敏感;最重要的,这种存在不会因人们的议论或评价,而有丝毫的改变。举例说吧,即使再有话语权的人发狠断言新诗已失败,也不会丝毫减损新诗的存在。换句话说,当代中国新诗已获得了一种诗性的书写意志。在我看来,这恐怕是它最大的成就。经过百年的实践,几代使用现代汉语的诗人,虽然走过不少弯路,也在极端狭隘的历史格局中进行了拼力挣扎,当代中国诗人终于获得了一种强大的诗歌能力,在措辞方面,在诗性洞察方面,在灵活处理诗的素材方面,我们终于有了可以应付各种复杂的当代问题的自信。
二、谢谢你的回答。对于第一个问题,几乎都给了中国当代诗歌肯定。而这种肯定,都和语言紧密联系。那么我想请教你,中国当代诗歌究竟为现代汉语提供了什么新机制和新内容?顺便再问一句,现代汉语和古白话又有什么本质的差异?期待你独特的高见。
作为一个文学事件,新诗刚刚发生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新诗的语言能力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怀疑;这种怀疑甚至在鼓吹新诗的阵营里,也很普遍。所以,我们今天再翻看新诗的发展史,会发现那个时代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群体在书写新诗时,几乎都带有一种玩票的性质。大家只是觉得,新诗作为一种现代事物,应该支持它。至少,这样立场符合那个时代的政治正确。但是,新诗的水在文学价值上究竟会有多深,所有的人其实心里都没底。胡适是如此,周氏兄弟也是如此。即便像卞之琳这样的大诗人,到了晚年,私下里也不过觉得新诗是一种雕虫之技:言下之意,新诗似乎担当不了大任。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大问题。也就是说,在新诗的发轫时期,现代汉语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现代事物被发明出来的。从语言学的角度看,现代汉语的发生及其传播,都带有很深的现代工具理性的痕迹。在骨子里,现代汉语在语言观念上侧重的是现代的交流,它的语言图式是清晰和延展。按现代性的标准,清晰和延展,在语言的表达方面,都指向一种逻辑的连贯,和意义的确定性。如果我们去细心辨认胡适有关新诗语言的设计方案,就会明显地感到这一点。按这样的语言学路径,现代汉语和诗性书写之间丰富的关联,其实被人为地狭隘化了。
但从大的方面讲,胡适也没有全错。胡适对新诗的语言和清晰性之间的关联的想法,毕竟为重构现代汉语的现实感奠定了一种方向。按胡适的想法,古代汉语在诗歌的书写方面,缺乏现场感,过于偏重记忆,不能有效地介入人生的历史场景;这是古代汉语在应对现代事物方面表现出的天然的缺陷。而现代语言对清晰性的要求,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在新诗百年的实践中,胡适的新诗语言观尽管颇受物议,但其实,经过新诗的文学场域合力修正,我们现在在使用现代汉语表达诗性的感受时,已经能将诗性的感受和风格的精确锤炼得相当自洽。
另一方面,正如我上面讲到的,现代汉语在推广之初,其实相当偏向于工具性,偏向对语法的逻辑性的过度迷信。按当时知识分子诗人的设想,新诗的书写对语言的含混,语言的延宕,语言的散逸,其实是相当排斥的。这种排斥相当专断,以至于连支持新诗的人,都会在私下里感到压抑。所以,才会发生周作人为李金发叫好那样的事。周作人并不真懂李金发的现代性,但是周作人懂语言的诗性问题。李金发的诗,简单而言,就是它贡献了一种现代汉语在表达上的陌生性。这种陌生性强化了汉语和现代意识之间的深刻关联。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当代诗对现代汉语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也是不可或缺的。即当代诗的异常多样的具有开创性的写作,为现代汉语带来持续的陌生性。因为当代诗的实践,我们强化现代汉语和现代审美之间的关系。我们也深化了现代汉语和现代感受力之间异常丰富的关联。最重要的,由于当代诗的书写,我们有效地从语言表达的内部改变了现代汉语对工具性的信奉。
三、很好,谢谢你的回复。在做这个微访谈时,我们在白话诗、新诗、现代诗、现代汉诗和当代诗歌等好几个词语中费了许多脑筋,总觉得没有最为准确的叫法。说新诗吧,那它针对什么旧呢?而且已经100年了,也不能一直这样叫下去。说现代诗歌吧,难道它不包括当代吗?说现代诗,其实好多诗并不现代,难道就要拒绝在这类诗歌历史之外?所以,我们真的很迷茫。所谓名正言顺,为中国百年来新的诗歌找到自己的名字,的确算一个迫切的问题,而且我们还发现,没有准确的命名,应该是中国现当代自由白话新诗最大的隐患。对此我们再次期待你的高见,找到最准确的说法。
我原先也焦虑这个问题,但现在说实话,不怎么焦虑这个问题了。现在,想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不可能;但会相当繁琐;而且按我的预感,即便我们在诗人共同体内解决了这个问题,回到当代文化的公共领域里,人们还是会有困惑。其实,新诗,现代诗,现代汉诗,当代诗,都对应于不同的谈话场合。它们之间的内涵和外延,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历史情境中,互有重合,又有区别。比如,站在诗人的立场,当代诗人基本的共识是,我们现在所写的“当代诗”,其实已经和“新诗”没什么关系。但这种感觉,可能只属于来自写作内部的一个视角。真要放到文学史的语境中,或者放到文化史的语境中,未必能获得多少应和。就我而言,当代诗已彻底颠覆了五四新诗的基本理念。它肯定属于一种新的诗歌书写类型了。我的基本想法是,如果想要准确的名称的话,这个问题恐怕现阶段无法解决。如果我们想做一个和具体的诗歌现象拉开点距离的探讨,使用“现代汉诗”这个名称,可能更适合进行一种相对而言客观的文学史观察。但沿着这个路径,即便我们对新诗的百年实践做出很好的阐释,这个名称要想被普遍接受,也要看运气。回到当代的写作情境,如果有人问,我肯定会明确地回答,我写的不是新诗,而是当代诗。但如果回到汉诗本身的发展脉络,从大的历史格局来看,我们现在所写的当代诗,恐怕依然要处于某种“新诗”的阴影之中。这个也没办法。我们恐怕无法阻止人们不将我们写的当代诗误解成我们依然是在写新诗。我理解,这种麻烦,是我们作为当代人必须付出的一种代价。
四、好的,你的说法有道理,但你也知道这样一个事实:这种诗,我们已经写了100年了。100年好像不长,但肯定也不短。亲,就你的阅历和学识,在这100里,有哪些诗人、哪些作品、哪些事件和哪些关于诗的言说,你认为是有价值的?有发展的?至少是你记得住的?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必定是一个关于诗歌100年历史的访谈。辛苦,辛苦。感谢,感谢。
在诗观方面,胡适的看法虽然有点粗糙,但这种粗糙,回到文学史语境中,却包含着奇妙的启示性。这一直很吸引我。艾青的直觉,是一个异常。卞之琳,大诗人,他可以说第一个运用现代汉语而接近现代智性的诗人。他的谦卑,近乎一种狡黠的文学骄傲。这个,也很有启示性。穆旦的天真,更是一笔明显的财富。戴望舒的语感,虽然不够稳定,但感觉找对了的时候,戴望舒绝对是一个令人钦佩的人物。谁能把洛尔迦翻得那么出色?作为一个文学事件,在大家都迷信意象的时候,海子对意象的极端的排斥,也很具有启发性。顾城的《颂歌世界》,我觉得很了不起。韩东的“诗到语言为止”,也很了不起。
五、谢谢你回复,让我们的访谈很有价值。在前面四个问题之后,我们觉得有一个绝大的问题必须摆到桌面上来:这个问题,就是诗歌的标准问题。诗歌到底有没有标准?或者说有没有唯一的永恒的标准?笼统而言,“古代诗歌”似乎是有标准的;而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白话入诗,诗歌事实上陷入一种先验的迷惑中:它至今也没有完全确立自身,或者说,它需要像中国古代诗歌一样,确立一个标准码?说白了吧,上追千年下启万世,到底什么是“诗”?期待你指教,并先谢。
诗的标准就是天才的标准。幸运的是,在诗的书写历史中,我们会遭遇到不同类型的天才,有让人深感意外的天才,有孤绝的不太按常理出牌的天才,也会有集大成式的人物。按我的观察,唯有天才的写作能给诗歌制定某种标准。其他的,比如,我们在具体的日常场合,或是在严肃的学术场合里,触及的和诗有关的好还的标准,都不会很可靠。诗的标准,只能来自诗。所以,一方面它和年代没有关系。这也是我说只有天才能确定诗的标准的一个理由。诗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生命的欲望。一种表达。古人说,诗言志。就此而言,诗的标准的给定理由,全赖天意。另一方面,诗的交流又发生在社会共同体之中。诗,又是交流的产物,它必然要遭遇人们对它的议论。好坏由此产生。不过,既然源于议论,就说明诗的标准是相对的。说古代诗歌有标准,其实也不确切。只能是相对而言。如果回到写作内部,新诗的写作其实也深受标准的制约。甚至可以说,它触及的标准问题比古诗的书写要多得多。古诗的写作图式基本上偏于格律体,意境,辞藻,声律之间的自洽性,是给出标准的基本来源。而新诗的写作图式偏于自由体,借助的是从散文内部锤炼散文的诗性,好的标准基本上是由诗的洞察力,语感的亲和力,感受里的复杂和微妙,语言的陌生给出的。另外,我觉得,说新诗没能确立自身,这基本上是外行无意中给新诗下的套。我们最好是不接这个茬;因为怎么接,总会有人无知地说,新诗还没确立自身。什么叫确立自身?康德讲过一个视角,疑惑时,最好抬头仰望一下星空。宇宙还在神秘地不断裂变自身呢。宇宙都没忙着确立自身,为什么非单单要求新诗确立自身?这个,我真想不明白。所以,我的直觉,这就是一个套。
六、谢谢你。关于中国百年诗歌的访谈,问题还多,但已大致有数。这里,我们想用一个古老的问题作为我们访谈的结束,那就是你为什么写诗?或者说是在今天,世界已经发生了那么大的改变,而你为什么还写诗?写诗,对你究竟有什么好处?
一开始写诗,是觉得诗的表达,能带来一种新奇的感受。这种新奇的感受,能突破日常生存中的很多谎言,刺激一个人回到生命的本意。因为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我们所受的教育里有很多谎言,而诗的表达倾向于天然的,不受羁绊的,自由书写。这种自由的抒写能激活一种生命的觉醒。后来发生的事,也很正常。因为只有一个人还有点抱负,那么他在一个行当里浸淫久了,他自然就会琢磨这个行当里的秘密。诗的书写,在我看来,它既能激活生命本身的觉悟,又能激发一种独特的快感。而且据我模糊的感受,这种写书的快感,还指向了一种生命的权力。诗是神秘之物。在现实层面,它无用,它是我们对世俗身份的一种极度的浪费。但就个体生命的自我完成而言,写诗又参与了塑造了最本真的那个我。所以,写诗这活计,说大也大,说小也小。但有时我真的会这么想,如果不写诗,我会失去我的面目。
臧棣,1964年,出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1997年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99年至2000年任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访问学者。曾获《作家》杂志 2000年度诗歌奖,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刘立杆回答
一、你认为中国当代诗歌最大的成功是什么?没成功的话那最大的问题又是什么?谢谢你的支持,我等着。
一片风景,无论壮阔秀美还是简陋平淡,似乎都跟成败不沾边;中国当代诗歌同样如此。如果非从社会影响或是文学史的角度作出判断,恐怕我不是那么乐观。在世俗生活的层面,诗有何用呢?那么多诗人和批评家不遗余力地为诗辩护,恰好证明在一个变化了的世界上,诗是必然失落的歌。提出诗的成败问题,大概也源自对“无用”的焦虑吧。
当然,抛开诗歌教育的缺失,读者对诗歌的工具性要求并无不妥。在一些危急时刻,诗歌也确实表现出无可替代的作用,比如集体创痛的抚慰,人性复苏的呼吁以及政治诉求的宣泄等——无论是朦胧诗,还是80年代诗歌运动,包括甜腻的“诗和远方”,都是因此生发。
在何种程度上,诗的介入和诗的见证是有效的?当代诗如何在硬邦邦的现实和复杂、晦暗的人性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也许正因为对无用的“焦虑”、文学行动的渴望,以及传统概念的文学使命,使当代诗歌在现实立场和自身的美学守则之间,呈现出一种跷跷板效应。在我的阅读范围内,不管迎合与挑逗,心机和利用,介入与躲避,此类两极化的应激性反应,实质上都削弱了诗的内在“回声”。
但因此把问题归咎于当代诗人的无能和软弱,显然过于苛责。新诗即便百年,在漫漫时空里也不过是一霎。而我们所说的当代诗歌仅仅在时间上保持了它的整体性,实则不过是断续的、孤立的、破碎化的景观。从白话新诗到九月派,从救亡文学到延安文艺讲话,从文革新民歌,再到朦胧诗和“第三代”,就像一台染了病毒、反复重启的电脑,只有不断崩裂、散落和重建,并没有一条清晰的脉络可循。到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更加复杂,不仅有社会的变迁,有传统与现代性的冲突,也有观念和写作实践的脱节。
至少,当代诗歌还有太多问题需要厘清,太多无聊的诗学争论和高蹈的理论建设需要回到常识,需要更多时间和耐心,而非快意的摧毁,口号和大字报式的革命。白话百年新诗作为一份遗产,还需要更加仔细清点和梳理。我个人觉得,当代诗歌至多完成了一部分基础工作。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五四白话诗及九月派拓出了一片空地,朦胧诗人拖着石碾压实了场地,第三代诗人铺上了碎石,而我们现在也许正搅拌水泥——起飞的跑道还没有铺砌完工,谈论信号塔似乎为时尚早。在此之中,唯一令人振奋的是,这一代诗人或许仍有着铺路的光荣。
这问题让我摸不着头绪。直白点说,如果你现在去街上拦下十个人,请他们背诵一首诗,我相信十有八九是“床前明月光”那种东西。那么,问题已经很清楚了。我理解百年新诗的成功仅仅是,我和亲友们说到写诗,不会有人觉得我在写古体诗——那是老干部写的,我显然不够资格。
二、谢谢你的回答。对于第一个问题,几乎都给了中国当代诗歌肯定。而这种肯定,都和语言紧密联系。那么我想请教你,中国当代诗歌究竟为现代汉语提供了什么新机制和新内容?顺便再问一句,现代汉语和古白话又有什么本质的差异?期待你独特的高见。
我不认为,诗歌能够为任何一种语言提供了新的机制和内容。这种想法未免太自大了。诗的语言和音调哪怕是律法,也不是人间的律法。我理解你的意思。颇为讽刺的是,在谈论汉语之美时,你会发现人们更经常拿古代汉语举例。
语言的变迁和诗歌音调的变化,同样是现实的折射。随便举例,小津安二郎有次对电影对白提出质疑。他说,日本男女在约会时怎么会说“我爱你”呢,最多说“今晚的月亮很圆”吧——你会说“我爱你”,但这不能归功于诗。
诗,为生活提供了一种新的想象,一种可能;它改写了美的边界;它把人的视线从地面引向高处;它提供了更多感受和观看的方式;它有别样的气息,优美或冷峻的音调。如此等等,我以为这些是高于诗的技艺层面的。
诗人们侍奉语言,但语言不能成为诗的终极。否则,就可能导致另一种危险。这些危险我们都不陌生:比如,命名的狂欢演变为暴力的变体;或者,由于对意识形态的怀疑,意义的消解,使诗进入过于挑剔的,消了毒的形式领域。在语言问题上,我以为这是尤其需要警惕的。
至于现代汉语和古白话的差异,对于我,大概等同于方言和普通话的差异,等同于汉语和英语的差异——它们表达的,无非是一样的欢乐和哀愁。
三、很好,谢谢你的回复。在做这个微访谈时,我们在白话诗、新诗、现代诗、现代汉诗和当代诗歌等好几个词语中费了许多脑筋,总觉得没有最为准确的叫法。说新诗吧,那它针对什么是旧呢?而且已经100年了,也不能一直这么叫下去。说现代诗歌吧,难道它不包括当代吗?说现代诗,其实好多诗并不现代,难道就要拒绝在这类诗歌历史之外?所以,我们真的很迷茫。所谓名正言顺,为中国百年来新的诗歌找到自己的名字,的确算一个迫切的问题,而且我们还发现,没有准确的命名,应该是中国现当代自由白话新诗最大的隐患。对此我们再次期待你的高见,找到最准确的说法。
你确实换了好几种说法,但意思已经足够清楚。或许还可以补充一下,过去还有很多人管这叫自由诗。道常无名,模糊和歧义本来就是诗的一部分。如果非要在你给出的选项里进行勾选:在百年的时限里,我会选新诗;在诗歌传统的语境里,我会选当代诗歌——我在第一问中解释过,百年新诗较为完整、持续和有序的脉络只能从朦胧诗算起,至于卞之琳或穆旦等孤例,对于今天的写作只是一道遥远而微弱的流光。
四、好的,你的说法有道理,但你也知道这样一个事实:这种诗,我们已经写了100年了。100年好像不长,但也肯定不短。亲,就你的阅历和学识,在这100年里,有哪些诗人、哪些作品、哪些事件和哪些关于诗的言说,你认为是有价值的?有发展的?至少是你记得住的?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必定是一个关于诗歌100年历史的访谈。辛苦,辛苦。感谢,感谢。
很惭愧,作为一个学徒,我对翻译诗和西方诗学理论的阅读,可能远多过这100年来的本土诗歌。对后者的阅读也是零打碎敲,就近学习,基本局限于读者批评的范畴。对当代诗歌的本土性问题,很长时间是我思考的盲区。我刚开始重新补课。所以,我只能以自己有限的经历和阅读印象,作个粗略的简述。
我在中学时第一次接触到现代诗人的诗,包括九月派,湖畔诗人,徐志摩、戴望舒和艾青等,来自一套白封皮、名为《现代文学参考资料》的丛书——算比较系统,但也仅止于阅读。其间,也在文学杂志上留意到北岛、舒婷和顾城的诗,多半是以争鸣的形式刊载。在诗歌启蒙的角度,朦胧诗与我就像是一扇新奇又令人费解的窗景。
真正促使我进入当代诗歌的,是碰巧冈进大学结识了一群诗人,包括韩东、小海、于小韦、小君等——他们要么是生活中的朋友,像小海还是同班同学。我是因为“他们”的缘故才开始学习写诗的。这是一个美妙的开始,诗歌对一个初学者不仅是青春的骚动和自我抒发的热情,这个巨大的磁场还意味着友谊和自由的呼吸。“他们”乃至口语诗推崇的直接、明朗和朴素,在我身上有着很深的烙印。延续到今天,口语或直接性已不再构成明确的写作原则,但作为诗歌棱镜的一个面,它们使我的视野有了更大的纵深。
除了翻译诗,我在九十年代细读的当代诗人包括吕德安、柏桦、多多和张枣。其中,张枣对我的影响尤深——很有趣,这种影响并不在于他标识性的美学追求,而在于他独特的音调和深度意象诗的回声,这多少暗合了当时我对意象派诗歌和勃莱的研读。老实说,在那个焦灼不安、充满自我怀疑的转变期,我汲取的养分更多来自搜罗来的西方画册——从后期印象派到超写实,靠这种偷懒的挪移,场景和画面逐渐被置于变化了的诗歌聚光灯下。对当代诗的阅读显然离不开对同龄人的关注。这里我愿意提到朱朱和叶辉——同样是偷懒、简便的阅读,就近原则,生活中的朋友。当然还有更多,不少于十数人,恕我无法一一提及。
至于事件和关于诗的言说,很抱歉,我只记得一些喧嚷和噪音。诗,通常大于事件和言说——我很尊重身体力行的写作,也特别羡慕行吟诗人的生活方式,但囿于个人视野和判断,我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
五、谢谢你的回复,让我们的访谈很有价值。在前面四个问题之后,我们觉得有一个绝大的问题必须摆到桌面上来:这个问题,就是诗歌的标准问题。诗歌到底有没有标准?或者说有没有唯一的永恒的标准?笼统而言,“古代诗歌”似乎是有标准的;而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白话入诗,诗歌事实上陷入了一种先验的迷惑中:它至今没有完全确立自身,或者说,它需要像中国古代诗歌一样,确立一个标准吗?说白了吧,上追千年下启万世,到底什么是“诗”?期待你的指教,并先谢。
诗无疑有自身的标准;但这个标准绝对不是先验的,也不能等同于工业流水线上的质检卡尺。它是滞后的,需要时间过滤的;从有效性的角度说,也是不断变化的。古代诗歌的标准也同样如此。比如李白就有众多应景或唱和的平庸之作,而杜甫在他生活的时代则是被忽略“小诗人”。
诗的标准既绝对又含混。它的绝对在于,诗必须展示至高的精神维度,独特的音调和观察事物的角度,对人性的洞悉,对虚无的穿刺力,以及同情、勇气、怜悯和理解,等等。它的含混在于,每一首伟大的诗都构成标准的一部分——它是开放性的,永远期待更多,始终处于令人兴奋的可能性中。
这个问题的提出,大概与当代诗混乱的价值取向有关。这显然是一锅杂烩或乱炖:乡村抒情和民族史诗,颂扬和规训,反讽,狭隘的个人和小市民的伤感主义,政治抗议和苦难叙事,绕避现实的风景诗,遗老式的缅怀和底层关怀,官方和草根,学院和民间……而这难道不是我们置身的现实图景吗?而一首伟大的诗就是一根大头针,足以把这个时代的众多标本钉在未来的卡纸上。
六、谢谢你。关于中国百年诗歌的访谈,问题还多,但已大致有数。这里,我们想用一个古老的问题作为我们访谈的结束,那就是你为什么写诗?或者说在今天,世界已经发生了那么大的改变,而你为什么还写诗?写诗,对你究竟有什么好处?
很简单,写诗或以诗为重心展开的生活,使一个诗人得以同时行走在两个世界。而从感受力的角度说,诗不仅帮助人们更深地进入世界,也通过对时间的质疑来抵抗虚无,挣脱人的局限——世界在变,但人性始终不变。我觉得,因为写诗自己其实活了两世。
七、哇,各位大侠:访谈完了,我们才发现是六个问题,而我们算了以下,六个问题不吉利。所以,我们必须麻烦你,再回复我们一个问。不过这个比较简单,也很好玩。你可以不回答,但一定不能不回复。一定。我们的这个问题是关于写诗与性的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说,写诗对你的性想象和性行为有没有影响?期待你的回复,多谢多谢。
“访谈完了”,就不扯淡了。
刘立杆,1967年生于江苏苏州,198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写诗及小说。

黄粱回答
一、你认为中国当代诗歌最大的成功是什么?没成功的话那最大的问题又是什么?谢谢你的支持,我等着。
最大成功:(一)对人的价值、心灵奥秘、社会生活、历史真相进行了深刻持续的探索,展现「另一种真实」的存在 。(二)对异域诗歌译本进行文本资源转化,丰富了本土的诗歌体式和诗语组织。(三)以日常生活语言介入诗歌触摸当下现实,使诗的体质连天接地,拓展言说范畴。
最大缺憾:(一)多数文本局限在「以中国为天下」的认识论视域中,对当代世界、人类文明、地球生态、灵性世纪等议题,缺乏心灵关注和诗意参与。(二)对「五四运动」将传统与现代两极分化产生的文化断裂,未能进行自觉性的溯源与连结,对「汉语文化」的主体性依旧认识模糊,对(古典/现代)汉语诗歌缺乏整体性的认知。(三)对「诗」的文化价值欠缺批判性反思,相对于丰富的新诗原创文本而言,新诗评论文本呈现视野窄限与论述浮泛化。
二、谢谢你的回答。对于第一个问题,几乎都给了中国当代诗歌肯定。而这种肯定,都和语言紧密联系。那么我想请教你,中国当代诗歌究竟为现代汉语提供了什么新机制和新内容?顺便再问一句,现代汉语和古白话又有什么本质的差异?期待你独特的高见。
汉语新诗变构/扩张了现代汉语的三重框架:句法学(语言图像)、语义学(现实图像)、语用学(心理图像);赋予新机制:诗的语言策略与思想视野,为现代汉语提供了新方法、新观念;赋予新内容:诗的空间想象与现实解构力,为现代汉语提供了更超越、更内在的文化图像。
现代汉语是现代书面语和现代口语的总称,古白话为前现代的现实生活语言。
三、很好,谢谢你的回复。在做这个微访谈时,我们在白话诗、新诗、现代诗、现代汉诗和当代诗歌等好几个词语中费了许多脑筋,总觉得没有最为准确的叫法。说新诗吧,那它针对什么旧呢?而且已经100年了,也不能一直这样叫下去。说现代诗歌吧,难道它不包括当代吗?说现代诗,其实好多诗并不现代,难道就要拒绝在这类诗歌历史之外?所以,我们真的很迷茫。所谓名正言顺,为中国百年来新的诗歌找到自己的名字,的确算一个迫切的问题,而且我们还发现,没有准确的命名,应该是中国现当代自由白话新诗最大的隐患。对此我们再次期待你的高见,找到最准确的说法。
「白话新诗」简称「新诗」,强调以「白话」书写的新诗。「中国现代诗」简称「现代诗」,强调以「现代诗体」书写的新诗。「现代汉语新诗」简称「现代汉诗」,强调以「现代汉语」书写的新诗。「华文新诗」简称「华文诗」,强调以「华文」书写的新诗。上述四种英文学术名称通用:「Modern Chinese Poetry」。
「当代中文诗」简称「当代诗」,强调在「当代时段」书写的新诗,英文为:「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四、好的,你的说法有道理,但你也知道这样一个事实:这种诗,我们已经写了100年了。100年好像不长,但肯定也不短。亲,就你的阅历和学识,在这100里,有哪些诗人、哪些作品、哪些事件和哪些关于诗的言说,你认为是有价值的?有发展的?至少是你记得住的?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必定是一个关于诗歌100年历史的访谈。辛苦,辛苦。感谢,感谢。
我将诗人与诗文本视为诗歌文化的核心图像,事件、思潮、流派、团体为边缘图像。
我所关注的诗人与诗文本例举20种如下:
鲁迅1881-《野草》、废名1901-的诗、穆旦1918-的诗、周梦蝶1921-的诗、商禽1930-《商禽诗全集》、痖弦1932-《痖弦诗集》、昌耀1936-《昌耀诗文总集》、梁秉钧1949-《普罗旺斯的汉诗》、北岛1949-《守夜》、多多1951-的诗、零雨1952-的诗、于坚1954-《零档案》《巨蹼》、王小妮1955-的诗、顾城1956-《顾城诗全集》、萧开愚1960-《内地研究》、余怒1966-的诗、杨键1967-《惭愧》《哭庙》、吉狄兆林1967-的诗、朵渔1973-的诗、昆鸟1981-《公斯芬克斯》。
五、谢谢你回复,让我们的访谈很有价值。在前面四个问题之后,我们觉得有一个绝大的问题必须摆到桌面上来:这个问题,就是诗歌的标准问题。诗歌到底有没有标准?或者说有没有唯一的永恒的标准?笼统而言,“古代诗歌”似乎是有标准的;而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白话入诗,诗歌事实上陷入一种先验的迷惑中:它至今也没有完全确立自身,或者说,它需要像中国古代诗歌一样,确立一个标准码?说白了吧,上追千年下启万世,到底什么是“诗”?期待你指教,并先谢。
不论古今中外,诗的座标架构都是恒定的:基础座标、文体座标、历史座标、审美座标;诗的评价尺度都是变动的:依时、依地、依文、依人而异。
诗者,停顿世界。诗是决定性经验与整体性价值的共同体,历史荒原上的人之树。从一首诗可洞观一世界。
六、谢谢你。关于中国百年诗歌的访谈,问题还多,但已大致有数。这里,我们想用一个古老的问题作为我们访谈的结束,那就是你为什么写诗?或者说是在今天,世界已经发生了那么大的改变,而你为什么还写诗?写诗,对你究竟有什么好处?
写诗,为轮回的人与历史留下「不虚此行」的痕迹。
七、哇,各位大侠:访谈完了,我们才发现是六个问题。而我们算了一下,六个问题不吉利。所以,我们必须麻烦你,再回复我们一个问。不过这个问比较简单,也很好玩。你可以不回答,但不能不回复。一定。我们的这个问题是关于写诗与性的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说,写诗对你的性想象和性行为有没有影响?期待你的回复,多谢多谢。
写诗,对人的身心灵具有决定性与整体性的影响。
黄粱,1958年出生于台北,祖籍福建漳浦。1982年始致志新诗,海内外多家诗刊特约编辑,新诗评论专栏撰述,创立「青铜社」、「青铜诗学会」,筹划汉语诗歌诗学建构纲领,为现代汉诗的文化主体性思维宏谋。著作诗论集《想象的对话》、《大块诗魂》,诗集《沥青与蜂蜜》、《携手独步》,主编《大陆先锋诗丛》等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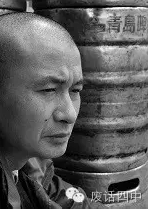
王音回答
一、你认为中国当代诗歌最大的成功是什么?没成功的话那最大的问题又是什么?谢谢你的支持,我等着。
最大的成功在于当代诗歌已经说人话了,已经回到了诗歌的本身--语言艺术上了。如果说还不成功的话,那就是还有许多诗人仍未现代,还在继续巩固既有的不是好诗的路子上,并且这些诗人在主流文坛还有一定的名气,并且这些诗人的作品还在影响着不懂诗歌的广大读者们。当然,这种现象已经正在被改变着,好诗在民间,这是真理,我相信。
二、谢谢你的回答。对于第一个问题,几乎都给了中国当代诗歌肯定。而这种肯定,都和语言紧密联系。那么我想请教你,中国当代诗歌究竟为现代汉语提供了什么新机制和新内容?顺便再问一句,现代汉语和古白话又有什么本质的差异?期待你独特的高见。
当代诗歌为现代汉语贡献很大很大,日常口语、方言、网络语、外来语等的灵活运用和丰富交融,直接影响到了小说写作语言、随笔写作语言等等,极大刺激和扩展了现代汉语的表现力,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日常的鸡零狗碎和各种生活细节已经在一些作品中自然而然地呈现着。
时代背景的不同,汉代汉语和古白话有很大区别,但语言文化是有源头的,在它漫长进化流变中,古白话和现代汉语还是有一点关联的。
三、很好,谢谢你的回复。在做这个微访谈时,我们在白话诗、新诗、现代诗、现代汉诗和当代诗歌等好几个词语中费了许多脑筋,总觉得没有最为准确的叫法。说新诗吧,那它针对什么旧呢?而且已经100年了,也不能一直这样叫下去。说现代诗歌吧,难道它不包括当代吗?说现代诗,其实好多诗并不现代,难道就要拒绝在这类诗歌历史之外?所以,我们真的很迷茫。所谓名正言顺,为中国百年来新的诗歌找到自己的名字,的确算一个迫切的问题,而且我们还发现,没有准确的命名,应该是中国现当代自由白话新诗最大的隐患。对此我们再次期待你的高见,找到最准确的说法。
现代诗,当代诗歌,现代汉诗,或者叫自由诗都可以,怎么顺口怎么叫吧。真正界定我们的诗歌名称,一定是后人写文学史的事了。
四、好的,你的说法有道理,但你也知道这样一个事实:这种诗,我们已经写了100年了。100年好像不长,但肯定也不短。亲,就你的阅历和学识,在这100里,有哪些诗人、哪些作品、哪些事件和哪些关于诗的言说,你认为是有价值的?有发展的?至少是你记得住的?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必定是一个关于诗歌100年历史的访谈。辛苦,辛苦。感谢,感谢。
现代诗歌草创期,郭沫若、戴望舒、卞之琳等诗人的几首作品是不错的,尤其小说家废名的诗写和言说,今天看来,他是继白话诗开山人胡适之后,贡献最大的一位。四九年至文革结束这一时期,我们只能读读台湾的纪弦、商禽,瘂弦等诗人的某些东西,以北岛为首的朦胧诗崛起以后,特别是第三代诗人的集体崛起,汉语诗歌有了崭新的面貌,韩东、杨黎、于坚、何小竹、于小韦、吉木狼格、周亚平、李亚伟、小安等诗人的作品为证。当代诗歌真正的成熟期,就是互联网在中国的这十五年,几代诗人在作品面前已经是一代了,我称之为网络的一代,前有互联网的橡皮写作群、下半身、垃圾派等流派群体,后有独立的专业纸质《橡皮》、《自便》、《Z诗选》、《汉诗》、《读诗》、《自行车》、《借来的诗》、《中国诗人村》、《地下》、《中国诗歌排行榜》、《今天》、《明天》、《扑克诗选》、《新诗典》、《泉诗刊》等。当下的诗歌力量以60后70后为中坚,80后已经崛起,90后也正在崛起,还剩下几个50后的诗人也仍在状态中,比如阿坚、严力、文康、凡斯等,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几代诗人一起共同创作的时代,伟大的互联网和伟大的民间独立诗刊的互动和推波助澜,当代诗歌已经蔚然成风了,我个人以为当下的现代汉语诗歌已呈现了“盛唐气象”。
杨黎与韩东当年的诗学论争对诗歌的发展有影响,杨黎和成都诗人、山东诗人及青岛诗人在2010年的青岛搞诗会是个事件,不仅引起不小的骚动和非议,某种程度上说,随之也吸引了诗人小招迅速来到青岛。。。。。。
杨黎和束晓静的以一年为期限的每日写诗双修计划,是个事件,某种意义上说,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诗歌文本,这已经是一件集诗歌、互联网技术、行为艺术、概念艺术、观念艺术为一体的先锋艺术作品了。
我从第一波就开始读和转发杨黎和李九如编著的《白话百年中国当代诗歌百人微访谈》了,我发现这其中兼容并包了各个流派、各种人物,可谓聚集了中国诗坛优秀的男女老少,包括海外的汉语诗人。这种现场感、文献性以及诗学意义是很大的,影响将是深远的,我认为。
五、谢谢你回复,让我们的访谈很有价值。在前面四个问题之后,我们觉得有一个绝大的问题必须摆到桌面上来:这个问题,就是诗歌的标准问题。诗歌到底有没有标准?或者说有没有唯一的永恒的标准?笼统而言,“古代诗歌”似乎是有标准的;而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白话入诗,诗歌事实上陷入一种先验的迷惑中:它至今也没有完全确立自身,或者说,它需要像中国古代诗歌一样,确立一个标准码?说白了吧,上追千年下启万世,到底什么是“诗”?期待你指教,并先谢。
诗歌与其它的艺术品种一样是有标准的,并且是有绝对的标准的。不好的诗有N种理由,而好诗却无需理由,好诗就是好诗,因为好诗是没有道理的。诗啊,妙不可言。
六、谢谢你。关于中国百年诗歌的访谈,问题还多,但已大致有数。这里,我们想用一个古老的问题作为我们访谈的结束,那就是你为什么写诗?或者说是在今天,世界已经发生了那么大的改变,而你为什么还写诗?写诗,对你究竟有什么好处?
我是中国年纪最大的年轻诗人,我出道比许多90后诗人还晚,但我一出手,就在高处写。我写诗,看似偶然,其实却是冥冥之中的事儿。因为音乐与诗歌同源嘛,再说了,作为母语的诗歌对我的影响,肯定要早于音乐。写诗的好处,对我来说就是身心舒服,既可以打发无聊的日子,也可以解构虚无,当然同时又重构了虚无,这是一种高级游戏,我喜欢。
七、哇,各位大侠:访谈完了,我们才发现是六个问题。而我们算了一下,六个问题不吉利。所以,我们必须麻烦你,再回复我们一个问。不过这个问比较简单,也很好玩。你可以不回答,但不能不回复。一定。我们的这个问题是关于写诗与性的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说,写诗对你的性想象和性行为有没有影响?期待你的回复,多谢多谢。
诗性,诗性也【哈哈哈哈】
王音,1963年生于青岛,1987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音乐系。诗人、艺术家、作家、啤酒文化研究者、青岛摇滚乐开创者。著有随笔集《青岛符号.》、《青岛符号续集》、摄影专题《啤酒屋里的青岛》、《母亲》等。诗歌代表作《D大调的心情》、《其实萨拉班德是一个悲伤的名字》、《自由》、《世界》、《父亲》等。
全部微访谈版权归“废话四中”所有
转载请联系编辑
未经同意请勿转载,谢谢
往期回顾:
重磅:白话百年中国当代诗歌百人微访谈(一) || 于坚、谭克修、小安
重磅:白话百年中国当代诗歌百人微访谈(二) || 孙文波、周亚平、李亚伟
重磅:白话百年中国当代诗歌百人微访谈(三) || 韩东、春树、徐敬亚
重磅:白话百年中国当代诗歌百人微访谈(四) || 余怒、杨小滨、汤巧巧
重磅:白话百年中国当代诗歌百人微访谈(五) || 俞心樵、叶匡政、文康
重磅:白话百年中国当代诗歌百人微访谈(六) || 邵风华、不识北、而戈
重磅:白话百年中国当代诗歌百人微访谈(七) || 束晓静、孙基林、马策
重磅:白话百年中国当代诗歌百人微访谈(八) || 祁国、张执浩、高星
重磅:白话百年中国当代诗歌百人微访谈(九) || 刘不伟,郎启波,尚仲敏
重磅:白话百年中国当代诗歌百人微访谈(十) || 潘洗尘、彭先春、李霞
重磅:白话百年中国当代诗歌百人微访谈(十一) || 魏天无、秦风、何小竹
重磅:白话百年中国当代诗歌百人微访谈(十二) || 牧野、孙智正、杨海明
重磅:白话百年中国当代诗歌百人微访谈(十三) || 李强、张羞、蒲秀彪
重磅:白话百年中国当代诗歌百人微访谈(十四) || 张岩松、陆渔、老巢
重磅:白话百年中国当代诗歌百人微访谈(十五 ) || 李昕、乌青、秦匹夫
重磅:白话百年中国当代诗歌百人微访谈(十六 ) || 方闲海、袁玮、管党生
重磅:白话百年中国当代诗歌百人微访谈(十七) || 王九禾、消除、孙磊
重磅:白话百年中国当代诗歌百人微访谈(十八) || 小引、黄贵奇、周瑟瑟
重磅:白话百年中国当代诗歌百人微访谈(十九) || 杨瑾、法清、魔头贝贝
重磅:白话百年中国当代诗歌百人微访谈(二十) || 向卫国、朱庆和、贾冬阳
重磅:白话百年中国当代诗歌百人微访谈(二十一) || 宇向、晓音、朵渔
重磅:白话百年中国当代诗歌百人微访谈(二十二) || 刘波、陈亚平、面海
重磅:白话百年中国当代诗歌百人微访谈(二十三) || 沈浩波、轩辕轼轲、凡斯
重磅:白话百年中国当代诗歌百人微访谈(二十四) || 刘洁岷、金汝平、周凤鸣
重磅:白话百年中国当代诗歌百人微访谈(二十五) || 石头、艾先、大头鸭鸭
重磅:白话百年中国当代诗歌百人微访谈(二十六) || 道辉、玩二、紫丁

长按二维码,关注杨黎束晓静“远飞”诗日记

编辑:@窈窕束女 athenashua
投稿邮箱:351607@qq.com
来源:废话四中(原创)


 纯贵坊酒业
纯贵坊酒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