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语者”鲁亢
【刘晓萍荐书之鲁亢《被骨头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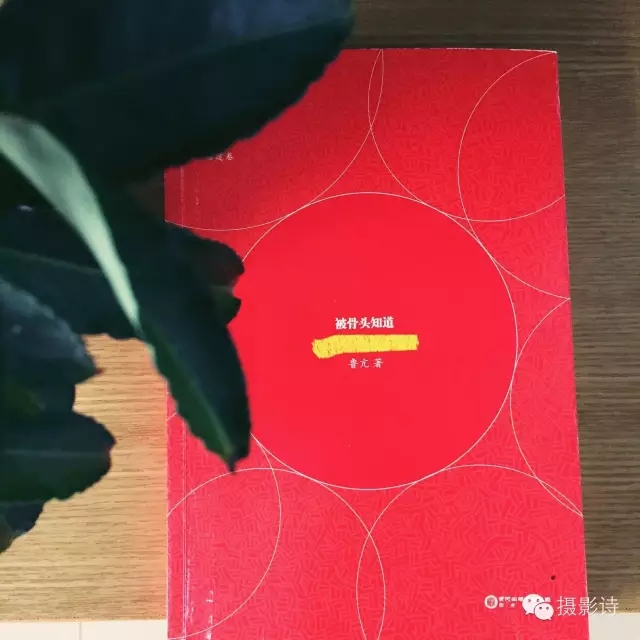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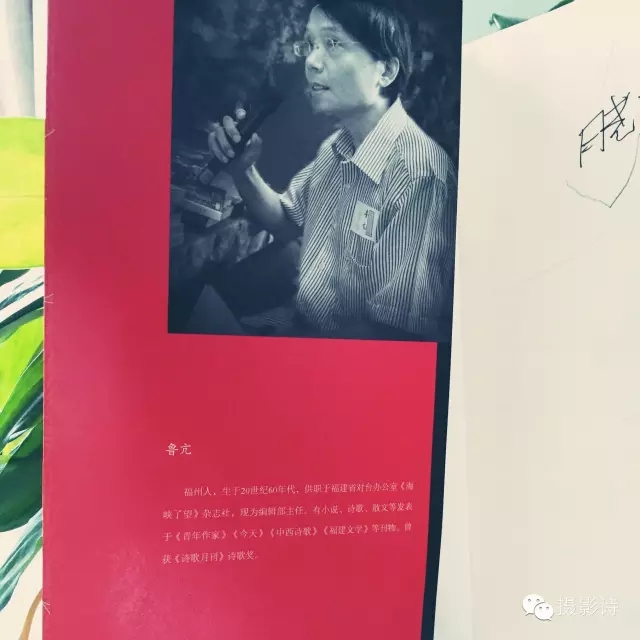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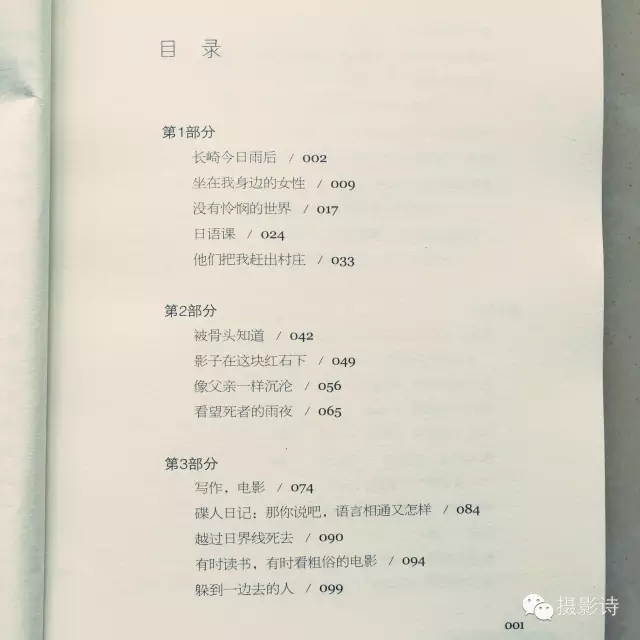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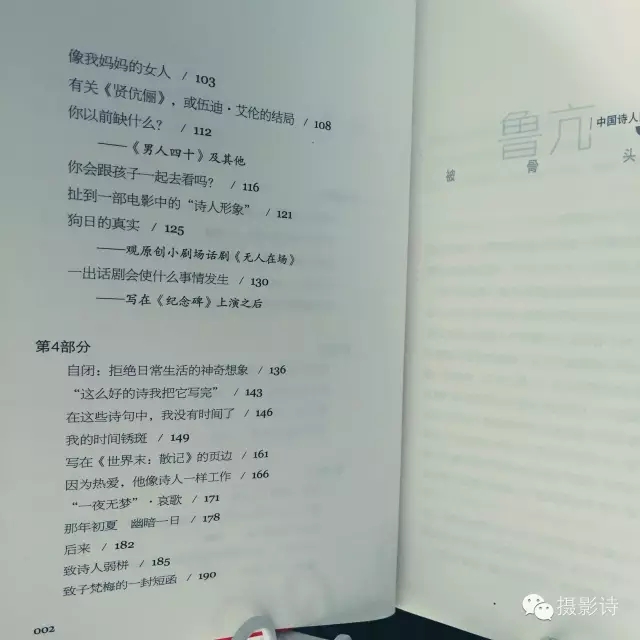
鲁亢这本暂且叫做随笔集,名为《被骨头知道》的新近出版物,我认为是难以定义的。虽然书名来自其中一篇交织着父子关系和生理病痛的“被骨头知道”,但这个书名明显是诗歌意象,而且是深度意象。我们都知道骨头意味着什么,这个人体中最具精神性的组织,许多时候意味着生命最坚硬的底线和与生活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我最想说的是,鲁亢这本《被骨头知道》是当下中国文学文本的一个另类,是跨文体写作的一个特列。它交织着作者对自我履历旁观式的自述、广泛阅读而带至的文本与文本的互渉、小说的叙述方式、诗歌的语言以及很难在随笔作品中产生的戏剧效果。
实际上,它是诗歌、随笔、小说、评论的跨文体实验。每一篇都可当做小说来读,即便是他写的电影评论,也可看作是电影评论界的“梦的解析”。在我看来,他根本就不想好好写什么“随笔”,他更乐于在其阅读的经验库中随意拉出来一个“潜语者”,他非常善于讲“故事”,而每一个故事都有伍迪艾伦式的超现实效果,把悲剧和喜剧融为一体。而他本身所具有幽默感总是让你在阅读过程中产生面聊的现场感。无疑,在如芸的写作者中,鲁亢是很难被发现也很难被埋没的“少数人”。这本《被骨头知道》只是他全部写作生涯的一个侧影,我不知道他当初自选稿时是否有考虑“阅读性”,而将其更加“晦涩”更加“不可忽略“的文本藏于深阁?
附:节选
《被骨头知道》
鲁亢/文
最后呼吸会停止,可能难免巨痛,也可能比较平静。医生说,应该不会那么可怕。医生还说了一件事,“有一位病人让人从五楼搬到六楼,他一上来就死了。”死了(用我母亲的话叫“去极乐世界”),对此医生只比我少了一点紧张,但比我多很多认识。我错过了一个机会,一天一位当年介绍父亲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辗转得到消息后来到病房。“他一定比较老?”我问母亲。原来他们年龄相近,他先参加的革命,父亲是他后来发展的“走上革命道路”的人们中的一员。看着瘦骨嶙峋的父亲,他对屋里的其他人,回顾了颇长的一段往事。父亲还有说话的力气,但他一言未发。在近乎弥留之际的那个头脑中,回忆是奢侈的,但想必还能接纳零星的回忆之磷火,摇曳着通往阴间的漫漫长路。一个去找那位老同志的念头一闪而过。父亲虽非权贵,但他早年的“干革命”对我颇富传奇。我在书堆中找十几年前读过的《阿尔米特奥·克罗斯之死》(〔墨西哥〕卡洛斯·富恩特斯著,亦潜译),我模糊地感到这本书能使我所知极少的“传奇”被托付其中加以想象,比如书的开头部分:“我醒了过来……把我弄醒的是同我身体接触的这件冰冷的东西。我原先不知道,有时人是会不由自主地撒尿的。”就是父亲当下的情景,他清醒时又会因片断回忆的冲撞倦极而眠。我还希望这本书能挑起我去了解父亲更多。但也难说,因为我对自己的冷漠并不怎么吃惊。有关父亲年轻时的一段经历…… 有关我父母的一切…… 我的父亲母亲……我很迷惑,我和父亲之间谈不上亲近,不是非常熟悉。我有一些小时候的记忆,青年时期的几个深刻印象,其实都糟糕透顶,那只是让一位失败者的人生轨迹更加清晰。这么多年来我们都在苦熬,这种纯属个人的判断是维系在我们之间的“情感纸带”,“风稍猛一点它就会断,飘走了”。我基本上能接受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一开始那没心没肺的独白,而不必强调自己“我,一个局外人,感到畏惧在一个根本不是我创造的世界里……”我们想都没想过去创造什么,找一处容身之地已属不易。这样的父与子,沉默是比较认真的选择。
癌症使他返生无望。这时候的他犹如搭上计程车,“哪儿都不去,码表依旧在跳”。我们只看到他身上本来就不多的肉越发减少。他要替还能活着的每一天支付掉的只有它了。皮肤已皱得有点像假的,仅仅骨头还保持原来的重量,并没有“轻得可以抛将起来”,起码我想整个抱起来替他翻个身还很吃力。不知他是否有点愠怒,我们的样子都像陷入思考,他已无力配合:窝囊废呵,养你何用。
我思考这一场癌症,在这位病人身上,延伸出什么样的隐喻。“在隐喻的意义上,癌症是一种内在的野蛮状态”(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就引起我去思考疾病的隐喻,同时又对每天得知的病况束手无策,我发现自己对苏珊·桑塔格的书熟悉乃至想念,会带来心态的平衡。这相当不幸,父亲离我有时比书还远一些。我不知道父亲怎么得的这种恶疾。因为吸烟?环境污染?吃的好或活太长?后两种在专家看来也是癌症的起因。父亲第一次因胃癌开刀前曾说:“怎么会是胃,我平常吃东西都是非常小心。”他吃的并不好。几年前就戒烟了。他也许算长寿,那是古代的标准:人生七十古来稀。其实我对解析病因相当恐惧。反而是一本有关疾病所含有的种种隐喻的著作,让我对这种常见的、致命的疾病,为能找到非医学上的解释、能使我游离出去而有所期待。我期待属于自己发现的隐喻能出现,如若不然,那么找到符合书上所提到的最有力的一个隐喻。像,“癌症是一种内在的野蛮状态”。
你可以用药物抑制住它,但它最终还是占了上风。它衰竭你,抽干你。痛不欲生,你活活变成尸体。
“一种内在的野蛮状态”,由此我想到另一个问题:是什么使父亲成为一个性格粗暴的人?在性格粗暴的群体中他不算典型,但也够呛,我感到难堪:哦,原来我的父亲也是这样。可以给出的解释或猜测是:父亲自小没有得到爱护;年轻时愤世嫉俗;中年之后郁郁不得志;晚年生活枯燥。他远比我耽于阅读,却离不开电视和收音机,对后者他还习惯接收外台。他是如此不信任这个社会,他万念俱灰,却无法丢弃“天父的面具”。对现实生活他没有积极的态度,思想上又不能超脱,以至于莫名其妙地变成了老“愤怒青年”。粗暴成了他永远的自卫武器。当他感觉到生命面临严重的危险,发现自己已不那么坚强;孱弱,无助,但暴怒的性格本质仍像一场火灾中的暗火,不知何时复燃。一旦复燃实在让人讶异:这里面到底压抑着多大的失败和空虚的感情,谁是他在世的最大的仇人,是命运还是天空?在一部工具书里,两位法国学者就“父亲”作为象征体的那一部分的阐释,为抽离沮丧的现实的人们,能平静地把父亲当作“研究的对象”提供了渠道:“父亲的作用就是阻止一切争取解放的努力,施加影响以便剥夺、限制、刁难、扼杀那种努力,并且维持隶属关系。他代表与本能冲动、自发激动和无意识相对立的觉悟,这是与促成转变的新生力量相对立的传统和权威世界。”仁慈和理解不为权威世界所容,形同被追杀的仇家的遗孤,四处躲藏,而内在的野蛮状态已形成外在的专制力量。
一个失败的儿子同时也将他的父亲视为失败者,并加以谴责。他少年时的几个与父有关的美好片断“正露出孤独的表情”。父亲的积极的形象在哪里?他想象自己做到了洁身自好不求人。他是人欲横流的社会中的一个小人物,一个“套中人”,他靠什么来反思,来洗心革面似地改变?他的信仰(有吗,或曾经有过?),在只有权力这种最好的兴奋剂才能使人找回一点“精神”的社会里,早就一文不值。他根本就没有过属于他这类人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一旦我们无限地放大某种所谓的“具有普世价值”的情结,其中饱含个体悲剧色彩的生命迹象,就失去了被真实讲述的可能。他最真实的一面是无法自控的际遇,反而使他相信能一以贯之地奉行超理想的为人准则。而且他不能接受你的质疑。你怀疑什么呢?“人类和他的愚蠢的行为会继续存在下去和蓬勃发展”,但你还应该相信“人是不可摧毁的,因为他有争取自由的单纯思想”。争取自由的思想给父亲同外人不大一样的形象,但也仅仅存在于我的思考之中,回到现实的一幕幕你只能感受到无边的防火墙。争取自由是多么荒唐的自我期许,在虚假的诱因里它被假想为精神囚笼中的睡狮,并认为可以唤醒,而它最终的表现及所达到的目的,往往使自由思想的尊严遭到损伤,因为真理已被扭曲,假象找好了位置,正挥舞着驯兽鞭。我更愿意不去理会父亲们的“争取自由”的“口水”,因为现实中父亲们已被简单地分为“瘦身型”和“肥胖型”,对这两种类型的个性界定因其可验证而使父亲们的“天父面具”得以揭开,回到首先是作为凡人的地位。如果他是瘦身型的,多具有分裂性气质,孤独,自闭,不爱社交,不现实;如果他是肥胖型的则具有循环性气质,亲切,现实,乐于社交和助人,爱好享受。我的父亲是瘦身型的,现在,他还是癌症患者,这样的患者“是些低速档的人,很少受情感爆发之害。自孩提时代起,他们与父母就有一种疏离感”。假如撇开父亲的精神生活不谈,他的个性就变得千篇一律,粗暴不过是这一类型的人之共有的“世界观”,没有隐喻上的意义。对于大多数的癌症患者,纽约的心理学和心理治疗专家苏伦斯·勒山在他1977年发表的著作(《为生活而斗争:癌症起因的情感》)中认为“普遍存在着一类人格构成”。他把“癌症患者的基本情感模式”划分为三种:“童年期或青少年期,其标志是疏离感”;成人期,其标志是“有意义的关系”的缺失;最后是“认定生活毫无意义”。劳伦斯·勒山写道:“癌症患者几乎无一例外地瞧不起自己,瞧不起自己的能力和潜力。”癌症患者“没有情感和自我”。父亲可以对号入座,就他的每一个时期,我也能隐约想起一些事来补充。他要是知道了会恼怒不已。也许他不会?我们来设想另外一种可能:他对儿子的想自浑沌到有序的明显是力不从心的探索,故作冷静的分析,表现出有限度的忍耐。他说出这样的话——如威廉·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里的主人公艾迪·本德仑的父亲对她常说的——“活着的理由就是为长期的死做好准备”。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父亲多半充当“朝闻道,夕死可矣”的伟大的、乐天的角色,即便他是那么的不够幸运,他克尽职守却并未让人感到快乐。
这已经不可能了。我也从未去想我们在精神上能否达到和解是重要的事。我们之间的不太了解在我看来不算太坏,这样就不必为对方的景况太过费心。他承担了养育的责任,我则在他身边守到最后。我们相对无言,我们的内心世界过于苍白,我们只记住了对方。他间隔几个小时就会被疼痛折磨一番。对杜冷丁的依赖使他不是很痛时也喊着要注射。有几天护士不得不用吸管将浓痰吸出,让他能咳得上来。每天定量的挂瓶造成新的扎针口越来越难找,血管加速硬化。我还听说有一种止痛药,从血管注射进去能坚持二至三天。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竟松了一口气。我还为父亲的每天高昂的医疗费能够全部报销而暗呼庆幸。这就是那条“革命道路”给他留下的“路费”。如此说来父亲还不是一个可以让你随便看不起的人,在这一点上他甚至可以轻视你。医院是一个讲等级讲金钱的场所,如果你付不起那么多的费用,医生就没有什么作用,你到这个时候就会死了心地认识到自己是流浪狗。这种事很多,父亲不在此列。父亲可以冷冰冰地看着我,甚至微笑(如果可能),“你是我的混蛋。”
我离开,他躺着。“谁比谁更好,只有天知道”。他其实还是很坚强,不与死神合作,不给等候的人准确的归期。虽然没人敢告诉他真实的病症,他恐怕也已猜到,但他沉默不语。他留意四周的动静,说话声,有时还开口纠正(“那是我订的杂志,邮递员搞错了。”我一头雾水)。有一次他将隔壁阳台上收衣服的声音误以为屋里有老鼠,突然嘴里发出“咄咄”的驱赶的声音。这声音很世俗化,很日常,死神听见了也会放缓步伐。可是父亲已死去很多,从肉到血液,从记忆到意志,只有骨头在撑着,像撑着一把破伞在毒日头下。只有他的眼睛流露出短暂的不舍之意,我不知是否猜对,也许那仍是怒火,只是在快熄灭前的黯淡微光。我离开。痛,很痛。
我在公车上看着窗外的建筑物,喧闹的白天,或乏味的晚上,我只想快快回到家。
梅艳芳在临终时得知癌细胞已扩散,再也保不住那副嗓子,她说:“既然这样,那我走了。”
既然这样,生命之水淤滞不流,死亡就来了。


 纯贵坊酒业
纯贵坊酒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