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烈祝贺《新诗潮》创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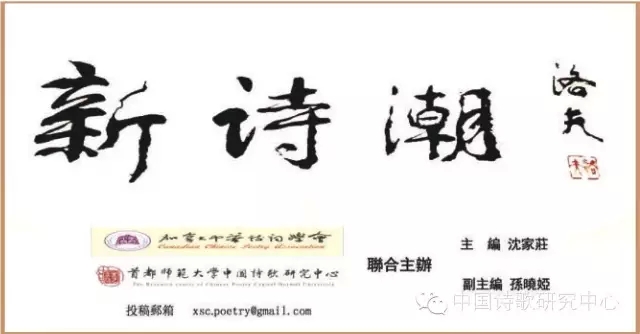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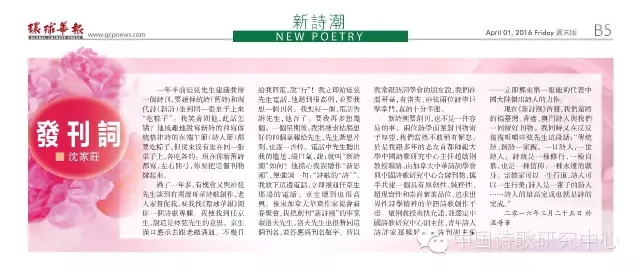
加拿大华文报刊《环球华报》新开《新诗潮》专栏,由加拿大中华诗词学会和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主编沈家庄,副主编孙晓娅,投稿信箱:xsc.poetry@gmail.com,敬请各位诗人方家惠赐大作!
發 刊 詞
沈家莊
一年半前瘂弦先生建议我辦一個詩刊,要让传统诗(旧詩)和现代诗(新诗)坐到同一張桌子上來“吃粽子”。我笑著問他,此話怎講?他風趣地說寫新詩的和寫传统格律詩的在端午節(诗人节)都要吃粽子,但從來沒有坐在同一張桌子上,各吃各的。現在你新舊詩都寫,左右開弓,你要把這個刊物辦起來。過了一年多,有機會又與瘂弦先生談到有關溫哥華詩歌創作,老人家督促我,要我找《環球華報》開辟一個詩歌專欄。我便找到任京生,說這是瘂弦先生的意思。京生滿口應承去跟老總溝通。不幾日給我回電,說“行”!我立即給瘂弦先生電話,他聽到很高興,并要我想一個刊名。我想好一個,電話告訴先生,他否了。要我再多想幾個。一個星期后,我將搜索枯腸想好的四個稟報給先生,先生默想片刻,也逐一否掉。電話中先生聽出我的尷尬,緩口氣,說:就叫“新詩潮”如何?他擔心我誤听作“新思潮”,便強調一句:“詩歌的‘詩’”。我放下這邊電話,立即撥通任京生那邊的電話。京生聽到也很高興。後來加拿大華裔作家協會新春聚會,我把創刊“新詩潮”的事稟報洛夫先生,洛夫先生也很贊同這個刊名,并答應爲刊名題字。所以我常跟詩詞學會的朋友說,我們在溫哥華,有洛夫、瘂弦兩位詩學巨擘掌門,真的十分幸運。
新詩潮要創刊,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兩位詩學前輩對刊物寄予厚望,我們當然不敢稍有懈怠。於是我跟多年的老友首都師範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主任趙敏俐教授聯絡,由加拿大中華詩詞學會與中國詩歌研究中心合辦刊物,攜手共建一個具有原創性、純粹性、超現實性和崇尚審美品位、追求世界性詩學精神的華語詩歌創作平臺。敏俐教授爽快允諾,并選定中國詩歌研究中心副主任、青年诗人诗评家孫曉婭作為詩刊副主編——立即郵來第一組能夠代表中國大陸傑出詩人的力作。
現在《新詩潮》首發,我們還將約稿台灣、香港、澳門詩人與我們一同辦好刊物。我同時又在反反復複咀嚼瘂弦先生這段話:“传统诗、新诗一家亲。一日詩人,一世詩人。詩就是一種修行,一種自慕,也是一種信仰,一種永遠的獻身。宗教家可以一生行道,詩人可以一生行美;詩人是一輩子的詩人……詩人的最高完成也就是詩的完成。”
二零一六 年 三月二十五日 於溫哥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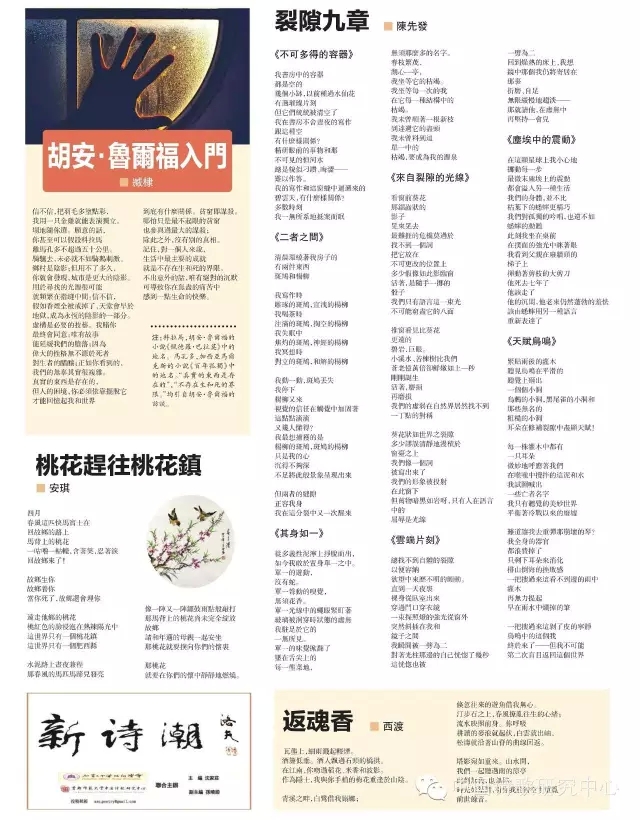
首刊所发诗歌文本如下:
《裂隙九章》
陈先发
《不可多得的容器》
我书房中的容器
都是空的
几个小钵,以前种过水仙花
有过璀璨片刻
但它们统统被清空了
我在书房不舍昼夜的写作
跟这种空
有什么样关系?
精研眼前的事物和那
不可见的恒河水
总是貌似刁钻、晦涩——
难以作答。
我的写作和这窗缝中逼过来的
碧云天,有什么样关系?
多数时刻
我一无所系地抵案而眠
《二者之间》
清晨环绕着我房子的
有两件东西
斑鸠和杨柳
我写作时
雕琢的斑鸠,宣泄的杨柳
我喝茶时
注满的斑鸠,掏空的杨柳
我失眠中
焦灼的斑鸠,神经的杨柳
我冥想时
对立的斑鸠,和解的杨柳
我动一动,斑鸠丢失
我停下
杨柳又来
视觉的信任在触觉中加固着
这点点滴滴
又几人懂得?
我最想捕获的是
杨柳的斑鸠,斑鸠的杨柳
只是我的心
沉得不够深
不足将此般景象呈现出来
但两者的缝隙
正容我身
我在这分裂中又一次醒来
《其身如一》
从多义性泥泞上挣脱而出,
如今我敢于置身单一之中。
单一的游动,
没有蛇。
单一耸动的嗅觉,
无须花香。
单一光线中的蝇眼紧盯着
玻璃被洞穿时状态的虚无
我驻足于它的
一无所见。
单一的味觉掀翻了
压在舌尖上的
每一垄菜地,
无须那么多的名字。
春枝繁茂,
湖心一亭,
我坐等它的枯竭。
我坐等每一次的我
在它每一种结构中的
枯竭。
我未曾顺着一根新枝
到达过它的尽头
我未曾料到这
单一中的
枯竭,要成为我的源泉
《来自裂隙的光线》
看窗前葵花
那锯齿状的
影子
晃来晃去
最难捱的危机莫过于
找不到一个词
把它放在
不可更改的位置上
多少假象如此影临窗
活着,是随手一掷的
骰子
我们只有语言这一束光
不可能穷尽它的八面
推窗看见比葵花
更远的
碧岩,巨眼。
小溪水、苦楝树比我们
苍老亿万倍却鲜嫩如上一秒
刚刚诞生
活着,磨损
再磨损
我们的虚弱在自然界居然找不到
一丁点的对称
葵花状如世界之裂隙
多少谬误清静地漫积于
窗台之上
我们像一个词
被写出来了
我们的形象被投射
在此窗下
但万物暗黑如岩呀,只有人在语言中的
屈辱是光线
《云端片刻》
总找不到自体的裂隙
以便容纳
欲望中来历不明的颤动。
直到一天夜里
裸身从卧室出来
穿过门口穿衣镜
一束探照灯的强光从窗外
突然斜插在我和
镜子之间
我瞬间被一劈为二
对着光柱那边的自己恍惚了几秒
这恍惚也被
一劈为二
回到燥热的床上,我想
镜中那个我仍将寄居在
那里
折磨、自足
无限缓慢地趋淡——
那就请他,在虚无中
再坚持一会儿
《尘埃中的震动》
在这颗星球上我小心地
挪动每一步
最微末尘埃上的震动
都会溢入另一种生活
我们的身体,并不比
枯叶下的蟋蟀更精巧
我们对孤独的吟唱,也远不如
蟋蟀的动听
此刻我坐在桌前
在扑面的强光中眯着眼
我看到父亲在废墙头的
梯子上
挥动着剪枝的大剪刀
他死去七年了
他该走了
他的沉闷,他老来仍然蓬勃的羞怯
该由蟋蟀用另一种语言
重新表达了
《天赋鸟鸣》
紧贴雨后的灌木
听见鸟鸣在平滑的
听觉上砸出
一个个小洞
乌鸫的小洞,黑尾雀的小洞和
那些无名的
粗糙的小洞
耳朵在修补裂隙中尽显天赋!
每一株灌木中都有
一只耳朵
微妙地呼应着我们
在喉咙中搅拌的这泥和水
我试图喊出
一些亡者名字
我只有听觉的美妙世界
平衡着冷战以来的废墟
难道让我去重弹那崩坏的琴?
我全身的器官
都浪费掉了
只剩下耳朵来消化
排山倒海的挫败感
一把搂过来这看不到边的雨中
灌木
再无力提起
早在雨水中烂掉的笔
一把搂过来这剥了皮的宁静
鸟鸣中的这个我
终于来了——但我不可能
第二次盲目返回这个世界
《胡安·鲁尔福入门》
臧棣
信不信,把羽毛多涂点彩,
我用一只金鸡就能表演独立。
场地随你选。愿意的话,
你甚至可以假设科拉马
离马孔多不超过五十公里。
骑驴去,未必就不如骑鹅刺激。
乡村是阴影;但用不了多久,
你就会发现,城市是更大的阴影。
用于寻找的光源很可能
就频繁在指缝中间:信不信,
假如香烟全被戒掉了,天堂会早于
地狱,成为永恒的阴影的一部分。
虚构是必要的技艺。我赌你
最终会同意:唯有故事
能延缓我们的堕落;因为
伟大的性格无不源于死者
对生者的酝酿;正如你看到的,
我们的无辜其实很复杂。
真实的东西是存在的,
但人的困境,你必须依靠摆脱它
才能回忆起我和世界
到底有什么关系。贫穷即谋杀。
哪怕只是最不起眼的贫穷
也参与过最大的谋杀;
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真相。
记住,对一个人来说,
生活中最主要的成就
就是不存在生和死的界限。
不出意外的话,唯有绝对的沉默
可导致你在无尽的痛苦中
感到一点生命的快乐。
注:科拉马,胡安·鲁尔福的小说《佩德罗·巴拉莫》中的地名。马孔多,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百年孤独》中的地名。“真实的东西是存在的”,“不存在生和死的界限。”均引自胡安·鲁尔福的访谈。
《桃花赶往桃花镇》
安琪
四月
春风这匹快马奔驰在
回故乡的路上
马背上的桃花
一咕噜一轱辘,含着笑,忍着泪
回故乡来了!
故乡生你
故乡养你
当你死了,故乡还会埋你
远走他乡的桃花
桃红色的脸浸泡在热辣阳光中
这世界只有一个桃花镇
这世界只有一个肥西县
水泥路上昼夜兼程
那春风的马匹马蹄儿发亮
像一阵又一阵锣鼓雨点般敲打
那马背上的桃花尚未完全绽放
故乡
请和年迈的母亲一起安坐
那桃花就要扑向你们的怀里
那桃花
就要在你们的怀中静静地燃烧。
《返魂香》
西渡
瓦垄上,细雨溅起轻烟。
酒帘低垂。酒人飘过石头的桥拱。
在江南,你吻过稻花、米香和波影。
作为隐士,我与你手植的梅花重逢于山阴。
青溪之畔,白鹭借我袅娜;
倏忽往来的游鱼借我无心。
汀步石之上,春风撩乱往生的心绪;
流水映照前身。你呼吸
耕读的麦浪就起伏,白云就出岫,
松涛就沿着山脊的曲线回返。
塔影宛如重来。山水间,
我们一起听过雨的凉亭
此刻无我,也无你。
时光如笙箫,引你我于清空中重觅
前世余音。
本刊投稿信箱:xsc.poetry@gmail.com,主编沈家庄,副主编孙晓娅,敬请各位诗人方家惠赐大作!
来源:沈家庄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纯贵坊酒业
纯贵坊酒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