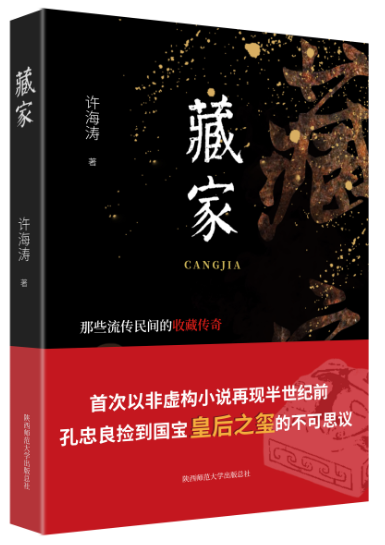
《藏家》:守住文化根脉 讲好中国故事
——《藏家》作者许海涛访谈
——《藏家》作者许海涛访谈
记者:发现“皇后之玺”是半世纪前的故事,您为什么现在把它写出来,并做为《藏家》开篇之作?
许海涛:文学的秘密往往与故乡和童年有关。1968年,13岁小孩儿捡到国宝“皇后之玺”的传奇,生于1969年的我,打小就听进了肚子里。我家就在五陵原上,距皇后之玺发现地十多公里。半个世纪的发酵,这则传奇依然浓烈而又新鲜,要“溢”出来了。2018年,坐在夏夜长陵顶的凉爽里,我跟孔忠良——皇后之玺的发现者,13岁的小孩儿已经是63岁的老人了——聊了三个晚上,聊得很透,像透过密实的封土,看见长陵埋藏的所有秘密。陪伴我俩的,除了满天的星斗,更多的,是五陵原的风,两千多年幽幽的风……七天后,在孔忠良家不怎么明亮的电灯泡下,我用尽浑身本事,声情并茂,用秦腔把《皇后之玺》朗诵了一遍。孔忠良叫道:“没麻达,就是这!”介绍我认识孔忠良的唐顺陵文管所副所长李小勇跟着叫道:“许哥,写得美!”那一刻,没有词语形容我内心的波澜。就像五陵原上的黄土,我一直找不出词语来表达我的敬仰。
记者:《皇后之玺》最大的特点是非虚构性,故事中的人和物都有迹可寻。孔忠良作为事中人,他对《皇后之玺》是怎样评价的?
许海涛:在12月15日举行的《藏家》新书发布会上,孔忠良说:“这几年,采访我的记者多,包括中央电视台。说实话,那么些记者,就数许海涛问得细,细得不能再细,把我都给问箍住了。我负责任地给大家说,捡到皇后之玺上交国家的全过程,今后就再别问我了,以许海涛写下的书为准。”
记者:您三年时间接连出了三本书:《跑家》、《残缺的成全》、《藏家》,每一部作品都与民间收藏有关,为什么?
许海涛:写你手触的东西。我是跑家里的写作者,写作者里的跑家。作为跑家,走村入巷、挨门进户收古董,发现、搜集、保护历史的遗存;作为写作者,透过时间镌刻的包浆,挖掘一件件古董老物背后的人情冷暖、喜怒哀乐,并记录下来。《跑家》,写了一群民间寻宝人的故事。《残缺的成全》,展现了一位民间收藏家的精神追求。《藏家》通过13个“老古董”的故事,穿过历史的沧桑,领悟生命真正的意义和生活的本真。我愿意是跑家,发现更多的历史遗存,挖掘更多的传奇故事。我更愿意是写作者,用地道的乡土语言,讲述每一件“老古董”的前世今生,看见根脉的执着,唤醒人们心底的乡愁。
记者:采访中,我们发现一种现象,有些中小学生也是您的粉丝。他们特别喜欢《跑家》和《藏家》,说看您的书像是上历史文化课,生动有趣。请问:在通过文学作品讲好中国历史故事这方面,您有怎样的考量?
许海涛:您发现的这个现象,让我惊喜。对历史过往的好奇,萦绕于心的乡愁,不光是大人的专利,孩子们一样拥有。孩子们更愿意看到“形象”的历史。历史教科书上的一句概括,在我的小说里,可能是一枚印,一幅画,一片瓦当,一尊石刻。这些印、画、瓦当、石刻正是历史的细微,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综合信息。也可以说,历史光影的回照,正好镌刻在细微的遗存上。孩子们喜欢,大约是在我的小说里看到了历史的某一个侧面,活生生的侧面。正像我在《藏家》自序里所写:一幅画、一枚印、一件家当,像根须,传到如今,还活着,意味着根还活着啊!
通过文学作品讲好中国历史故事方面,我觉得,语言一定是中国的,纯正地道的中国语言;情感一定是中国的,含蓄而又浓烈的中国情感;故事一定的中国的,古老而又生机勃勃的大江南北“长”出来的中国故事。
记者:写作是一件孤独而艰辛的事情。请问您从事写作的初衷是什么?其中遇到过怎样的困惑?又是如何自我突破的?您从中得到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许海涛:我不觉得孤独和艰辛,就像攀登珠峰的人,激情舞蹈的人,沉醉画画儿的人,得到更多的,一定是乐趣。作为跑家,我看见太多的“物质”湮灭、残损在历史的长河里,一点呻吟都没有。唯有文字流传,照亮历史的长夜,让我们看见先人的精彩和磨难。我想,我的文字也会发光的,哪怕只是萤火虫那样微微的光,也会让后人看见我们曾经走过的路程。这就是我写作的初衷。困惑时时有,天天有,不但写作人有,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正常的。我的困惑是怎样精准地、艺术地表达——明明画面就在眼前,就是写不出画面里的精髓,写不出那一股子味儿。这个时候,我不企图突破,唯有等待,离开电脑,喝茶,远望,听音乐……等待,等待,似乎有一个看不见的我,某一刻贴在我的耳边说:“这样写!”于是,键盘停止沉默,显示屏亮了,一河水开了……写作让急躁的我变得安宁,让我的眼睛看的更深、更远,陶醉活着的真实和美好。
记者:您未来有什么写作计划?
许海涛:一辈子一件事。作为跑家,跑更多的路,见到民间更多的奇珍异宝,经历或者听到更多的传奇。作为写作者,讲述更多更好、更有影响的中国故事。


 纯贵坊酒业
纯贵坊酒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