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瑞箫
第一次见戴老师,是十多年前跟着大学恩师,班主任曹惠民老师去戴老师家拜访。其时我已被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录取,师从王文英所长和戴翊老师。因为曹老师和戴老师是华师大研究生同学,同为钱谷融先生弟子,所以我也得以有幸忝列钱门,成为再传弟子。
戴老师非常温和,第一次见面就问我读什么书,写什么文章,从前的一些工作经历,谈话基本围绕工作学习,很少家长里短。印象深的是,戴老师家的书籍从客厅一直铺到卧室,书柜顶天立地。老师身体不太好,可是行动坐卧,手不释卷。另外就是,戴老师父亲,爷爷年事虽高,却写得一手漂亮书法,是书法家协会的老会员,多年修炼,家里挂满了老人的笔墨。书,书法,书香和墨香,老师宽厚的微笑,师母的和蔼,是我这个学生对老师和老师生活的第一印象。
读研以后,跟老师接触多了。老师对工作非常认真,每次上课,都是极其认真仔细备课,将一部当代文学史,讲得头头是道,而我总是马马虎虎,心不在焉,心下只喜诗,一直不喜理论和小说。另外,无论对17年还是对文革那段历史,既隔膜又不感兴趣。那时代的小说,即使作为时代的见证,历史的烙印,也不想再去重读和深究,可是既然自己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那么当代史是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必须去了解和研究。只是由于自己偷懒和麻木,就一直回避思考。仁厚的老师似乎没看出学生缺乏兴趣,仍不厌其烦,希望能还原真实的历史,分析各个作家创作给我们听,呕心沥血,依然孜孜不倦讲课和批改我们敷衍潦草的论文作业。
等讲到80年代以后的小说,审美经验越来越丰富驳杂,新时期以后,尤其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已日臻成熟。我的眼睛也终于睁开了,终于能认真仔细听老师的课。老师是中国小说学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上海中长篇小说的评委,长期从事长篇小说研究,对当代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可谓了如指掌。而我这个喜爱诗歌的人,一看到长篇小说就头大,因为读完一部长篇,实在太耗时费力,还要通读几遍,查寻资料,然后详细笔记,最后加以思考,才能形成一篇几千字的论文,实在是入不敷出,劳民伤财。所以,当老师要求我们读长篇,写评论练笔时,我们就非常躲避和害怕,在上海,大家都太忙了。到了研二,很多同学忙着去找工作考公务员,实在没时间细读长篇。
90年代中,一次偶尔机会我在《人民文学》上读到了小说家李洱的一个短篇《缝隙》,觉得很对口味,一直记忆犹新。后来读研二时,我在复旦图书馆、华师大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找到、复印并通读了李洱所有的作品(其时这位小说家还没正式出版小说集,还没获得大奖,爆得大名),经过努力,我写成了一篇小小论文,交给老师,得到了戴老师大大的夸赞。戴老师是长篇小说的评委和专家,对小说艺术深有研究。老师认为李洱是位非常出色的小说家,而我的小论文,对李洱的点评也十分到位。老师认为我凭借自己的眼光,发现了一位优秀的作家,对我大加赞赏。他希望我扩充论文,继续追踪这位小说家的创作。而老师自己,虽然体弱多病,却从来没有因此耽误过工作,他的成果常常超过健康人。师母说他经常带着大部头小说进医院的血透病室,在很多病人难受难忍时,我的老师边血透边读书,即使在病中,也绝对不拖欠约稿和评审稿,更有多次带病坚持工作,直到完成稿件大病一场的时候。师母每次心疼得掉泪,可也无法阻拦他,只好一边照顾病中老师的饮食起居,一边按照老师开出的书单,忙着把需要的资料从家里和单位图书馆中一一搬运去医院病房。直到老师退休,他还是坚持这样拼命的工作态度,我和师母多次劝阻,甚至威胁他,他每次都笑眯眯地答应不干了不干了,可一转身,又看到他在读书写稿了。有次我以健康为理由阻止他再读长篇写论文,太累人了,可他郑重地对我说,男人,就是要以事业为重。因此,直到他病重后不得已长时间住院,才终于放下了手中的笔和书。
而我不知道,进入新世纪后,老师病情已渐渐加重。他从来微笑面对困难,天性特别乐观坚强,从来总是把最光明最健康的一面显露给我们。他早年从复旦大学本科毕业后,在特殊的年代被分配去了江西农村教书,在特别艰苦的条件下,教书之余,仍挑灯夜读,文革后凭自己努力,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人到中年的他重回校园,刻苦攻读,据说老师为学习外语,每日凌晨起床用功,可他的身体也在长期劳累中透支了。他年轻时因操劳过度,得过慢性肾炎,后来竟发展成了肾衰竭,也就是尿毒症。而我们根本不知他的病情,只知他经常去医院,每年都会住院治疗一段时间。而天性悲观的我,见面每常要跟老师唠叨自己的痛苦烦恼,怨声载道,慈悲的老师每次都是认真倾听,帮我分析排解,好心的师母也常会劝慰我。自私如我,根本不知老师的大病痛。
研究生毕业后,我去了报社工作,跟老师的交流接触渐渐稀少了。老师时不时会来电话问候,我总是云山雾罩一番,因为我的老师比我还老实,从来不会怀疑我的话。他最关心的不外乎我的事业,这是他最看重的。虽然我懒惰晕乎,但老师一直坚信:瑞燕是有才华的,一定要发挥出来,这是他最着急的。他看着我每天在报社忙忙碌碌,虽然听到我打开局面,建立平台,接触了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创作的许多大家,增长了见识和知识,替我高兴的同时也替我担忧,担心我一直忙于琐务,荒废了自己的学业和事业。所以,无论我怎么飞来飞去,他总不忘了提醒我,要停下来,多读书,多思考,要多写好东西,这个才是根本。老师提醒我要多出成果。
而我除了几篇论文,读研以来,也没好好给老师看过我的作品。曹惠民老师早在我读大学时就读过我的多篇散文,他说不懂诗歌,可一直夸赞我的散文,他跟戴老师讲过好多次,大意是这是个好苗子,要好好栽培。后来,不知哪天我突然鼓起勇气,打印了一些诗歌散文给戴老师读,老师读罢激动万分,马上电话说你写得非常好!很有才华,千万不能浪费!过后师母给我说,老师高兴极了,读我的作品读了好多遍。从此,老师逢人便说学生有才华,虽然很多人并不相信,老师还是坚信不疑。
就在老师肯定我,希望我早日成材之时,我却遭遇了生命中最黑暗的岁月。整整7-8年时间,我几乎一直在黑暗的隧道里摸索,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塌陷下来,无力去承担。这个时候,是我亲爱的老师和最好的师母在我身边,给我最大的鼓励和安慰。当我受尽委屈和痛苦,就会跑去老师家里哭诉,我诉说求子的不易,大家庭的矛盾,事业的迷茫,父母的重病,一切的一切,我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的人,而在我最困难时,是我重病的老师和宽容的师母给了我最大的温暖和安慰。他们常把自己年轻时经历的种种艰难和辛酸告诉我,告诉我人生无不如此——人,必须坚强,才能挺过难关,绝不能垮下!若干年后,当我终于度过难过,云开雾散之时,师母悄悄告诉我,其实那时老师非常着急,着急我的事业迟迟没有起色,而师母对他说,瑞燕家事太多了,她能挺下来,不生病,没垮掉,就不错了,千万不要再去催她写文章。温厚善良善解人意的师母,曾对我说,“瑞燕,人家看你,羡慕你,觉得你幸福、光鲜。只有我最知你的苦。像你这样年龄的女孩子,没几个吃过你这样多苦,一个女人家该吃的能吃的苦,你都吃了。所以我常对你老师说,不要再去逼她,让她好好度过难关吧。”
而当我终于度过难关时,我的老师,身体已大不如前。频繁住院,他几乎每年都会大病一两场,有时甚至生命垂危。师母十几年如一日,无微不至关爱和照顾老师。当我父母双亲去世后,老师和师母看我并没一味沉浸在痛苦中不可自拔,而是勇敢走出伤痛,走出了狭隘天地,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老师非常高兴,他和师母说我现在的状态越来越好,几年前他们非常为我担忧,现在,终于可以放心了。老师告诉我不仅要打开局面,多创作,还要继续从事评论研究工作,这才是立足根本。当我有一天告诉老师,我要出一本诗集,完成创作诗歌20多年的心愿,我要在上海北京开两场朗诵会时,老师简直喜笑颜开。虽然那时,他已因为一场大病,心脏装了支架,九死一生,已行走不便,他坐在轮椅里还是喜笑颜开,只记得他连声说——好好好!并要求我尽快把诗集送给他。
可无知如我并不知道,其时老师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我只知道,他还是每周按时去透析。师母跟我说,血透的极限是10年,而老师在师母的精心照顾下,透析了整整13年,血管已脆弱不堪,心肺常因积液过多而诱发炎症,还因心衰被抢救过,身体的机能已渐渐衰竭,回天无力了,但老师和师母总对我隐瞒病情,我只知道,他经常住院,在我忙忙碌碌时,老师又住院了,这次一住几个月简直就不出来了,非同小可,病危通知都下了。住院中间我去看了一次,在医院,他时而清晰时而糊涂,但他还是认出了我。夏天,房间开着空调,老师盖着毯子,骨瘦如柴,我这样拉着他的手,跟他絮叨什么全忘了,只记得他看到我就是高兴,就是笑,尤其听我吹牛时,笑得更欢。想起来,那是我们师生此生最后一面了吧。我带去了无锡的水蜜桃,但他吃不下,也不舍得吃,嘱咐他弟弟带给他的小外孙吃。坐了不到半小时,我匆匆走了。而我的诗集一拖再拖,直到六月底才交稿给北京,然后又忙着去欧洲旅行,旅行回来后再修改,拖到8月底9月初,等样书出来时,老师已病入膏肓。当师母跟他说,瑞燕的书出来了,老师已不会说话,但他努力挥了挥手,表示高兴。
其时,我和师妹本来还想再去看望老师,但是师母说,他已完全不认得人,希望我们等老师好转能认人后再去。而我忙着筹备朗诵会,照顾孩子,也无暇他顾。忙碌之余,心里残存着一丝希望,希望老师能再次闯过难关,因为他一生坚强,多次死里逃生,我相信吉人天相。但噩耗终于还是传来了——2013年9月26日上午9点多,我亲爱的老师在仁济医院与世长辞,师母说他走时非常从容平静。
2013年10月,我将拖欠已久的我的诗集,放到了父母的墓地和老师的灵台前——久久跪拜,深深愧疚。在上海,我将一场迟到已久的朗诵会,献给了我远在天国的父母双亲和我最深爱的老师。
2014-2015 上海
 戴翊先生
戴翊先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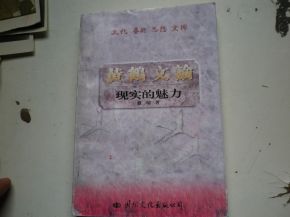 戴翊先生专著
戴翊先生专著

 纯贵坊酒业
纯贵坊酒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