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送我上学堂
作者:杨远新
沉浸于对往事的回忆,这几乎是老年人的专利。我自然避不开这个规律。尤其是每逢传统佳节,首先奔腾在脑海里的,全是父母养育自己的那些往事。在今年的整个春节期间,我无论白天举起酒杯,还是夜间燃放烟花,母亲慈祥的笑容都会浮现在我眼前。因为如果不是母亲对我的精心培育,我哪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在我漫漫人生征途上,能有些许收获,关键在于母亲为我开好了局,起好了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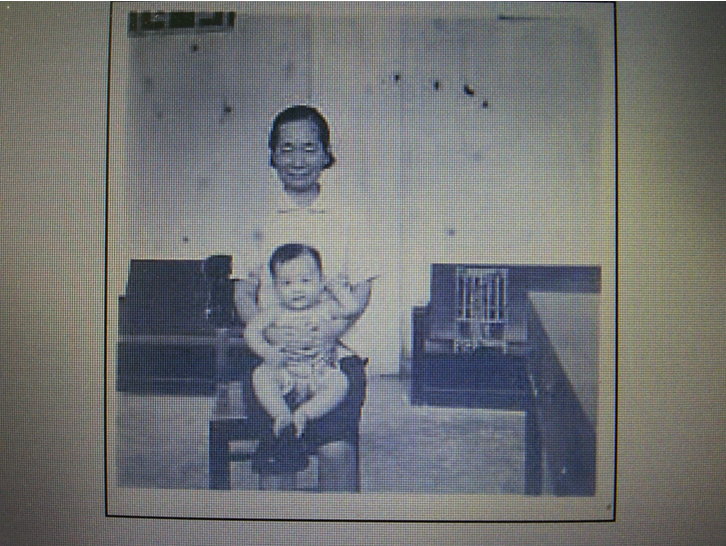 杨远新的母亲李清凤,怀中是她的孙子杨一萌,于1982年合影
杨远新的母亲李清凤,怀中是她的孙子杨一萌,于1982年合影
那年我刚满6岁,母亲给我算命,说我犯“水扑星”,为了隔开我与水的距离,母亲捧着我的脸说,你长大了,你晓得吗?不要每天围着我和你奶奶转来转去了,要到外面去看世界,去涨知识。当时我不完全懂她话里的内容。没点头,也没摇头,一脸茫然。
第二天,她把我交给长我三岁的姐姐美云,嘱咐她领我到熊家铺小学报名入学。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离开母亲的视线,远行不到一华里。自她送我和姐姐跨出开满芷花和兰花小院的那一瞬,她的心就附在了我身上。仅隔半天,她上学校,向班主任邓老师了解我玩心大不大,听课有没有举手提问。邓老师给了她满意的回答。可她还不放心,又藏在教室外面的一棵大柳树后,透过枝叶观察我在课堂上的表现。见我坐得端正,张起耳朵认真听老师讲课,她会心地一笑,放心地回队上的棉地里收摘棉花去了。
那天下午,放学时间到了,母亲见队上其他与我同班的孩子都放学回家了,却迟迟没有看见我。我家与熊家铺小学直线距离四五百米,中间隔着几坵平展展,绿油油的稻田,一条米把宽的土路,从小学西侧的熊家巷口向北伸出,穿越田野,连到我家门口,然后继续向北,经过蒋家园、高家巷口,抵何婆桥,朝东拐个弯,大约三百米,又拐向北,翻上李家湾的一片长满杂草和小树的高坡地,进入绿树摇摇,翠竹飒飒的李家湾,连接碧莲河大堤,通达坐落在沅水南岸的新兴嘴码头。
母亲站在家门口,向南看,不见我的影子,朝北眺,也不见我的影子。她怀疑我是不是跑到何婆桥水湾,或是碧莲河大堤上玩去了。既然南北都不见我的影子,她便迈开双脚,像一片飞起的云,来到熊家铺小学。
她刚走进学校前面那座宽大的操场,就被我的班主任邓老师看见了。邓老师跨出教室,迎上前问:“凤姐姐,看你这风急火急的样子,发生了什么事?”
母亲一眼扫遍长达两三百米的一溜教室,每间教室里都是空空的,心里越发着急,她向邓老师打听我的去向。邓老师告诉她早在一个小时前就已经放学了,目送我背着书包往家走。
母亲断定我去了何婆桥水湾捉鱼,于是跨出学校东侧门,抄近路往那里赶。没走出多远,她看见我姐姐美云独自背着书包往家里走。她几步赶上去,对我姐姐问道:“美云,是你带着兄儿(常德人对弟弟的称呼)去上学,大家都放学了,你怎么没领他一起回屋?”
我姐姐回答:“兄儿和蠢婆在学校后面晒书。”
母亲不明白地问:“为什么晒书?”
姐姐讲出了原因,并手指学校后面一条南北向的排灌支渠,说:“兄儿就在那里晒书。”
母亲一线风似的赶过去。她眼前的这条支渠连通环抱学校的一片水湾,而水湾被大树和翠竹掩映,西斜的太阳照射着水湾和南岸的树竹、北岸的稻田,母亲从这幅美景中听见了我的声音,发现了我的身影。
她轻手轻脚地走近我,一幕令她哭笑不得的情景映入她的眼帘。毛边纸制的语文课本,被水浸湿,像皱纹满布的脸,张开在太阳底下的绿草地上。我和同一天入学的邻居邓德爱,小名叫蠢婆,都睁大眼睛盯着水淋淋的课本,恨不得它一下被晒干。
原来,学校发给我的课本,被我染上了指头大一点墨汁,我嫌它脏,想尽了办法,都没有除掉。放学了,我与相隔一座竹园的邻居,同班同学邓德爱结伴回家。他年长我三岁,个子高大,小名叫“蠢婆”,无论在队上,还是在学校,他都是我依赖的保护神。路上,我向他讨教课本染上了墨渍,如何复原的办法。他出了几个主意,我说那些都试过了,没有作用。说话间,我俩经过学校后面那片碧绿如镜的水湾,我灵机一动,提出:“衣服搞脏了,用水洗就变得干净了。这课本染上墨渍,也可以用水洗呀!”
邓德爱说:“这是个好主意。”
我说:“东边角里背人眼,我们躲到那边去洗。”
邓德爱夸奖我:“你真聪明。”
于是我俩顺着水湾与稻田之间的小路,从西向东,选中了水边的一小片绿草地,坐下来,打开书包,掏出课本,小心翼翼地逐页拆开,拿出被染上墨汁的那一页,放进清凌凌的水里去洗。那时课本的用料全是毛边纸,入水就浸透了。我见此情形急得哇哇直哭。我问邓德爱:“蠢婆哥哥,这怎么得了呀?”
我一边问,一边用手从水里托起那页课本,放在绿草地上。
邓德爱说:“你莫急,这里当太阳,不要好久就晒干了。”
我俩都不敢再伸手碰那页课本,只用眼睛盯着它,希望借助温暖的阳光尽快把他晒干。
母亲观察了片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真是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她没有责怪我,而是替我收拾起水洗的课本,牵着我的手,走进邓老师的住房,向邓老师赔不是,自责地说:“都怪我没教育好。他这课本洗了,晒干也没用了。求您给他换新课本好啵?!”
邓老师解释说:“课本都是上面按实际学生人数发下来的。这要向聂家桥联校反映,看有没有办法。”
我一听这话,又急得扑进母亲怀里放声大哭。
邓老师人美心美,她捧着我的脸,安慰我说:“你的课本只洗坏了一页,其他可以重新装订起来。明天上课讲到这一页时,你可以搭看同桌同学的课本。”
母亲牵着我的手回家,一路上,母亲谆谆教导我,做每件事都要想一想,做得,还是做不得。我始终低着头,不敢看母亲一眼。因为我知道母亲那些日子里身体不好,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其实母亲不是病了,而是因为怀孕,反应太大。一路上,我觉得两边田里的稻谷都替我害羞得低下了头,青蛙看到我都逃得远远的,蜻蜓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就飞走了。
母亲替我背着书包,一手牵着我,一手提着我带中餐的饭笼子,那五百米的田间小路,我平时多数时候是打起飞脚跑过的,一眨眼就到了,今天却显得路程格外的长,格外的坑洼不平,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总算走进了自家的竹篱小院。
奶奶带着三岁的妹妹美珍打开院门迎接,她见我两眼通红,眼角挂有泪㾗,问是发生了什么事。
母亲简短地给奶奶介绍了情况。
奶奶一听就急了,担心地说:“书洗了,以后天天上课没有书了,那怎么得了嘞!”
母亲说:“只洗坏了一页,会影响到明天和后天的上课。”
奶奶说:“那还好。明天后天不上就是的,没有么得要紧的。”
母亲说:“那你讲得好。又不是吃饭,两天不吃不得饿死,两天的课要是落下了,以后就跟不上班了。”
奶奶一听又急了,说:“新书也没得领的了,还有么得别的办法想啵?”
母亲把我交给奶奶,说:“恩娘你领他们姊妹三个到食堂吃晚饭。他爹爹回来问起我,就说我到外面办点事很快就会回来。远新洗书的事,莫跟他爹爹讲起。”
说完母亲背起我的书包,走出了竹篱小院。我不知她要去做什么,只见她从原路返回,腆着肚子,一步一步地,比领着我回来的时候要走得快多了。我目送她穿过一坵又一坵稻田,朝熊家铺小学走去。她的身影很快被熊家巷口两边的参天大树遮掩。
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母亲回家了。她还没进竹篱小院的门就问:“恩娘!先德回来了没有?”
我奶奶正在灶门前洗碗,回答:“连他的人影子都还没有看到。”
母亲听了没有进屋,沿着我家的竹篱院子向西去了。我悄悄跟在后面,看见她走过我家院子的东篱,走进两边南竹相拥的一个巷口,往前去了。我经常和邓德爱在这个巷口里捉迷藏,南竹园是他家的,他家一栋四柱五骑、四缝三间的大瓦屋,被四周的南竹紧紧包围。他家往北过去三户人家,然后就是生产队的队部和食堂。
很快,母亲回来了,走近了,我看见她手中拿着一本我熟悉的小学一年级课本,我心想她难道是要给我补课,可她一字不识,怎么给我补课?
母亲走到我面前,我看见她累得满头大汗,心里感到很惭愧。母亲却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仍如平时那样摸了一把我的头,牵着我的手走进院子里。
她走进屋,奶奶对她说:“清凤,你的饭我从食堂领来了,搭热吃了吧!”
母亲回答:“还不饿,等一下。”
说着,她把堂屋里的一张方桌收拾干净,摆上借来的课本,接着打开我的书包,从里面拿出两张毛边纸,还有一支毛笔、一瓶墨汁,摆在桌子正中。
这时,太阳已经下山,晚霞透过树叶和竹枝的缝隙,照在院子里和禾场上,像是无数颗金星跳跃。平时我会追赶这些金灿灿的星星,用手捧,或用脚踩,可是今天没有这种心情。
我看着母亲把那些东西摆好,等待她对我的吩咐。
母亲给一支高脚灯盏里加满煤油,摆在毛边纸一旁,然后拿起玻璃灯罩,双手捧起,往灯罩里面哈了哈气,将一块旧布塞进灯罩里面,轻轻地擦拭。
就在这时,父亲回来了。母亲招呼他在方桌前坐下。父亲看了我一眼,似乎已经知道我洗书晒书的事情,因为那双乌黑的大眼睛没有平时那么亲切。我赶紧躲到母亲身后。父亲从不打骂孩子,但我要是做错了事,会被他叫到面前罚站。
奶奶把大门关上,带了姐姐美云和妹妹美珍,往卧房里去了,她边走边叮嘱:“十元你一双眼睛瞪得像两只擂缽,要是嚇到我孙儿了,我还你脱不得乎。”
父亲没有回答,接过母亲递给他的一把裁纸刀,抚平毛边纸,拿起课本,在毛边纸上比画,裁成一般高一般宽。
我从父母亲的对话中得知,母亲领我回家后,背着我的书包,直接去了聂家桥联校,找到联校长,替我检讨了洗书晒书的错误,请求给我再发一本新的课本。联校长的回答与邓老师讲的一样,课本是上面按学生人数,有计划发放的,联校也没有。但是答应向汉寿县新华书店提出申请,请求特事特办。母亲见新课本一时无望,就从聂家桥供销社中心门市部文具柜台,购买了毛边纸、毛笔、黑汁。
这时,父亲按照母亲的安排,将裁剪好的毛边纸蒙在邓德爱的课本上,一笔一划的小心翼翼地临擵,也许是过分紧张,额头汗珠直滚,母亲就用毛巾轻轻地替他擦掉汗水。
父亲终于把课本中的那一页临擵好了,母亲拿起反复比照,最终说了一句:“看样子蛮像。”
父亲说:“幸好这一个个字都有蛮大,字也不多,还能够比画。要是字多,字小,我就搞不好了。”
说着,父亲把他临擵好的那一页,放进我的课本。
母亲接过,用针线将课本重新缝好,放入我的书包。她叮嘱我:“明天你把德爱的课本还给他,要向他表示感谢。”
第二天到学校,我洗书晒书的事情经邓德爱一说,已经迅速传开了。
我同桌的同学拿起他的课本对我说:“你以后每天从家里带一把蚕豆给我,你就看我的课本一起上课。”
我往课桌上摆出父母亲替我修复好的课本,骄傲地看了他一眼,说:“你会想破后脑壳。”
从此,我对自己的课本十分珍爱,就像爱惜自己的眼睛那样,不在上面乱涂乱画,也不沾染一点墨渍,不卷边,不折角,保持菱角分明,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对书上老师讲解过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我都真正消化理解,装进了脑海里,每次作业都能打满分。每天回家后,母亲看到我拿出课本认认真真的复习,不声不响地完成家庭作业,脸上总是露出满意的微笑。
大约过了半个月,又是邓老师的语文课,她从讲台走到我身边,一手抚摸我的头,一手将一本崭新的课本放在了我的课桌上。迄今邓老师那两道满含怜爱的眼神,那双无限柔情的手掌,仍存储于我心底。我手捧新课本,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
也就在这时,邓老师从我课桌上拿起那本父母亲替我修复好的课本,举在手上,在全班同学面前对我父母给予了表扬,并希望每个同学的父母都向我的父母学习,真正关心自己孩子的学习和成长。她还籍此指出,整个学期即将过半,可有的家长却连影儿都没有看到。学校召开家长会不参加,老师上门家访也不露面,再忙也不能不管孩子的学习。要想孩子茁壮成长,做家长的必须付出心血。
 2006年8月杨远新(后排右)与母亲李清凤(前排右)、父亲杨先德(前排左)及姐姐杨美云(后排中)、大弟杨远明(后排左)于老渡口老家院内合影
2006年8月杨远新(后排右)与母亲李清凤(前排右)、父亲杨先德(前排左)及姐姐杨美云(后排中)、大弟杨远明(后排左)于老渡口老家院内合影
我听了邓老师的话,脸上热烘烘的,心里充满了自豪和骄傲。
我把父母修复的课本珍藏了下来,一直到2001年,父亲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把我完好保存的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的课本和作业本、还有高中毕业后直至参加工作之前的读书笔记、创作手稿,从屋梁上摘下来,全部当废品卖给了老渡口供销社。母亲事后知道了,把他狠狠地责怪了一顿。过后我知道了,感到十分可惜,十分遗憾。但我没有责怪父亲。我只问他:“你用蛇皮袋包好,为了防潮挂在屋梁上,替我保管了几十年,为什么要当废品卖掉?”父亲抚摸他那英俊的平头,嘿嘿一笑说:“我以为你已经写出那么多的书,那些旧书旧稿要起再也没有作用了。”
我内心原谅了父亲,他毕竟只读过三年私塾,还不完全具备文化人的情结。
那时候任何人都不会想到,就是这个洗书晒书的孩子,后来竟成长为写书的作家,到70岁时,已经发表了1800多万字的作品,出版了55本书,43岁破格评为副编审,46岁破格评为国家一级作家。
 本文作者杨远新近照
本文作者杨远新近照
【作者简介】:杨远新,湖南汉寿县人,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第五、六、七届理事,湖南省首届公安文学艺术协会秘书长、湖南省公安文联理事。迄今已发表出版文学作品1800余万字,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春柳湖(全四部)》(与杨一萌、陈双娥合著)《百变神探》《爱海恨涯》《东追西捕》《拟任厅长》《红颜贪官》《春涌洞庭》,中篇侦探小说《特区警官》《惊天牛案》;中篇纪实小说集《中国刑警大扫黑》《中国刑警在边关》,长篇儿童小说《欢笑的碧莲河》《小甲鱼的阿姨》《牛蛙大王》《险走洞庭湖》(与陈双娥合著)《雾过洞庭湖》《孤胆邱克》,中短篇儿童小说集《落空的晚宴》《今夜,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长篇报告文学《内地刑警与香港警方联合大行动》《创造奇迹的人们》《奇人帅孟奇》《县委书记的十五个日日夜夜》《走进福山福水》《天有巧云》等,201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8卷本880万字《杨远新文集》。作品曾获国家图书奖、公安部金盾文学奖首届一等奖、二届二等奖、三届三等奖、四届二等奖,文化部和全国妇联等七部委联合颁发的编辑奖、湖南首届文艺创作奖、湖南首届儿童文学奖等各类奖项58次。散文《我的祖母》被编入大学教材,分别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纯贵坊酒业
纯贵坊酒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