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起的银杏叶
作者:南小塘
世上最难说清的是情感。当情感和理智发生冲突时,应该用理智战胜情感。小说的故事纯属虚构。——题记

五十岁的陈教授在图书馆初遇林晚星时,她正踮脚够一本《里尔克诗选》。
此后三年,他珍藏着她落下的每一片银杏书签,直到那天她带着樱花香氛的气息说“我脱单了”,他手中的古籍骤然滑落。
他开始在校园每个角落“偶遇”他们牵手的身影。
咖啡馆玻璃倒映他鬓角新生白发时,他听见她用他教的德语对男友说:
“Ich liebe dich——这是陈教授教我的,最动人的句子。”

那年秋日,图书馆光线沉静,浮动着旧纸张特有的气味。陈树言教授穿过高耸的书架丛林,眼角瞥见一抹踮起的脚尖,正徒劳地够着顶层一本硬壳精装的《里尔克诗选》。书脊上烫金字母微微闪光,映衬那年轻的手指。他走过去,轻易取下那本沉重的书,递过去。女孩惊得微微后仰,眼睛在瞬间慌乱后亮起来,像被拨开的晨雾:“谢谢您!”声音清亮,带着点雨后青草的气息。她接过书,书页里夹着一片扇形金黄的银杏叶飘落在地。他弯腰拾起,指尖拂过那叶脉清晰的纹路,递还时,触到她微凉的指尖。她笑了,脸颊上浮起浅浅的涡,像投入湖心的石子漾开的涟漪:“送您啦,教授!”那叶子,后来被他夹进了自己案头常翻的《柏拉图全集》扉页。
从此,那片银杏叶仿佛开启了一个隐秘的仪式。每年秋天,林晚星总会不经意地“遗落”一枚精心挑选的银杏书签在他常驻的阅览桌角、他办公室门缝下,甚至夹在他批改后发还的论文里。金黄的叶子,脉络清晰如命运手笔,被他一一收拢,用一方素净蓝绸帕子包好,放进书桌最深的那个抽屉。它们像无声的密码,记录着三年时光里若有若无的靠近。他习惯她带着问题的叩门声,习惯她谈论艰深理论时发亮的眼神,习惯她偶尔带来的、带着微甜气息的点心。他看着她拔节生长,像一株向着阳光舒展的植物,自己心底某个沉寂已久的角落,也似乎被这光悄然照亮,生出些他自己也不愿深究的暖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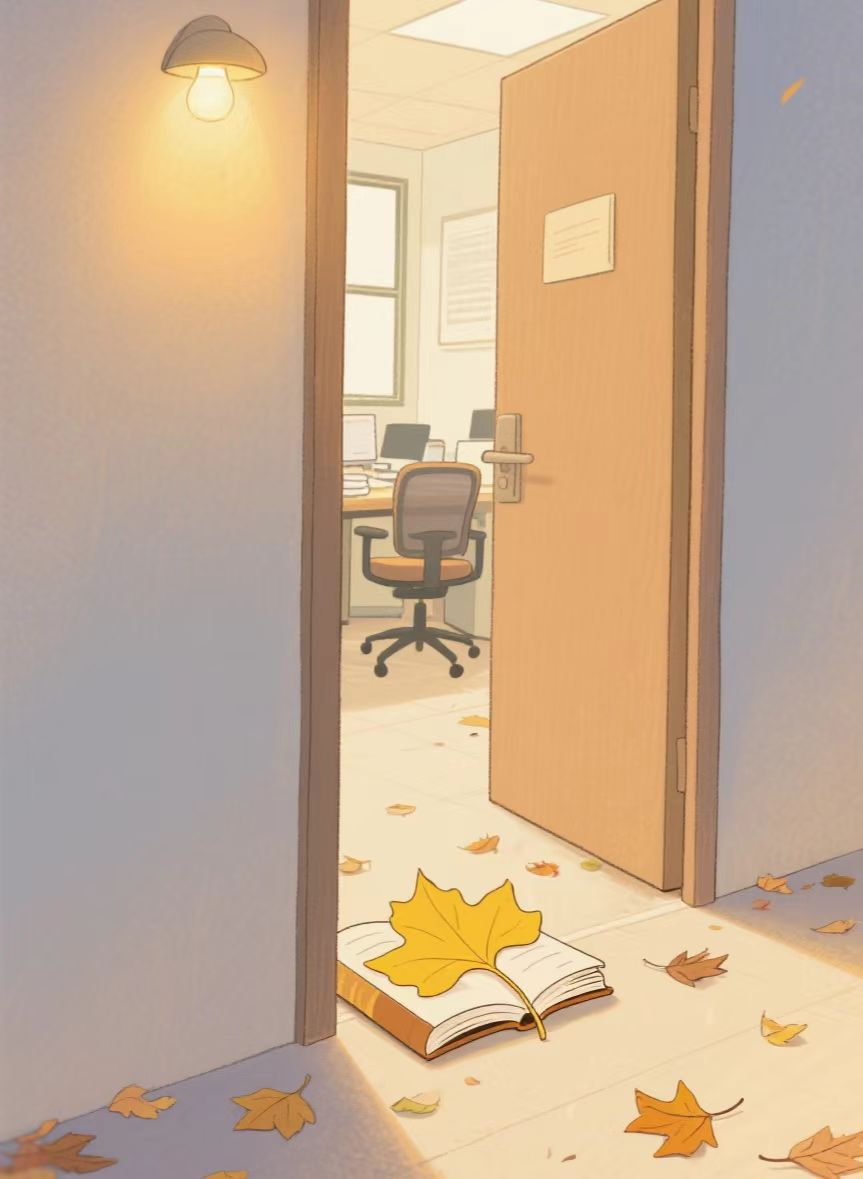
那天下午,办公室里弥漫着初春慵懒的暖意。窗外那棵银杏树刚抽出一点怯生生的嫩芽。林晚星推门进来时,带来一阵风,裹着一种陌生的、清甜的樱花香氛气息,与办公室里沉郁的书卷气格格不入。她脸上焕发着一种从未见过的光彩,眉梢眼角都跳跃着生动的喜悦。
“陈老师!”她声音比平时更脆亮,带着一种急于分享的雀跃,“跟您说个事儿!”
教授放下手中的笔,抬起头,脸上是他惯有的温和笑容,像一张熨帖的面具:“哦?什么好事,让你这么开心?”他看到她眼睛里闪烁的光,心没来由地微微一跳。
“我脱单啦!”她几乎是宣布般地,轻轻拍了拍手,脸颊飞上两朵红云。
“哐当”一声闷响。陈树言手边那本厚重的《西方哲学大全》猝然滑落,砸在光洁的橡木地板上,扬起细微的尘埃。那声音在突然变得死寂的空气里显得格外刺耳。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如同凝固的石膏面具,随即被一种极快的、近乎狼狈的苍白覆盖。血液似乎在这一刹那从四肢百骸倒流回心脏,又在下一秒猛烈地撞击着胸腔,带来一阵眩晕的钝痛。
“啊……好,好……”他喉咙发紧,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着木板,每一个字都带着粗粝的痛感。他弯下腰去捡书,动作僵硬得如同生锈的机械。指尖触到凉硬的书壳,那冷意瞬间刺透了皮肤,直抵心脏。他不敢抬头看她此刻的表情,那带着樱花香气的喜悦像无形的针,密密地扎在心上。他笨拙地把书放回桌上,书脊撞倒了旁边的红木笔架,几支上好的狼毫笔滚落下来,墨点溅上他素来一尘不染的衬衫袖口,像几滴绝望的泪痕。他盯着那墨点,视野有些模糊。
“老师?”林晚星的声音带着一丝困惑和关切,似乎想上前帮忙。
“没事!没事!”他猛地直起身,动作幅度大得有些突兀,几乎是粗鲁地挥了挥手,想挥开空气中那令人窒息的甜香和随之而来的巨大空洞,“恭喜你,晚星……这是好事。” “真的……恭喜。”声音空洞,在寂静的办公室里嗡嗡回响,像石子投入枯井。他清晰地听见自己胸腔里某种东西碎裂坍塌的声音。

那场短暂对话之后,陈树言如同被投入了一个玻璃罩子。校园里的一切——熟悉的林荫道、喧闹的食堂、安静的图书馆——都蒙上了一层灰翳,失去了原有的色彩和声音。他依然准时出现在课堂,声音平稳,条理清晰。然而只有他自己知道,那精心构筑的理性堤坝之下,汹涌着一股股情感暗流。每一个独处的间隙,那带着樱花香气的宣告便会在耳边炸响。他开始失眠,深夜对着昏黄的台灯,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蓝绸帕子里那些早已失去水分、变得薄脆的银杏叶。那些叶脉的纹路,带来一阵阵细密而持久的刺痛。
他变得像一个幽灵,不自觉地开始在校园里游荡。他“恰巧”出现在他们常去的第三食堂门口,看见林晚星和一个高大阳光的年轻男孩并肩走出来,男孩手里拿着两杯奶茶,很自然地插好吸管,先递给了她。她笑着接过,吸了一口,然后踮起脚尖,飞快地在男孩脸颊上啄了一下。那笑容明媚得刺眼。陈树言像被烫到一般,猛地转过身,心脏剧烈地抽搐,仿佛要挣脱胸腔的束缚。
他“路过”他们傍晚散步必经的未名湖畔。夕阳的金辉洒在湖面上,碎成万点金光。他们牵着手,步伐轻快,女孩仰着头对男孩说着什么,男孩侧耳倾听,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林晚星的长发在晚风中轻轻飘动,那画面美好得像一幅青春电影的剧照。陈树言站在一棵老银杏树的阴影里,树皮的粗糙质感抵着他的掌心。他死死盯着那两只紧紧相扣的手,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一种深切的无力感和被彻底排除在外的冰冷,从脚底蔓延上来,将他冻结在原地。

一次次的“偶遇”,如同一次次缓慢的凌迟。每一次瞥见他们年轻的身影,每一次捕捉到她脸上那全然的、与他无关的幸福笑容,都像一把钝刀,在他心上反复切割。他试图用理智的绳索捆住这头名为嫉妒和痛苦的野兽——她是学生,是清晨的露珠,是注定要飞向广阔天空的鸟;他,已是日暮途远的倦客,是岸边沉默的礁石。年龄、身份、伦常……每一道都是深不见底的鸿沟,横亘在他与她之间。这道理像冰冷的铁律,刻在骨髓里。然而,心底那份难以言说的眷恋和骤然被掏空般的失落,却如同顽固的藤蔓,越是挣扎,缠绕得越紧,勒得他喘不过气。
他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在迅速地衰败下去。对镜剃须时,目光扫过鬓角,赫然发现那里新添的几缕白发,在黑色的底色上显得格外刺目,像冬夜提前降临的霜雪。眼角的纹路也似乎在一夜之间加深了,疲惫如同墨汁,沉淀在眼睑之下。一种深刻的、无法挽回的苍老感,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攫住了他。那是一种比时间的流逝更残酷的剥夺,是被蓬勃的生命力无情映照下的黯然失色。
周五下午,他鬼使神差地走进了那家位于校园后街、他们曾多次讨论过论文的“鸢尾”咖啡馆。熟悉的咖啡豆烘焙的焦香和轻柔的爵士乐包裹着他。他习惯性地走向角落那个靠窗的位置——那是林晚星最喜欢的座位,可以安静地观察街景而不被打扰。脚步却在离座位几步之遥的地方顿住了。
那个位置上,坐着林晚星和她的男友。他们头挨得很近,低声私语着。阳光透过洁净的落地玻璃窗斜射进来,恰好笼罩着他们年轻的身影,仿佛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边。男孩戴着和他相似的黑框眼镜,镜片后的眼睛带着笑意。林晚星端起面前的拿铁,小口啜饮着,脸上洋溢着一种近乎透明的幸福光彩。

陈树言僵在原地,进退维谷。咖啡馆明亮的灯光此刻显得如此刺目,将他无所遁形地暴露在一种巨大的尴尬和狼狈之中。他下意识地侧身,想把自己藏进旁边一盆茂盛绿植的阴影里。目光却不由自主地投向那扇巨大的落地窗。光洁如镜的玻璃上,清晰地映出他自己的身影:一个穿着熨帖却难掩暮气的灰色衬衫的男人,鬓角的白发在灯光下无所遁形,面容疲惫而灰败,眼神里盛满了无处安放的落寞和一种深刻的、与这明亮场所格格不入的寂寥。窗玻璃像一面残酷的镜子,将里外两个世界分隔得如此清晰——里面是阳光下的青春与爱恋,外面是阴影里的迟暮与孤单。
就在这时,林晚星清脆的笑声低低响起。她放下咖啡杯,转向身边的男友,眼神亮晶晶的,带着点小小的得意。她微微扬起脸,清晰地、一字一顿地用德语说道:
“Ich liebe dich——”
那声音不大,却像一道惊雷,瞬间劈开了咖啡馆里慵懒的空气,也狠狠劈中了窗边阴影里的陈树言。他全身的血液似乎在这一刻凝固了。
“——这是陈教授教我的,”林晚星的声音带着轻快的笑意,清晰地传入他的耳中,每一个字都像冰冷的针,“他说过,这是德语里……最动人的句子。”
Ich liebe dich。
我爱你。
时间在那一刻仿佛被冻结了。咖啡馆里低回的爵士乐、咖啡机的蒸汽嘶鸣、邻座的低语……所有声音都潮水般退去,只剩下那句“Ich liebe dich”在陈树言死寂的脑海里反复轰鸣、炸裂。这句他曾凝视着她的眼睛,在讲解德语诗歌情感表达时,特意强调过的句子。那时窗外也是阳光正好,一片金黄的银杏叶安静地躺在他摊开的书页上。他记得自己当时的声音带着一种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温柔,说它承载着语言难以企及的重量与纯粹。他万万没有想到,它最终会从她口中说出,带着那样甜蜜的语调,指向的却是另一个人。
玻璃窗上,映着他自己骤然失血的脸,灰败得如同墓园的雕像。他清晰地看到自己嘴角难以控制地微微抽搐了一下,那是一个比哭更难看的表情。
侍者端着托盘走了过来,礼貌地询问:“先生,您需要点什么?”
陈树言猛地回过神,像从一场冰冷的噩梦中惊醒。他几乎是仓皇地、胡乱地指了一下菜单上的第一个名字:“这个……就这个。”
很快,一杯深黑色的浓缩咖啡放在了他勉强找到的、离那个角落最远的座位上。小小的白瓷杯,盛着几乎凝滞的液体,像一小滩绝望的泥沼。他机械地端起杯子,滚烫的杯壁灼烧着指尖也浑然不觉。他猛地灌了一大口。
浓烈的、尖锐的苦味,如同烧红的铁钎,瞬间贯穿了他的舌苔,凶猛地燎过整个口腔,直冲喉咙深处。这苦来得如此暴烈,如此蛮横,几乎让他窒息。他下意识地想要咳嗽,却死死忍住了,只是紧紧抿住了嘴唇,喉结剧烈地上下滚动。这苦,瞬间击溃了所有试图维持体面的努力,将他内心那无法言说的、庞大的失落和痛楚,以一种最直接、最粗粝的方式具象化了。原来这就是答案,这就是他所有挣扎、所有隐忍的最终滋味——浓缩的、纯粹的、无处可逃的苦。
他放下杯子,手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目光再次投向那个阳光满溢的角落。林晚星和她的男友不知何时已经离开了,只留下两个空空的咖啡杯和桌上一点细微的水渍。阳光依旧慷慨地铺洒在那张空椅子上,明亮得晃眼。

陈树言的目光缓缓移向窗外。街道上行人如织,车流不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初春午后。他枯坐了很久,直到那杯浓缩咖啡彻底冷透,杯沿凝了一圈深褐色的渍。身体里的喧嚣似乎也随着那冰冷的苦意沉淀了下去,只剩下一种无边无际的、疲惫的虚空。
他慢慢站起身,动作迟缓得像一个真正的老人。走到吧台结账时,他的手伸进随身的旧公文包。指尖触到的不只是钱包,还有一个硬挺的、熟悉的书角。他顿了一下,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缓缓地、将那本书抽了出来。
是那本硬壳精装的《里尔克诗选》。书页间,依然夹着三年前她“遗落”的第一片银杏叶,金黄的色泽早已褪成一种黯淡的浅褐,薄脆得仿佛一碰即碎。在书的内封页上,一行遒劲的钢笔字墨迹已有些年份:“给晚星——愿诗与思的光,照亮你的旅程。陈树言”。这是她入学那年,他精心挑选的礼物,却因种种顾虑,始终未曾送出。
他翻开扉页,那片干枯的银杏叶静静地躺在那里。他凝视片刻,然后用手指,极其缓慢地、珍重地,将那片叶子从书页间取了出来。细碎的叶脉发出几不可闻的碎裂声。他小心翼翼地将这片承载了三年无声时光的枯叶,放进了自己衬衫胸前的口袋里,紧贴着心脏的位置。那里似乎还残留着一点微不足道的暖意。
然后,他将那本崭新的、扉页题了字的《里尔克诗选》,轻轻放在了刚才林晚星坐过的位置——那张被阳光晒得暖融融的空椅子上。
他最后看了一眼那本沐浴在阳光里的书,转身推开了咖啡馆沉重的玻璃门。门上的铜铃发出一声清脆的“叮当”,像是在告别。

初春的风还带着料峭的寒意,扑面而来,卷起了他灰色风衣的下摆。他挺直了微驼的背脊,沿着人行道,一步一步,融入了外面喧闹而充满生机的街道。阳光将他孤独的影子在身后拉得很长,很长,一直延伸到街道的拐角,终于被川流不息的人群彻底吞没。

说明:第一张照片系本人拍照,其余是智能生成。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纯贵坊酒业
纯贵坊酒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