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无之城”与“失败之书”
——《北京主义》中的北京书写
王士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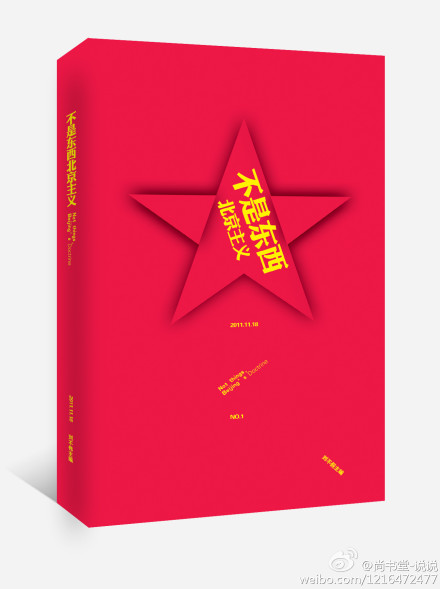
“一个我出现在北京,另一个我出现在虚无之城”“一座坏了的城,我们却还无可救药地爱着它”,这两句话都选自近年出版的《北京主义》作品集,前者出自盛华厚的长篇随笔《北京:考研日记》,后者出自搅水女孩的诗歌《坏城》。《北京主义》是由诗人刘不伟主编的一份文学刊物,其作者大多是生活、居住在北京而户籍在外地的所谓“北漂”,其所发表作品有诗歌、小说、随笔、访谈,也包括一些非虚构实录等跨文体文本。如其命名所示,“北京主义”具有明显的“北京”元素,其中所包含的北京叙述颇具特色,值得分析。确如搅水女孩所说“一座坏了的城,我们却还无可救药地爱着它”,北京是一个既让人爱又让人恨的城市,它光鲜亮丽、异彩纷呈,而又包含着重重的问题、对个体形成严重的压抑,让人割舍不得、剪不断理还乱。如范儿的《宋庄时代》中所表现的,这是一个看似精神亢奋实则精神分裂的时代,如诗中所写“很多人挨饿很多人酗酒很多人夜里失眠发疯很多人羞耻地呼吸着过了今天就不再想明天。/很多人在精神的伤口边缘种植葡萄和罂粟双重的饥渴难以令人忍受。/很多人蜗居在狭小的天地依然幻想着自由和战斗在每一个瞬间都迸发自戕的灵感举起手中的笔就像举起一支左轮手枪。”“很多人一夜暴富之后死去很多人一夜破产之后被送进精神病院朝所有的人吐唾沫并哭声叫嚣:我是一个艺术家!”这首诗明显受到美国“垮掉一代”的影响,但不能不说,它所表达的的确是今日之中国、今日之北京的一个方面,是及物而真实的。北京汇聚了诸多截然相反的要素:它既是峰巅,又是深渊;既熟透了,又很幼稚;既是过剩之所,又是匮乏之地;既汇善之大端,又聚恶之大成;它是权力、体制之城,又是崇尚个性、包容万有之城;它是前现代、封建之城,又是现代化、现代性之城,更是混搭、并置的后现代之城。北京的城市之大、人口之多、节奏之快、竞争之激烈、精神之冷漠,一切都是超乎寻常的,在这里,权力、金钱、资本、等级的逻辑已经无孔不入,而个体愈益渺小,个人的价值与尊严摇摇欲坠、岌岌可危。个人不接受、不被纳入现实的逻辑体系则无法生存,个人接受这一体系则意味着失去自主性,而被裹挟、被异化。绝大多数的人,则是在认同与抗拒之间摇摆、奔波、居无定所。
《北京主义》的写作大都具有一定的先锋性、独立性、前卫性,称他们为一群先锋写作者应并不为过,然而,从社会身份来讲,他们又属于“屌丝”“北漂”“底层”。他们大都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社会保障,收入不高,常为生活所困,属于无权、无钱,也看不到太多改变现状希望的“弱势群体”。精神上的富足、自由、高贵与现实中的贫困、卑微、压抑便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们从尘埃里来、从污泥浊水中来,他们所写的主要内容,是找工作、加班、失业、租房、生病、考研、失恋、性苦闷、手淫,而他们的内心,则在空虚、无聊、绝望、压抑、孤独、麻木之间辗转流徙,所有这些无疑与国家叙事、主流叙事中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有着霄壤之别。城市作为一个坚硬的庞然大物,对于血肉之躯的个体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和威胁,黄旭峰发现:“现在或许什么东西都是软塌塌的/——除了硬邦邦的钱”(《饕餮》),而不识北则说:“而我又没有钱/而我又一个人在北京/漂泊/而我还渴望爱情/假如我生病了/囊中羞涩/谁来给我支付医药费/只要房东把门锁了/我就无家可归/实际上我本身就没有家/关于未来/我没有未来”(《你们思考人类我思考我自己》)。现实冰硬而冷酷,生存的逻辑强势覆盖,使人成为了单向度、平面化的人,浅予的诗《北京,我要做大胸》写道:“拿着简历四处奔波/北京的风/吹得脸生生地疼/我总是在晚上走过天桥时加快脚步/多看一眼这些繁华灯火/心情就更低落一分”,继而,她写了对于都市和都市人的一种发现:“孤独的人到处都有/漠然的脸也充斥周围/繁华都市的风景/并不是楼宇轩昂/花灯锦绣/车水马龙/而是这些统一的孤独/统一的脸”。这种“统一的孤独”“统一的脸”几乎是令人毛骨悚然、怵目惊心的,然而,它又是如此形象而传神,揭示了现代都市生活的某种本质。顾夏的小说《沦于流年》中则如此写孤独:“渊抱我的时候,我会难过的想流泪。不是因为他太用力,而是终于有一个人肯温暖我冰凉的身体。”到处都是人,却没有一个体己的、可亲近之人,这种情感状况在现代都市中同样是具有普遍性的。
面对无处不在的异己性力量、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他们(写作者与主人公很大程度上是同一的)已然不再激愤地反抗而更多的是将矛头对准了自己,自我解嘲、自娱自乐、自我消解、得过且过。不识北的诗《我很悲伤》,从标题看似乎是要写一个严重的问题,其内容却是:“我的微博/掉了一个粉/尽管后来又回来一个/但不是掉的那个”,颇具黑色幽默效果,让人一笑之后却不禁悲从中来。消除的诗《献给一只贫穷的胃》讨论“买房”的问题:“这期间,我的女人还隔着门对我说/我们是不是要买个房子,我说/好啊。她说:你觉得买在哪儿好/我说,当然买在城里的别墅最好,有保安/有有修养的邻居、有小三和红色跑车/去上班还不用挤公交车。她说,/去你妈的”,这里面有戏谑、有自我解嘲,内在也包含控诉与悲怆,耐人寻味。安琪则以“悲欣交集”的心情来写当上了房奴的心情:“从一粒沙开始攒∕从一块砖开始存∕40年来第一次有了当房奴的机会应当珍惜∕相爱的人要齐心供奉政府的巨胃∕在自己的祖国节俭一生”(《悲欣交集》)。消除的另一首诗《那栋楼一共有多少层》中,“我”为摩天大楼总共有多少层而困惑不已,一直数到目光眩晕、眼睛充血。这首诗中,无聊之事、无聊之人,以及写作者对其的呈现,构成了多重的解读层次,在扁平化、无意义的表象之中,其实又包含了价值指向和深层意蕴。在消费主义的现代都城,人被物包围、笼罩,“主体”的地位较之此前大为降低了,写作者也往往有意地后撤、降低,呈现一种纯客观化的景观。比如王那厮的诗《北京,天通苑西一区信息》将沿途所见小区的各种标识记录下来,除此再无其他,而小虚则将房间里的100多种东西——包括书名——排列在一起,其题目叫做《朝阳,我的房间。或者:当123种物质排列组合在一起,一种新物质产生了》,这里,客观化、去情感化虽然比较明显,但慢慢读来,其背后仍然是隐约有所指的,不同的人可以从中读出不同的内容,经过如此不无冗长、乏味的排列组合之后,“一种新物质产生了”。
“北京主义”的书写相当程度上堪称“失败之书”,一方面,这与他们的现实处境、生活状况有关,另一方面,则与他们的价值立场和对人生的认知理解有关。对他们而言,生活是由一个接一个的失败构成的,他们被剥夺,无权无势、经济窘迫、颠沛流离、不知所终,这构成了“失败之书”书写的内容,也强化了“失败之书”书写的力度和动力。这种“失败”,既有面对权力、面对体制的失败,也有面对现实生活、面对人生遭际的失败,更有面对命运、面对生命本体的失败,这种“失败”书写有的时候侧重于某一方面,更多时候则是互相交织、混糅的。不识北的《出门忘带钥匙记》面对某种体制的“庞然大物”:“我在将心比心想到723老村长暴力下的苦难我随时可能就是其中一者他们警棍制服把暴力伸向全国/我是温顺的小百姓出门怕被车轧死怕莫名其妙被打无缘无故消失/到处都是谎言到处都是麻木到处都是冰冷到处都是欲望膨胀善良愚蠢的微生物”,它揭开了生活温情脉脉的表面,而呈现出了某种真相,这真相,令人惊悚、不适,不忍面对。李飞骏的《父爱并不能让你强大》则更多面对生活中具体、现实的问题:“你必须小心翼翼地捧着泥饭碗/所谓狗屁理想必须向工作让路/人格不得不向上司低头/盼着节假日加班/为挣了一罐进口奶粉而欣喜/你学会了与菜贩讨价还价/写日记的习惯改为记流水账/你必须省下买书的钱买尿不湿/学会省下电影票买一卷卫生纸/你无法帮女儿选择户籍,正如/无法选择没有地沟油的祖国/你无法帮女儿逃离幼儿园到大学的/产品流水线/无法避免女儿重蹈你的覆辙/你知道自己的一生就是/女儿的一生。”失败已然无可避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甚至代代相传,这无疑是让人绝望、窒息的失败书写。李九如在《2010—2011年度自我总结》中写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北京哟/难道你真的如此冷酷/我想对你说/我很伤心/我很恐惧/我很不幸地沦为/某个窗子后面/猥琐的等待者/即使现在的这首诗/也救不了我。” “失败”,是逐渐炼成的,而拯救,却似乎杳然无着、渺茫无期。
——这是一座“虚无之城”,如鲁迅所言“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然而,知晓了这虚无,乃可抵抗一阵,乃可“反抗绝望”,而不致完全误入歧途,或者草草缴械投降。这是一种“失败之书”,然而,失败无处不在、无可避免!写出这种失败,本身即是一种成功,它是对自我、对内心、对更多人的慰藉与关怀,它如依稀之光,伴随人们的追求、探索与奋斗,这是“人”的成功,也是文学存在的理由。
作者简介:
王士强,1979年生,山东临沂人,文学博士。2009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同年至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现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与评论,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诗探索》特约编辑。


 纯贵坊酒业
纯贵坊酒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