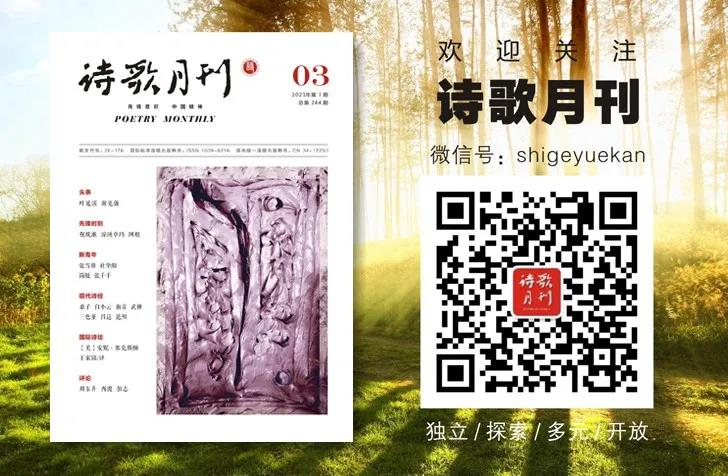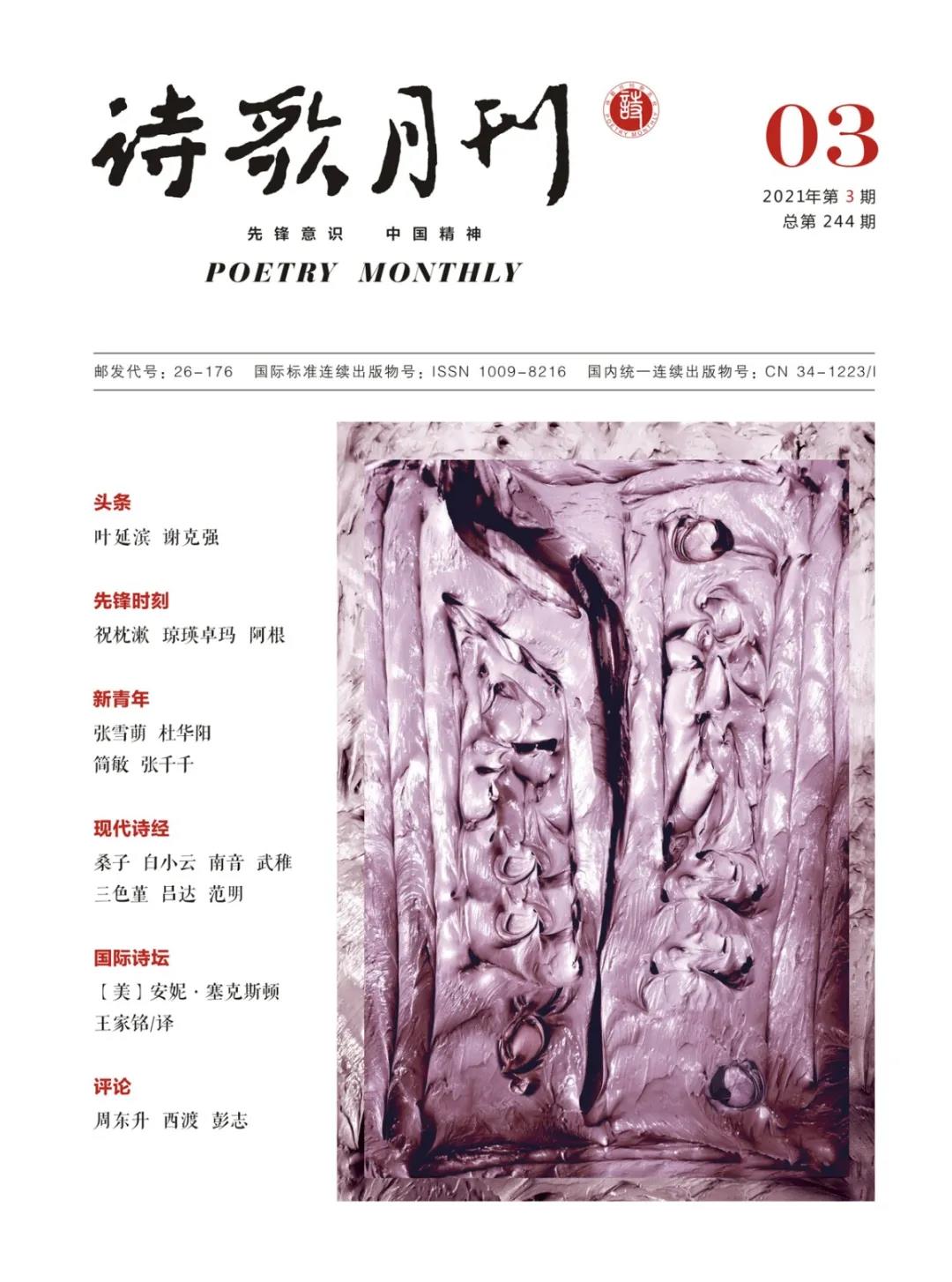
《诗歌月刊》2021年3期目录
头条
庚子十六帖(组诗)/叶延滨
庚子诗札记(随笔)/叶延滨
风从故乡来(组诗)/谢克强
学诗札记(随笔)/谢克强
先锋时刻
祝枕漱/琼瑛卓玛/阿根
新青年
张雪萌/杜华阳/简敏/张千千
现代诗经
“她们”诗歌专辑
桑子/白小云/南音/武稚/三色堇/吕达/范明
国际诗坛
安妮·塞克斯顿的诗
【美国】安妮·塞克斯顿 王家铭/译
评论
多多的孤愤/周东升
一人来到黑暗的现场……/西渡
汲古、借镜与写心/彭志
诗版图
天津黑色海诗社诗人作品
大可/红杏/荣儿/阿蒙/贾启香/左文义/孙学东/李永萍
方春燕/黄梅/安连国/侯宏江/王爱民/胡庆军
诗人在线
杨海蒂/姚辉/包苞/李永才/王学芯/谭滢/马累/高凯
游离/吉尔/计虹/千野/韦法明/李永立/梅尔/马道子
余述平/徐小华/张建明/宋心海/姚瑶/潘莉/邓木桂
王彬/月色江河/李静/周雁翔/何正国/周伟/钟雪
张晓云/刘联合/汪柯/朱成玉/羊儿/王胜江
栏目主持人语
头条
本期为读者重磅推出一直活跃在我国诗坛的两位实力派诗人——叶延滨先生和谢克强先生的近作,他俩是中国诗坛的宿将,也是常青树。他们已步入七旬,到了这浮云参透、返璞归真,唯留诗心之时,他们的诗歌和诗思又是怎样的境界?这是我想深思和揣测的。尤其是,面对过去的多灾多事之年景,他们的精神世界又是怎样风云万千?来,让我们读他们的诗和诗思吧。
叶延滨先生的《庚子16帖》,我读完后,其诗中词语相互碰撞着火花,让我惊诧。一是“悲壮”和“豪放”。不错,庚子年的新冠病毒夺去我们众多生命,诗人在作品中呼吁人们尊重自然的同时,更用悲悯之心吟出“珍爱生命”的心声。他咏出这样一句泣血之语:“隔着无边奈何天,/死活都是你的人”,以及豪壮地向受难者呐喊出:“一口气撑着就活,活下去”,同时,他以语言的昂扬姿态,向衰老和死亡发出“原来每个放声大笑的人,/都是命运之河的大瀑布”这样的通透之声,这是他“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大写意的旷达人生观,也是他个体生命的宣言,又是对厄运和死神的檄文和重击,更是对弱者和无助者精神振奋的擂鼓之声。二是“穿越”与“重塑”。他在诗里多次做现实与梦境、此地到彼地、天上与地下、古往到今日的精神穿越。在穿越中,他对现代科技智能化生活提出个体性的沉思和质疑,他保持着喜爱后的警惕,他让自己穿越到“桃花潭”,但清醒认识到自己“不是陶令”,当面对手机、人脸识别等高科技时,他又开始反省和追问生存的目的和意义,正如他在《庚子札记》中写的“反思和自省是灵魂的沐浴”,他诘问:“只是活着有劲吗?”同时,他在诗中重塑自己的时空观、世界观、人生观乃至自己的诗学观。他是一个负责的诗人,他的诗观强调,“最后能留下的(诗),必然是与时代社会有关联记录和反映了那个时代特征的。”是的,他的《庚子16帖》是他的思考、记录,也会留下的。
谢克强先生的《风从故乡来》,表面写的是对故乡、亲情、农家、农事的返乡追思,仿佛是一组向远逝的农业文明唱的挽歌。其实,向深里读,你会发现他老成见到,有自己对当下农村和人们的生活另一层面的哲学意义上的考量。是的,他写民谚、民歌、族谱,桑和野菜等“老旧”具象,但他在其中浸入了他的真情实感和独特发现,新的诗性表达。他的诗中对村庄不见炊烟发出这样哀婉又机智的追问:“那炊烟,/母亲带走了吗?”他用游子归乡的心境,观察熟悉而又陌生的一切,他用“参军前栽下的几十棵树”“掏雀蛋”“压岁钱”等诸多细节来再现和还原过去的一切,他还写出这样朴实而又豁达的诗句:“老就老呗,谁不老呢?”“想飞就飞,想唱就唱。”这超然脱俗的蔑视衰老和死亡的诗句,是积极的,有力量的暮年心态。他要求自己的诗:“就是在日常平凡的事物中,发掘出自己独到且蕴藏着巨大的精神内涵,即他所象征或隐藏着的丰富的社会内容。”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这个诗观点和我前文所引的叶延滨的诗观点是一致的,不知道是否他们都处在铅华洗尽、珠玑不御的境界里。
对于他俩的诗,我想要改写“剑老无芒,人老无刚”这句成语,应为“剑老存芒,人老则刚。”打住。
——李云
投稿邮箱:shigeyuekan@163.com
先锋时刻
祝枕漱的诗歌初读起来,让人感到一种古典的诗歌意味。这种诗歌,在当今可以说简直泛滥了,它不过是对古典诗歌的“炒剩饭”。但是,当我仔细再读,我发现,他的诗歌远非如此。他诗歌中的“古典”并非是其全部,其中更有着一种现代人孤寒的生存体验。在存在的意义上,他诗歌中的古典,与当下的生存现实构成了互文性的关系。他的诗歌里的形象,是一个现代书生的形象,瘦削而感伤。他笔下那种郁结凝滞处,往往让现代感强烈地呈现出来,像刻刀刻出来的。“在这末世,养鹤也无法登高。”(《卫懿公养鹤》)之类的句子镶嵌诗中,便是这种郁结凝滞。
无疑,琼瑛卓玛已经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诗人。她是属于那种学徒期非常短,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迅速成长的类型。这背后是她的勤奋和天赋,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两年以前我见到她的诗歌,还远不是这样,但她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声音,她的诗歌的声音非常独特,是在当今诗坛具有标识性的那种。“这可真不赖,可我得走了”(《礼物》)这种声音,极其自然轻柔,雪落无声。她已经发展出一种轻逸、灵动,且具有细节清晰的视觉化的诗歌,而这种视觉化,却同时还拥有自己的声音,这太难能可贵了!她的诗歌对感受的捕捉相当精确,以至于她笔下的那些事物,有一种直抵空无的品质。所谓“事如春梦了无痕”,形容她的诗是贴切的。我想,用严羽的话来描述她的诗,也同样贴切:“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阿根的诗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就是他的诗歌与阅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诗歌能否以阅读展开写作?这当然没有任何问题。但关键在于,它在当代的先锋诗歌写作中成为一个敏感的议题。其原因就是在诗歌的写作,是原创的还是互文的。这已经成为一个诗歌史问题,当然也是一个诗学问题。从阿根的诗歌来看,他的诗很显然也在试图做出回答:为什么不可以既是互文的,又是原创的?我们从他的这组诗歌可以见出,他的阅读和他个人的经验已经深深融为一体,分不清彼此。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诗歌是“原创”,而阅读,则扩展了其表达的广度和深度,并让他的诗作在丰富性上获得了根本的保证。这样的写作无疑是一种非常有益的文体探索。
——李商雨
投稿信箱:lisychengdu@163.com
新青年
00后诗人张雪萌的诗歌在叙述上具有主观意念的恣意性,其强烈的感觉和触觉通过描述性语言让其陈述命题得以在句法的变化中被复杂地表达,在看似驳杂的意象组群里,这些诗歌材料的汇集密度存在着相互释义的功能,同时也有着互相阻碍的设置,譬如《蝴蝶》一诗,“那只蝴蝶越洋而来了”而引发的一系列主观意识流形态:德先生、赛先生、虱子、耗子、鸽哨、假柿子、瓜子皮……由每一个意象单一的行为逐渐聚合,诗歌的容器故意塞满了时空交错的混乱,诗的叙述节奏和层次像藤蔓杂而无序。这种诗歌技法写作稍有不慎就会造成诗歌表达意义上的迟缓和呆滞,而我们看到的是张雪萌依靠强大的描述性手段,通过一系列浓密的意象和修辞策略,利用夸张、反讽、悖论的诗歌技法驱使客体不断完成了自我集合与分离的动态“表达”过程。
张千千的诗歌多以人称代词的有效叙述而力图保持诗歌的客观经验,以体现主观意愿的验证性。在诗歌中喜欢呈现故事性和戏剧化场景,试图避免诗歌意象、物象以超现实主义方式取自于主观或者经验的自语、自洽与自造的语境模式。其由点到面的叙述角度有着逻辑上的并置与转换,并带来了舞台剧的具象化效果,独白和对话形式的入诗展开了诗歌内容的丰富性和色彩性,改变了常见的诗歌叙述场景和叙述角色的因袭因素。在《半程》《晚酌》等诗中,张千千多次用了明喻“像”,就如同以色列诗人阿米亥喜欢动用明喻“像”一样,诗歌有着个人独特经营的预设能力。
相比张雪萌和张千千,年轻的杜华阳和简敏的诗歌相对来说,讲究节奏与意象的和谐性,诗歌情感与情绪自然交融,节奏与语义的起伏都有着明晰的抒情况味。编者认为诗歌不是过多材料合成的金属,很多时候没有必要在坩埚里通过搅拌、熔解、提炼,诗歌有其自然的天赋与状态,主体与客体相矛盾的“我”如何延续这种诗歌的自然性是对诗人诗歌写作的一种非常挑剔的考验,就如同葡萄牙诗人佩索阿在诗歌写作中曾独创了“知心的我”(me self)一词一样,也即思考与存在是同一的。杜华阳和简敏的诗歌多数依靠“我”为第一人称展开,写我见、我思、我乐、我忧,杜华阳沉溺于日常细微事件的借物抒情,将生活和情感碎片化的记忆拾掇于一起,形成了诗歌抒情的一个整体性;简敏的诗歌具备了唯美、决绝与空旷的意味,诗歌追求形而上的意象和物象,并加以驾驭,让诗歌有了某种审美层次上的辽阔之感。
——樊子
投稿信箱:fanzi1967@163.com
现代诗经
又到了草长莺飞、万物萌发的三月,本期适时推出一组“她们”的作品。其实,在这里编者并不想过多地强调女性的性别身份,因为在生活中,特别是在现代生活中,每一个体都充当了多重身份或角色,性别只是其现实生命形态的一个面相。但另一方面,诗歌又是一种生命的表征,介于现实和理想之间。在现实中,有时候,也许“她们”不能选择所要的生活,但“她们”可以选择诗歌,并在诗歌写作中获得一种生命的升华。“她们”的生命长于感性,其写作带给读者的是最直接的感受力,情感表达的细腻,文字和场景具有某种裹挟性和代入感,有着真实可触的生命质感。具体到每个人,“她们”的诗歌表现又截然不同:桑子的诗偏于想象和哲思,感性与理性交织,有着巾帼不让须眉的胸襟;白小云在诗中追求一种臻境,在美与真之间,她更倾向于前者,为此,她不惜付出满腔的爱;南音的诗中有一种寂静中的喧哗,她的音符向天空和大地敞开;武稚的诗如溪水积聚,低缓徘徊,柔肠百转,有着对生命的守候和探寻;三色堇的诗诉说着眼中所见,呼应着内心的景象,有光影的变幻,人世的苍茫;吕达的诗沉思中有思辨,有美好的愿景和爱;范明的诗追求自然的表述,她波澜不惊的叙述语言将人们代入她所营造的诗歌空间。
——黄玲君
投稿信箱:lingjun0316@126.com
国际诗坛
或许所有的抒情诗都是挽歌。安妮·塞克斯顿是写缺失的诗人,这比绝大多数抒情诗人更为确切和耐久。她是在心理医生的建议下开始写诗的,作为对产后抑郁的一个处方,写作最终成为她日常心理治疗的一部分。不仅如此,后来所谓的自白派的最经典的意义,也就显示自白和心理治疗具有一致性。塞克斯顿用超现实主义手法、调侃的语调强烈表达女性的时下处境、极度精神压抑和情感痛苦,同时包含着对美好乃至令人崇敬事物的追求。她的诗作敏锐、坦诚、有力,她努力追求感情急剧转变的、近似自言自语的风格,与个人的梦魇反复格杀,终至精疲力竭。不论她的诗看上去可能会是多么痛苦,却都是对生活的肯定与生活的庆典——这就是诗的全部。
——阿翔
投稿信箱:a_xiang2003@163.com
评论
诗歌写作是一项艰苦而复杂的精神劳动,一个优秀诗人的文本创造,总是凝结着大量的心血。而作为诗歌批评,就不能止步于理论的高蹈或大而化之的评价,而应深入到文本的肌理或细节中去勾玄探秘,充分展现诗人创造的复杂与精密,这样才能对得起诗人的劳动。本期推出三篇文章,周东升分析了多多的《痴呆山上》,通过精彩的文本细读,展现了多多诗歌文本的精密幽微而又生气淋漓的面貌,同时结合文化研究方法,进一步对文本隐藏的现实感和忧患意识加以阐发;西渡分析了伽蓝的《星空盖顶》,在细读的基础上,又结合比较研究和阐释阅读,对这首朴素小诗所具有的经验性、实践性的现代性品质进行了充分的展示;彭志的文章评论了川木的诗艺探索,细致分析,体察入微,也值得一读。
——刘康凯
投稿信箱:lerkai@163.com


 纯贵坊酒业
纯贵坊酒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