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仲义: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评点
(2006.5.14福建晋江: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颁奖会发言)
诗刊社主办新世纪以来十佳青年女诗人评选活动,60名后选人经专家评选,刚落下帷幕,有幸作为评委,在颁奖地举行的座谈会上,临时做了评点。面对新世纪丰富多彩的女性诗写,笨拙的知觉囿于有限篇幅,不免粗疏。欠妥处就教于读者尤其女读者们。
[路也]
我对路也的评语是“诗意的小说化调性”。并且称她是一个“后退”的诗人。
近年她的《江心洲》系列,是用小说化调性叙述她“诗意的栖息”理想。江心洲——可以看作是女诗人地理与精神的共同家园,据此来涵纳心灵的寄托。江心洲系列让她孤苦的写作释然多了。我特别喜欢其中的《木梳》,诗人摒弃时代的物欲,怀想从前的日子,那是长亭古道式的临水而居,是沁园春与如梦令的生活。显然她是在推崇一种缓慢、悠闲和后退的生活,是有点不合时宜,但看出女诗人对于时代的抵抗与宽容,体现了一个纯棉女人特有的简朴、自我追求的尊严。在世俗生活的诗意提升中,的确有一股绵长细腻的根性力量。她的诗写,从容通达,充溢着古典情怀,且视阈辽阔,心胸清朗。
[蓝蓝]
大概是早期印象使然,评选中我对蓝蓝不暇思索写下8字:清纯、率真、透明、宁静。
她与大自然、土地高度亲和,用露水般的新鲜、生命、热爱、和灵动歌唱。她的最大优势和特点,是来自于大地,乡村,带着泥土、野花、溪水的气息,自在地歌吟,所以她不刻意技巧。因为对城市的拒斥和深刻的童年经验,所以她还能保持不被污染的天然质地,这是当下很不容易的品质。梦亦非说她,与四季的生命亲切感应、交谈,她写的是人间烟火,但深处却脱尽烟火之气。耿占春说:蓝蓝的诗从哀歌式的赞美向讽喻式的批判的转变。我是很赞同的。后来的这种转变带着较多理性的坚利。总体上我觉得她的诗有一种轻微的叹息、温存的忧伤,和一种淳朴之美。我倒希望蓝蓝在转变中,依然不失庄稼从地里长出来、那种感性的流淌状态,那种在“阴影”与“毒刺”中闪耀的“童贞”。
[安琪]
我有一篇长文专论安琪,题目叫《纸蝶翻飞于涡旋中》(山花03.12)这里简单再说两句。安琪有两个突出优点,一个是发散式思维,能在瞬时间将全身心调动起来:感觉、想象、意念、意识流,所以能做出男性诗人那样的跨文体写作,像《轮回碑》堆满十几种文体:儿歌、邀请函、访谈、演出、菜谱、词典、处方、案例、任命书,以及用括号标明的“后设”文体,这是需要一种杂芜包容的能耐。
另一个优势是,安琪对语言的应急能力相当出色。语言的搭配、组装、交互、畸变,她应付裕如。语言的外遇、私奔,一直处于高发冲动和瞬间婚变的临界。几年前,我曾下过一断言,就诗歌语言天资看,安琪在全国女诗人行列里,是最具潜力与挑战的人选之一,至今,还确信不疑。安琪今后如果要更上层楼,一定不能放弃精神元素。
[娜夜]
娜夜的爱情诗写得短小、鲜润而丰盈,往往通过日常境遇不经意的捕捉,给人惊喜。比如那么多人写《起风了》,但我觉得就这一首独树一帜。
“起风了/我爱你/芦苇/野茫茫的一片/顺着风//在这遥远的地方 不需要/思想/只需要芦苇/顺着风//野茫茫的一片/像我们的爱/没有内容”。“起风了”,是自然界的,又是内心情感的。“我爱你芦苇”——是暗暗的呼叫,又是赤裸的表白;芦苇,是特指的实在的称谓,又是隐匿的对象的代码,而回应这一“植物”情侣的,是两次出现“野茫茫的一片”,情语通过景语“对接”,是如此的天契地合。
“野茫茫”——秘而不宣、含而不露、言尽而意远。是爱欲,和生命的高峰体验。“野茫茫”——没有内容的感性注脚,两者共同指向广茂和超迈。女诗人就这么用——起风了、芦苇、野茫茫,三个简洁词组,提起起小诗的重量。总共才9行52字(比七律还少4字)。写得异常简淡、简约、简隽。
透过这一阵风的吹拂,也许我们可以闻到娜夜的整体芬芳了。
[鲁西西]
中国诗歌缺乏宗教感。在现行诗人中,鲁西西是屈指可数的。祝福、忏悔、宽容、慈悲几乎贯穿她后来写作。这使得女诗人拥有强大的精神背景;许多诗作有了泛灵论倾向。
《喜悦》是其中突出的文本之一,为主人翁所遭遇的神迹做出极为形象的“论证”。可贵的是,鲁西西的诗作没有强直性的布道、说教,而是将神性感动弥散于唱诗般的和谐中,用感同身受沉入事物的冥想里。
一种信仰的抵达与成功,可以改变诗歌的质地,可以提升诗的想象和感觉能力;诗人也可以在瞬间获得神的祝福,并由此把福音传递给他人。
这里要提出的问题和再次强调的是:在宗教感和神性普遍匮乏的国度,鲁西西所做的一切是颇为稀贵的。
[海男]
海男有语言“魔女”之称。这次我写的评语是“自我臆想的迷幻花园”。她是名副其实的迷幻诗人。
记得海男曾说过,我依赖于想象写作,我喜欢在一个寂静的空间里想象无穷无尽的问题,我依靠游移不定的暗语写作。
从海男的写作中容易概括出这么几个关键词:臆想、自白性抒发、绚烂的女巫气息、燃烧的意绪、纠缠的迷宫式言说,共同组成海男幽深的花园。那里幻象跳动、扑朔迷离,有身体成分、死亡意象,以及神秘氛围。
海男同时用三种文体(小说、散文、诗歌)写作,令人赞叹她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总的看来,三管齐下的语言,相对比较一致,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不知不觉进行混同。也许将语言分而治之,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和效果?
[李小洛]
应该说,李洛是幸运的,为何在那么多70后女诗人写作中,独独她被选中脱颖而出?我想主要是别有气质。我一时还说不清楚,似乎是年纪不大,就有一种随意、悲凉,看透人世的趋向;没有同时期女性的过份自恋,就对命运的悲剧和虚无展开叙述,真挚诚恳,且多自嘲自省,在哀伤中保持豁达;在独来独往的行进中,比同年龄有更多领悟。
《乌鸦》中写一只乌鸦背着影子,引领亡魂,在天上飞。《响声》中写道“我开始给自己制造响声 /把房间、走廊、凳子、椅子 /把碗筷、钢笔、报纸、床铺 /弄出了一种巨大的响声 /这样,我就感觉我还在活着” 《逃犯》中写到“我想我应该是从牢房里来的吧”“我知道从一开始我就是/一个要不断逃跑的囚犯——这一切,正指示着李小洛有自己深切的路径。
[荣荣]
有评论说荣荣是个意义独特的诗人,好比诗歌界的池莉,理由是她娴熟地瞄准当下底层市民的生存状况。不管这个类比有多少准确和获得多大认可,用荣荣自己的诗来说,她描写的是“在正常人腰部以下的世界”。从而道出荣荣平民化的性质,是属于和煤球、汽车尾气联系在一起的写作。
除此之外,它还具有都市路口“探头”的“跟进”功能,许多诗的射线直指人心的脆弱、阴郁、无奈,不时涉及死亡、疯巅、生病、衰老,表现了女诗人特有的关爱情怀,而且如同她“快人快语”般的犀利:“当我在梦中哭泣,我悲伤的/不是没人推醒我,而是摸不着开关”(《心情》)“一篇使内心喧闹的小说/我在其中,阴影连缀起/一个个千疮百孔的细节”(《避免》)。可能有些粗放粗砺,但具有男性化特点,有较强的质感和冲击力。
[林雪]
林雪经历了情感世界生死轮回和脱胎换骨,没有早期女生们容易患的浅显稚嫩,一开始就写得曲折、幽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她忠实于个人的隐私与疼痛,无情而大胆地呈露出来。她似乎特别专注沉湎于个人的高峰体验,被动地承受生活与情感的重压,因为执著内心的绝对真实,执著生命与女性经验,所以作品相对较少但一向保持较齐整的质量。
林雪的孤独、沧桑和积郁,使得诗歌的情感世界丰富而深刻,也由于语言的精致打磨,她的不少诗句有着树脂样的质地,(像“春天是腮腺炎”“夏天是痱子”之类)。而《苹果上的豹》,这一代表性诗题,能成为新生代诗丛书非常适合的命名,可见其标识性决非是偶然的。
林雪出道较早,后来的路子逐渐拓宽,但骨子里的高雅没有改变。
[杜涯]
如果说林雪是“贵族”式的,杜涯则偏向“贫下中农”(这里没有丝毫贬低的意思)。杜涯的诗歌如同她的性格,给人诚恳,本份的印象。是有点中规中矩。至今还保持着十分低调和隐忍。
杜涯深受谢冕先生的赏识。她用功努力,出过《风用它明亮的翅膀》等4本诗集。从许多题目和内容,可以看到她总体风貌的晓畅、敦厚、平实。她的淳朴有目共睹。
杜涯相对较少写到人,至少在早期是这样,这证实她想逃离嘈杂的人世,只保持与自然、乡村交谈,并且“只有在赞美的领域里才悲哀”。这样的单纯有些“冒险”和让人不太满足。幸好后来杜涯有所改进。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在后记中写道:“真正的诗歌应是无声的,是沉默。我写诗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回到沉默。”并且实践到底。
这是一句很有价值的诗歌箴言。的确,无声与沉默,是诗歌一种极高的境界,尤其在喧嚣的当下。
原载《星星》诗刊2007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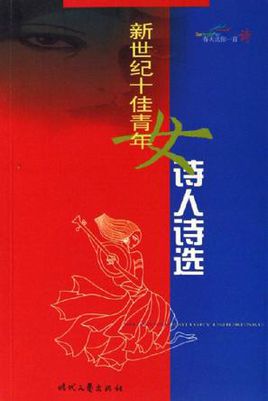


 纯贵坊酒业
纯贵坊酒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