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于《 从边缘出发 》
漳州师范学院2003教育系心理学2班 熊旭峰
【前言】
《从边缘出发》:首届非师专业职业技能竞赛之“校友访谈录”一等奖作品。作者:吴地梅
该作品素材多取自对女诗人安琪的访谈,其内容展示出来的画面感真实强烈,可读性强。但笔者认为:单从有限的对话中去探究诗人的内在质地,多少有些浅尝辄止,余犹未尽。
故本文另辟蹊径,转换一个角度通过分析女诗人不同时期的诗歌作品,同时结合诗人当时所处的生活背景,试图挖掘诗人安琪深藏于心的真实和深入底里的精致。
历经数届接近诗歌节,从开始到现在每次都会请来一些漳州本地诗人。跟他们也有过藕断丝连的联系,知道私底下这些诗人们跟普通人一样。吃饭睡觉。结婚生子。偶尔争吵然后又重归于好。
其中有一位诗人,她叫安琪。一个“血液里有背叛的东西在作怪”的女人。极不安分并且行踪诡秘。
因为深入骨髓的叛逆,安琪没有安于呆在漳州这个安逸闲散的小资城市,毅然北上闯荡。并开始在那片完全陌生的领域扎根。南北距离的遥不可及也是安琪迟迟未在母校诗歌节露面的原因。
其实对安琪的深入了解是在好友吴地梅和陈素芳对她进行专访并整理成校友访谈录《从边缘出发》一文之后。
细细品读,从字里行间发现安琪这个不安分的女人从头到尾都一直在蜕变,在“像杜拉斯一样生活”,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至少在我35年的生命中,我的影子接近了杜拉斯的生活,接近了诗的生活”。
杜拉斯,女人的梦游者和可能。
这是安琪写过的一句诗。整个诗歌的语言结构呈现出一种反抗挣扎而又带有些许期冀的姿态,但又似乎摆脱不了世俗的偏见与压制,所以只能在梦游状态来完成这一对天性的解放。安琪的确是不安分守己的,她沉溺于内心强烈的渴望之中,与现实的约束和世俗习惯化的“三纲五常”分庭抗礼。
“女人”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把她与华艳高跟鞋、丝蕾花边长袜联系起来。似乎女人天生就应该被这些东西来装饰。很少有例外。如果真有例外的话,我想女诗人安琪就算其中一个另类。她特别不喜欢穿皮鞋,甚至连袜子都不喜欢穿。这个女人违反常纲,让人不可思议。
安琪至今惟一呆过一年以上的城市就是漳州和北京,所以其诗歌作品的写作素材全部来源于这两座城市,两座城市的事件也悄然在她的诗歌里面发生。诗歌与生活已经融为一体。
然而令人神往的大城市并非是想象中的天堂,要想在北京立足更是需要莫大的资本。一个城市的三次辗转迁徙,安琪已习惯了与亲人朋友失去联系的落寞无依。对于北京她是陌生的。她是一个孤独的挣扎在城市边缘的人。
选择与放弃已在于一念之间,而此时光明与黑暗亦只有一墙之隔。
也就在这面临艰难抉择的时刻,安琪坚持下来了。面对欲来的风雨,她抬起自己的肩膀笑脸相迎。也正如《从边缘出发》说的,“是的,安琪之所以成为安琪,就在于当俗世的生活成为艺术的阻碍之时,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放弃生活,而让那求知的欲望和或喜或悲或狂乱或无力的创作激情在那未知的空间里闪烁”。
然而在这放弃生活选择艺术的过程中,安琪的意识观念及思维结构也悄然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女诗人心态平静,生活状态安适。对于前途没有太多的野心和奢望。所以,1997年的诗集《奔跑的栅栏》结集之前,安琪的作品诸如《干蚂蚁》、《未完成》和《节律》等诗作整体风格倾向于唯美与平衡,颇有抒情意味。
“这是春天枝头的干蚂蚁/在我的手心它灼痛了我/和有着太多欲望的星辰/来回流泪,不经过土地和天空 / ”――摘自《干蚂蚁》
后来,安琪则受美国诗人庞德的影响,风格偏向意象派,主张“要在转瞬间呈现给人们一个感情和理智的综合体,也就是说意象的形成意味着感情和理智突然结合成一个综合体。”(庞德语)同时期安琪推出诗集《任性》。诗作的语言已开始从黑夜意识淡出,这一次的蜕变使“以语词为中心变频的碎片写作样态”过渡到“另一种与更直接开阔的历史现实对接的互文性。”语言运用飞舞张狂,思维的超频跳跃,内在张力过度消耗成为这一阶段的特点。
再后来,就到了安琪北京时期的作品《像杜拉斯一样生活》。诗中呈现的杜拉斯已经与年轻毫无关联。满脸皱纹。牙齿脱落。步履蹒跚。但也就是这个七十四岁的杜拉斯用一种飞扬跋扈肆无忌惮的几乎疯癫的语言创作出的自传体《情人》并获法国著名的龚古尔文学奖。这个备受争议的女人生活独立豪放,她不但拥有不只一个情人,并且越老就越将她的热情她的张扬她的火热演绎地淋漓尽致。世界上许多崇尚自由的女性都把她的《情人》奉为“圣经”。
也就是这个与众不同的老女人把安琪带到了一个超越性别的空间。在安琪的诗里,这时已经越来越难意识到诗人的女性性别了。
女诗人对杜拉斯歆羡,同时又苦于现实的乌云挥散不去(安琪进京一年后离婚独居),所以安琪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杜拉斯身上,以虚幻的投射来释放内心的情感火山。
或许是脱离短暂休眠后的女诗人,由对现实的思考转换了角度,“亢奋”过后归于平静,并对诗歌创作进行了重新定位和探索;也或许是女诗人文学地位的稳固和提高,安琪作为“中间代”的杰出代表,在诗歌言语的驾驭上在更趋于现实的内敛和控制。但不管诗人如何的控制和内敛,我们都可以在其诗作中感受到一种不安和捉摸不定。如:“你低着头假装很安静/ 假装不知道安静的安,安全的安,安琪的/ 安 /无数人问我:安/或者不安?却不知安和不安其实是一码事/其实,那么多年你一直在/诗歌里,比较疯狂/比较不在小说里”(出自诗作《赌徒》)。
这样看来,女诗人安琪一直在原来诗歌创作状态的基础上进行新一轮的更迭和重建。而这种更迭和重建根本就在于诗人不安现状的生存方式。新的方式的建立与旧的秩序的退出必然引发内心的极度矛盾,甚至恐慌。要知道,每一次改变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毕竟,任何一种诗歌风格的产生对读者和诗人们而言都要有一个接受,然后适应的过程。
但这一切都正因为安琪清楚地知道,每一次蜕变都可能是重生。后退几步确定一个新的起点,原来是为了要跳得更远。而事实也证明了《从边缘出发》中对女诗人的描述“一个认准适合自己的目标,从边缘出发的人”。
“从边缘出发”。我想,这不仅是对女诗人安琪的个人写照,更是对我们一种深刻的指引;而诗人近十年生活情感以及诗句的淬炼便是对“从边缘出发”最完美的诠释。
那么,“像杜拉斯一样生活”则呈现出安琪“自私”的“不足与外人道也”的内心独白。因为这是一种如履薄冰的危险,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身入其中并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抽身而退的。
而给这世界留下的,那些或张扬或唯美或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诗句也证明着这种别样的生活。像杜拉斯一样的老而弥坚,越发绽放着迷人的风情。或许,这就是女诗人一生所追求的一种完美状态吧。
可以满脸再皱纹些
牙齿再掉落些
步履再蹒跚些没关系我的杜拉斯
我的亲爱的
亲爱的杜拉斯!
我要像你一样生活
像你一样满脸再皱纹些
牙齿再掉落些
步履再蹒跚些
脑再快些手再快些爱再快些性也再
快些
快些快些再块些快些我的杜拉斯亲爱的杜
拉斯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
爱的。呼——哧——我累了亲爱的杜拉斯我不能
像你一样生活。
2006年3月2日
 李小白。20150625,作家网。
李小白。20150625,作家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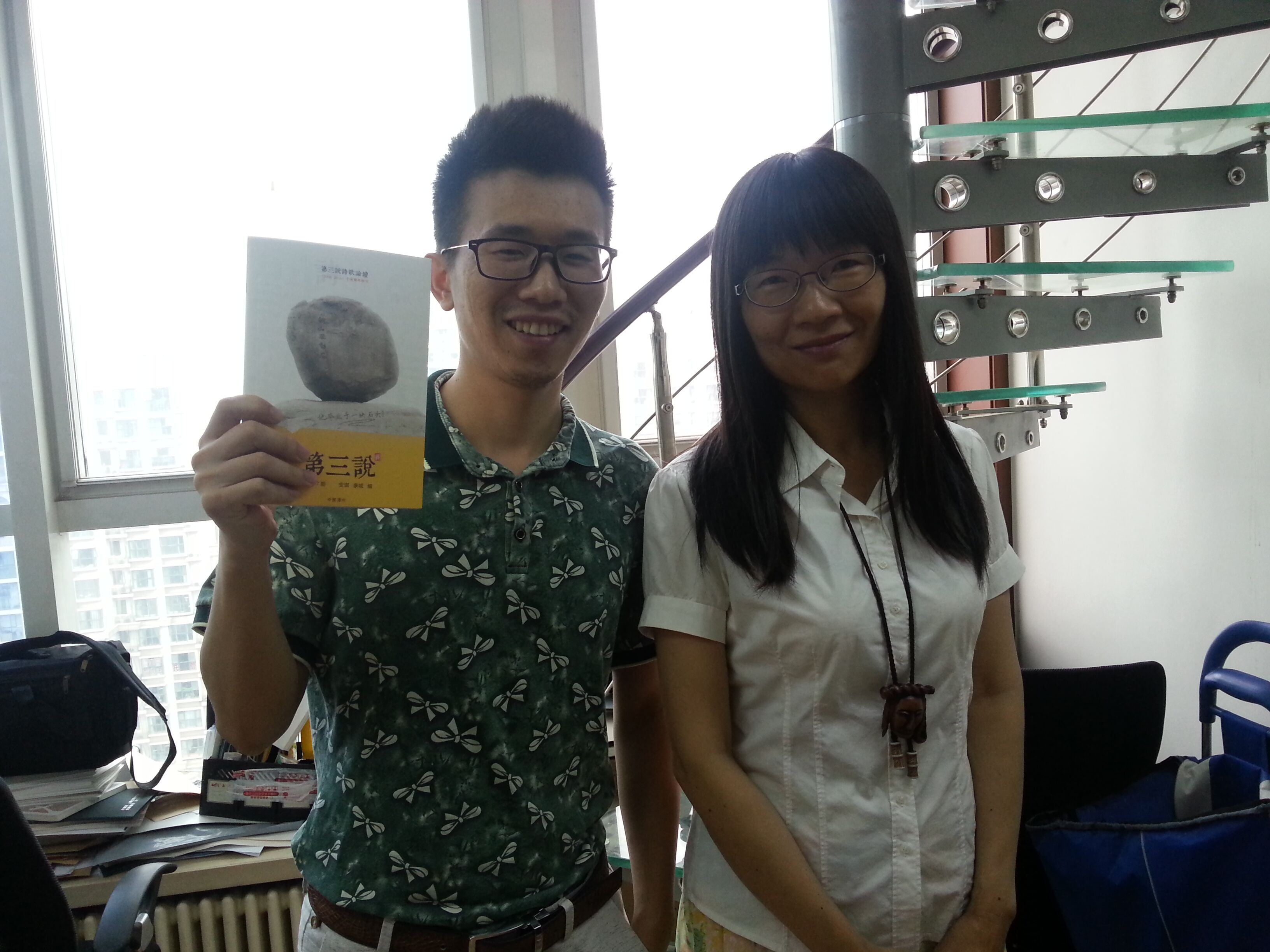 作者与安琪合影。20150625,作家网。
作者与安琪合影。20150625,作家网。

 纯贵坊酒业
纯贵坊酒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