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书写与乡土反刍
——读沙克诗集《诗意的运河之都》
作者:张德明
捧读诗人沙克寄来的诗集《诗意的运河之都》,内心有无限的感慨和回味。这部厚达400多页的诗集,是沙克从事创作四十余年来重要诗作的一次精品荟萃和实力展示,从中我们能窥见到诗人对宇宙人生的深刻领悟和对故土亲人的殷殷深情,也能对其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和艺术风格获得较为全面的了解与认识。这部诗集以“运河”流域为基本的观照对象,将这个地域的特定历史与现实加以艺术的彰显,在地方文化书写上具有突出的审美价值。与此同时,诗人虽然出生于城市又生活工作于多个城市,但是在他童年少年时期,有过随做医师的父母从城市下放到运河乡土的公社医院生活多年的深刻体会,成年后也有在运河流域城乡之间往返穿梭的丰富经历,促成了其对那片乡土的深层次体味和理性化反刍,在此基础上,他对乡村、对故土的理解和领会,又达到了一般诗人难以企及的认识程度。
吉狄马加称赞沙克的这部诗集是“用诗歌的方式为河流立传”的典范之作,我认为是极为精准的。也就是说,沙克通过对运河流域的风物与人情的艺术书写,将萦绕在河流之上的鲜活的历史情貌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我认为,如果说《诗意的运河之都》是一部精彩纷呈的诗化史书的话,那么这部史书所揭示的历史无疑又是多样性和立体化的,既有河流史、家族史,又有故乡变迁史和地域人文史,而且这几部历史并非彼此独立、互不相关,而是相互对话、相互交织,共同成就了运河的人文景观,也共同组构成沙克诗歌迷人的诗意世界,因而值得我们细致地品读和深入地剖析。
在《大运河简史》中,沙克深情地歌咏道:
那么长的游丝,贴在地上
曲延向南,串通着一些水系
拴着一些码头与祸福
一支船队,一个家,风雨不阻
这条流动的路,永远弯曲
船棚里的一辈辈人,跟着弯下腰来
或弓身摇橹,承载着命运走向
这该如何叙说是好,河床下的祖母
躺在九泉,期待什么啊
赵钱孙李的命,就是漂泊
活着的全部艰辛,是为了上岸
建一个直得起腰来的家
在家的胸口建城
叫运河之都
这首诗并没有用叙事的笔法去大量地铺叙大运河的发展历史,而是以一种审视的目光来凝望和思忖这条河流,将河流的流向与河边人家的身世命运等统筹在一起加以艺术写照,并以“祸福”“漂泊”“艰辛”等词汇来反映运河流域的人们真实的生存境遇和历史情状,从而写出了历史深处的疼痛与内蕴。可以说,这首诗为整部诗集的情感表达定下了某种基调,它告诉我们,诗人对运河历史的审视与表述,绝不是一种非理性的颂扬、高分贝的夸赞,而是以带有反思性和内省性的观照视角,通过理性烛照这条河流以及河流串接起来的这块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写出了河流所具有的错综复杂的精神情调,从而将历史内部藏蕴的无限深意有效地挖掘出来。
历史是过去时光留存下来的斑斑影像,时光的流向、河流的流向和历史的流向都是线形的,它们之间因此往往有着某种精神同构的内在关系。沙克对运河史的书写,就注意写出了这种滚滚奔流、不断向前的生命特质:“淮河故道像线/穿过一只地球的不锈钢的象征/穿起一部地理账册/这里是中国大陆的南北分界线/淮水裹浃着朝代滚滚东流//地理中收着历史/两岸景色中含着世俗人情/折柳,送走家家户户那些难念的经/扬鞭,送走西洋传教士/送走东洋人马全都送进黄海//不锈钢的地球/洋气着,把原始的垂柳芦苇压下去/河面的老桥墩,是异番痕迹/仿佛是工业文明曾经欺负农业生活/留下的水泥和铁的欠条//淮水之阴的城市早改成新名字淮安/吉祥如意,淮水安澜/穿城而过的古运河多了几座拱桥/都在做挺胸弯腰的健身运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南北之中/显得过时的物什见天见多/人人事事,悄然刷新/有如流波裂变产生着换代的放射性”(《南北分界线》),这里对淮河简史的精彩写照,那高度概括性的描述文字,让人能迅速睹见到淮河流域的历史发展和人文变迁等状貌。
历史其实并非就是冷凝的、固化的和静态的存在,真正的历史必然是活着的历史,是今天的人们站在当下的时间节点上回首过往而目睹到的景观,基于此,历史的呈现中往往有着过去与当下的对话和互文。沙克的《夜游清江浦》就是在古今对话中书写河流历史的诗作:“微浪拍岸/黄香蒲卸了黄花/结了绿豆荚,长叶触碰亭栏//夜行船/游的是隋炀帝的河床/前些天的水/看的是岸上的灯/此时此刻的光//造景的人历经数朝/开埠的人陈瑄是六百岁铜像/站在岸边默看船闸、塔楼/辨认禅寺、庙观、庵堂的新旧版本/胸怀久远,感念当代//摩天大厦高过古城太多/夜行船游东瞅西瞅都不瞅它们一眼/黄香蒲的绿豆荚像厚厚的嘴唇/抿着玉米牙不插话//上下夜行船的人/走的是御码头游的是六十里古迹/从韩侯故里到漕运总督府/再三打听清江浦的水缘来头/原来直通中原黄河”。诗人与一群朋友夜游清江浦,游历之中浮想联翩,思绪万千,在“胸怀久远,感念当代”之中,写出了以今人之目所能睹见到的真切历史,给人带来可以闻见、可以触摸的鲜明历史感知。
除了书写河流的历史,这部诗集中还有不少篇章是对家族历史的艺术演绎。《1935年的照片》《小姑爷爷的牺牲》《两本家谱的故事》《二叔祖父的抗日》《家,一直都在》《我的籍贯在命中流淌》等等,都可以说是这部集子中书写诗人家族史的代表性诗作。沙克的祖父是地下党员,父亲是新四军红小鬼,都为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奉献过青春和热血,这也是诗人引以为傲的事情,是家族史中闪光的一页,在《祖和父,镰和锤》一诗中,诗人先是交代了祖父和父亲的光荣历史:“我祖挥镰/另一只手为村野及城镇写字/他收割麦子,也收割鬼子的性命/他职业是教师,性质是地下党/我父一手拿锤/另一只手在战争及和平中看病/他敲击伤病,也敲击敌人的脑袋/他职业是军医,性质是共产党”,后又对祖父和父亲带给自己的骄傲和荣光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和极力的歌吟:“你用好莱坞巨片/也换不来我的泛黄照片/1939年我祖棉袍子染血/1946年我父灰布衣染血/那种红,与所有的红不同/是拿性命去革命的红/是热烈的基因//我的基因红,必须的/思考如镰,劳动如锤,关键是真和力/流连于家庭相册和网络博客/我祖我父给予的这种颜色/我喜欢,是涂改不了的身世”。为自己家族光彩的历史而欣喜和自豪,这是沙克书写饱含血亲痛感的家族史时自然流露出的一种真实情感。
沙克的家族史书写,既有对祖辈历史的追忆,也有对个人历史的回顾,而这份个人历史回顾图中,最有标志性意义的符号就是“家”了。创作于1987年的《家》,以时间为线索,展示了诗人对处于分离与团圆等不同状况下“家”所具有的意义和味道的深刻理解与认知:“很久很久以前/它是一片无垠的荒野/父母亲勤苦地耕作/哥哥是种根/弟弟是种芽//说不清哪一年/它变成多难的邮车/父母亲是游离的信封/哥哥是揉皱的信笺/弟弟是信的辛酸内容//在喜悲交加的那一天/它切为一道冷漠的海峡/父母亲是苦涩的海水/哥哥是盼归的码头/弟弟是颠簸的小舟//祈求,但愿——/它化作一张完整的合家欢/父母亲笑坐在中间/哥哥守在石边/弟弟护在左面”。“家”在变化,“家”也在发展,在“家”的发展与变化中,家庭中每个人的个人史,也在默默地书写和生成。
在沙克的家族史书写中,“家”并非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常常与“国”连在一起,如《怀里的祖国》《日常颂》《我与国》等,这是具有深厚中华文化底蕴的家国观的生动体现。以《日常颂》为例:“请允许我使用颂词/采取贴身的表达/这样的话语更亲切、真实//列祖列宗是家/开门立户,我敬爱着/世世代代是国/和睦兴旺,我热爱着/我和孩子是人民/康安吉祥,我自爱着/家谱相册是历史/刻录着成人成家成就的大不易/生命消长,硬骨传承/其中的苦厄与抗争,光荣与梦想/是无尽的家产我珍爱着//我在歌颂家常生活中的吉光片羽/善美的人性、文化及情感/还有汗水与钱币、耐磨的性格/我表达生老病死的动态/唇齿嗑碰,心有忧患/每个家人甜多于苦,过得实诚/这物质,这精神,这数据/是常态,如这年头越来越好”,国富民强,国泰民安,这是中国人从古至今都信奉的一种人文关系式。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的思维习惯里,家庭的发展始终和国家的命运牵连在一起的,家庭的现实状况也是国家状况的生动折射,在《日常颂》中,沙克以颂词的形式,表达了对舒心快慰日常生活的由衷赞美之情,在家国一体的观念之中将日益兴旺的家族发展状况加以形象表述。
故乡变迁史和地域人文史也是沙克绘制的历史版图中较有分量的两个部分,也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对于城乡的发展与变化,沙克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也乐于用分行的文字将这种发展和变化加以彰显和诠释。诗人惯于运用对比的手法,在今昔比照之中将故乡前行的历史脉络勾勒出来,如《中国苏北,历史进行曲》一诗:“斗笠在淮河上走/斗笠在独轮车上走/斗笠在海滩上走/碧绿的运河在斗笠上走/浑浊的黄河故道在斗笠上的茅屋上走/血红的太阳在移民的鸟巢上走啊!//所有的斗笠的传统,都顶在苏北的头上/把斗笠翻过来,机器、电脑/高速公路、信息技术的事物在斗笠下走/机场的跑道和城市化的电锤在斗笠下走/斗笠下面/矗立着小跑的苏北大地!”“斗笠”意象构成了诗人观察苏北变化的生动比喻,从前的斗笠是苏北人沿着河滩艰难前行时的遮阳帽,而倒立的斗笠则是当今苏北在现代化征程上大步向前的一种昭示。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化之中,故乡飞速发展的情形由此可见一斑。对于地域人文史的描述,沙克主要通过对那片土地上曾经出现的历史人物的诗化演绎来实现。在运河之都——淮安市,出现过许多历史文化名人,如韩信、枚乘、吴承恩、刘鹗、周恩来等,也有不少历史人物曾在这块土地上留下自己的足印,沙克的《韩信在乡》《淮阴侯至今藏着成语之冕》《草民之帝俯瞰淮海》《一对祖孙皇帝下江南》《问李煜还有几多愁》《写一位明代状元》等等,光从这些标题上就能窥见到历史的踪迹。另有一些诗歌,虽不直接书写历史人物,但也借助对地域文化某一侧面的描写,将其中藏有的历史韵味有效揭示出来,比如《伯仲之地》:“烟花,琼花,月季花/拿捏江南雨花/运河,里下河,盐河/渔船货船游船……顶着蓝印花布/温润、水性的淮扬//抓不住它几万条小辫子的淮扬/懒得叙帝王将相/伯仲分户,裙带交搭/大碗阳春面喂成了千百个诗书人家//淮扬近亲,烟雨不分/蟹黄包子和口含绣球的狮子头不分/胸骨里的经史学问往外胀/淮安扬州的牙齿舌头通灶神”,这里描述了千古淮扬的商业文化、饮食文化、读书文化,通过这些文化的写照,特定地域的人文历史也悄然敞现出来。
如果说历史书写构成了沙克诗歌美学表征的第一层面的话,那么,乡土反刍则构成其诗歌艺术构造的另一层面。小说家、诗人邱华栋曾将沙克的这部诗集视为怀乡寻根类书写的美学样本,对其创作成就进行了充分肯定,并深刻地指出:“怀乡寻根类的文学有它的哲学依据,一切生命都将回归精神本体,而非是指‘从城里到乡下’之类走偏的单维价值取向。”这是相当富有见地的。邱华栋的话提醒我们,对于故园乡土的写照,不是从迁移的空间学轨迹上去考量那么简单,而是应该站在人类的精神维度和生命本体的视野上审视,才能达到更高的情感强度和精神指标。也就是说,必须在反思性和批判性的立场上来重审作为我们出生地的乡土世界,给予更理性的判断和评价,从更深邃的层次上将诗人的忧患意识与人文关怀表达出来,才能更贴近怀乡寻根书写的美学本质。在当下中国诗坛,怀乡寻根类题材的诗歌极为普遍,但很多此类诗歌在思想力度上是极为欠缺的,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对诗坛上存在的大量伪乡土诗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评,文中写道:
在乡土中国的风俗习惯里,故乡是一个特别令人珍视的地方,那里的山川草木、人事物情,似乎都闪着奇异的光泽,令多少游子梦绕魂牵,迷途知返。而浩如烟海的中国古典诗歌,把大部分的篇幅都给予了乡土这块领地,中国古代卷帙浩繁的乡土田园诗与乡土中国的农业文明之间构成了深度互文的关系。但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的不断拓进,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世界正在不断瓦解,因此如果当代诗人还沉浸于对传统乡土田园的非理性、盲目式讴歌与咏赞之中,那么他写下的诗章所具有的真实程度,必然是可疑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不站在当下城市化、现代化不断扩张的历史语境下来客观审视乡土,我们就无法将属于当代人的特定乡土世界如实书写出来。而在我看来,当下还有不少诗人仍沉浸在某种幻象式的乡村膜拜和乡土怀想之中,他们对于乡土田园的赞美诗式的书写只能算作伪乡土诗,其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都是要大打折扣的。我们知道,在不断城市化的历史背景下,许多出自农村的孩子都纷纷离开了故土,来到了大城市、小城市居住、营生,他们对乡土的情感是繁复的、纷乱的、五味杂陈的。因此,诗人要真实地呈现当下的乡土情貌,不是只讲诉它的安谧、祥和、牛羊静美、草木丰茂,还要正视它的破落、衰败、荒芜、今不如昨。这是中国社会不断发展时必然会经历的过程,也是乡土中国向现代化中国转型时可能要遭受的阵痛。(《诗人建构的关系学》)
沙克的怀乡寻根书写则是建立在诗人独立的思考、理性的审视基础之上的,不是一种外在性的情绪式、美化式表达,而是一种深入历史与现实内部的“反刍的诗学”,从而体现出更大的思想意义和文化价值来。具体来说,沙克的诗歌在呈现乡土世界的历史和现实样貌时,往往将其充满多样化和复杂性的特质全方位揭示出来,既写出了那里的温馨、富裕、爱恋、欢乐,也不回避它的苦难、穷愁、遗恨和悲戚,由此书写出来的乡土世界才是立体的、真实的,也才更令人信服和感动。
在《高高的杉树》一诗中,诗人如此写道:“乡村的视野/凸出了杉树,高过/所有树木和房屋的杉树/不枝不蔓地/吞吐阳光,月光和雨水//运木材的马车/跑了马,车上的娘子/贪婪杉树的笔直,修长/这笛声,又一种鸟鸣/在北风的紧吹之下/幸福地颤抖/杉树在独自长高//尖细的叶子和圆圆的/果子,也无缘无故地成长/缝隙间的云和鸟巢/看得清清楚楚//乡村的视野盯着/杉树倒下的样子/不惊不慌地/横在斧子和锯子的旁边/比伐木者的影子长几倍//鸟儿迁往另一棵杉树/巢儿留给了刚成婚的娘子/这一切我看得清清楚楚/这一切教我欲悲无声”,在这首诗中,高大笔直的杉树,妩媚动人的新娘子以及云朵和鸟巢,无疑是令人欣喜的乡村美景,但杉树倒下的惨景和伐木者在乡土世界蠢蠢欲动的身影,却令人焦虑不安,“教我欲悲无声”。这首诗将乡村的美与丑、兴与衰放在一起加以呈现,呈现了乡土世界斑斓复杂的精神图影。
也许应该指出,沙克的故乡理念包括着乡和城的连体时空,诗集《诗意的运河之都》中有许多涉及城市生活景象的作品,并且还列有“城市影像篇”专辑,这正是我在《诗人建构的关系学》一文中述及的“现代化不断扩张的”故乡概念,我以为沙克恰恰是“站在当下城市化、现代化不断扩张的历史语境下来客观审视乡土”的,因此他的运河书写便自然地连通了历史维度和现代空间。沙克对我说过,他这部诗集的重心部分在“精神故土篇”,这里沉淀着他对土地、河流及命运的刻骨体验、深度反思和对精神原乡的终极探寻。除了那首《高高的杉树》,还有《我们家的手》《时间之痛》《小麦和田野互相悲伤》《领行的河流》《我从哪里来》等诗,它们将乡村的痛与爱、欢乐与悲戚放在同一个平台来展示,给人五味杂陈的阅读感受和体验。以《小麦和田野互相悲伤》为例,全诗为:“叫做化学的敌人,混着雪水漫来/带来刺激、割裂和腐蚀/小麦难受得痉挛,直不起腰/伤在根部,痛在心头//田野受难更甚,还被混凝土侵压/被轮子鞋子乱踩,被刮去金屑/被剥掉了植被的衣裳/它的血毒增多,血压增高//小麦把破皮的脚指向下伸/触到田野的内伤/处处是带来污染的过度物质/却找不到被告,无法起诉侵略者//运粮的汽车不断加大载重/小麦和田野屈无辩言/它们多么担心/吃粮的人和动物受到伤害//气候和环境被咬住脖子/瞪着眼,吐着白沫//侵略者来到它们家乡/小麦和田野抱在一起忍住悲伤/咬破嘴唇,险境维生”,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的当下语境,乡土世界正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其现实样态并不完全令人乐观。这首诗通过小麦与田野在现代化侵袭之下所遭遇的窘境的生动述写,将诗人对于乡土世界的复杂情绪形象昭示出来。
可以说,在沙克的怀乡寻根书写中,诗人既呈现了乡土世界温馨甜美的一面,又能客观理性将其失意的乃至阴暗的一面大胆曝光在人们面前,而由此展现的诗人的悲情与痛感,显然来自诗人对这片土地历史与现实状况的深度咀嚼与心灵过滤,因而更具有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沙克由此建构起来的“反刍的诗学”,已然构成了当代诗歌怀乡寻根书写的一道格外亮丽的艺术风景,其所具有的历史与美学的价值都是不可低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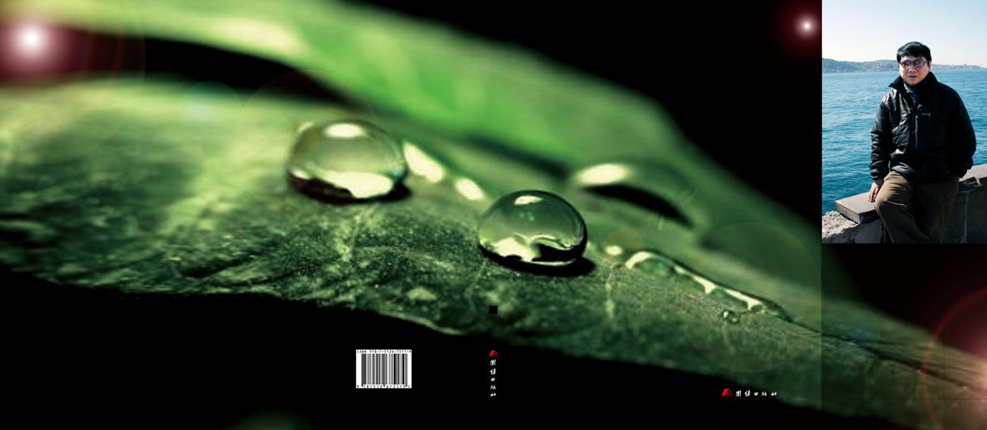
作者简介:张德明,文学博士,岭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南方诗歌研究中心主任,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评审专家,中国作协会员,广东省作协首届签约评论家。已出版《现代性及其不满》《网络诗歌研究》《新世纪诗歌研究》《新诗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等多部学术著作,在国内重要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曾获广东省青年文学奖理论类一等奖、2013年度“诗探索奖”理论奖、《星星》诗刊2014年度批评家奖、第五届“啄木鸟杯”年度优秀论文奖等奖项。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



 纯贵坊酒业
纯贵坊酒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