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宁是谁?以及我与朱力平的通信
作者:金锋
题记:今年十月初,在锦溪的“苏州诗院”,祁国给了我一本朱力平先生的小说-《梅宁的选择》。祁国说,你读下这本书。我回到工作室之后,这本书一直在我的书桌上搁着,似乎我在等待一个阅读的时机。直到最近,我突然拿起了这本书,开始翻读,书没有序言,只有后记。后记很短,是朱力平自己写的,但这“后记”已经死死地吸引我了。我花了三天时间,把这本接近24万字的小说读完了。小说的文字简直太棒了,隽妙、幽默而老辣。冯唐的文字很出色,我觉得朱先生的文字功力在冯唐之上。我开始琢磨着怎样写出我的感受与心得。最后我选择了书信的形式,想与这位未曾谋面的先生做个交流。下面就是我们的通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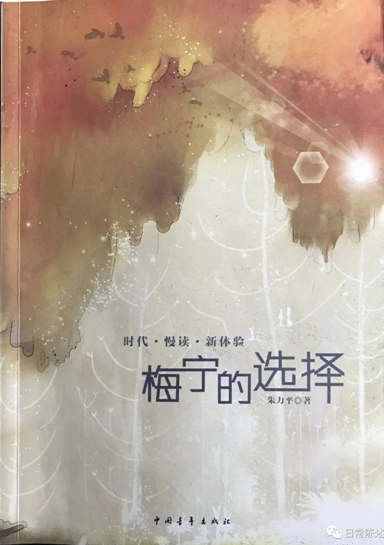
梅宁的选择/朱力平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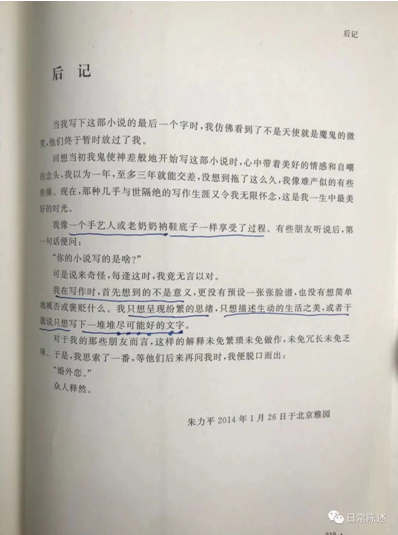
朱力平写的后记
给朱力平的一封信
力平兄:
见字如晤。
我们未曾谋面,就直呼为兄,好像很是唐突,其实非也!我是读了你的《梅宁的选择》之后才这么决定的。《梅宁的选择》是你的诗人朋友祁国给我的,他希望我认真读一下你的书。我是不仅读进去了,而且喜欢得不是一点两点,是爱不释手了,这才有了非常走近你的感觉。我只是在想,怎样把“读后感”告诉你呢?我觉得书信的形式还是大致体面的。我跟许多人写过信,不过都是故人,比如丢勒、庞加莱,比如苏格拉底、希尔伯特,我跟这些人不可能谋面。我觉得,跟未曾谋面之人写信、交流,心里踏实。如此,我也把这种的习性延续到你这里了。
我是先读了你的后记,才静下心来进入了你的文字。你简短的后记,是撩拨我进入你文字的诱饵,你说写这本书,“像一个手艺人或老奶奶衲鞋底子一样享受了过程”,而当别人问你,这本书究竟写了什么?你居然“无言以对”,你“只想描述生动的生活之美,或者干脆说只想写下一堆堆尽可能好的文字”,这种直露心扉的实话,一般读者也许费解,但我很明白。我是作为一个艺术家在读你的作品,我会很细腻地用我的固执搅拌到你的文字里去,或者把你的文字误读到我的偏执里面来。我这样说,表达不同,意思一样,就是在你的小说中要读出我来。你是玩文字的高手,字跟词好像都是有磁性的,相互吸附得那么调皮,那么的不落窠臼。但我看到了你的艰苦卓越与顽强好斗,你是把文字反复打磨得像一件精致的玉器之后,这才放心地让它们问世的。我高兴的是,你的漂亮的文字不是一堆装饰的死肉,它们都恰如其分且非同凡响地坐落在自己该在的位置上,它们都得体、优雅、孤傲地示众着自己。文字,这些字与词,它们曾经都被规定在词典里,大部分的字、词也都未曾谋面,字跟字以及词跟词能成为搭档,并且透露出崭新的含义,这是你码字的智慧与劳作,是你的“使坏”,让词与词的“通奸”获得了全新的合法身份,这是最吸引我的部分。
作为小说,梅宁选择什么,这已经不是最要紧的追究了。一个苦逼的读书人,只有把他安放在一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位置上,他的灵与肉在坐标上的点,才能构成一个可以分析的函数,虽然不够独特,但也不至于无解。我宁肯喜欢你所呈现的梅宁,不造作不装逼,他的美学正好够得上意淫,又恰巧有量子缠绕般的沙沙与娜娜这样的存在,再加上一个只会顾家的傻老婆,这样,故事想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了,即便把故事说到事故的程度也是不难的。但小说的结尾:“快进来吧,二德子!”这个意外结果完全跃出了我的判断,这个构思是来之不易的。我说的“使坏”正是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小动作”,它撑起了整部作品的段位。这个结局,让读者的意识一下子失重了。坠落,或者下沉,二选其一。
我觉得,这个世界,每个男人都分沾着梅宁,每个女人也都分沾着沙沙与娜娜,每个诗人分沾着胡州,每个官员都分沾着高正人,每个老板都分沾着何有情……我们都分沾着这个社会最不想描述部分,没有例外。梅宁的灵与肉是分离的,只有分离了,才有一般或常规地活着的共同体。其实,大家背地里不可告人、不可交流的忙碌都是一样的。这样的共同体,体量极大,但构不成威胁,因为这是一个散装的共同体,在小心思上还是各自为政的。
梅宁最后的选择,我的猜测,是让一部分肉体先死掉,换回一部分灵魂,由此获得心理上的安宁,好像有一种归宿是可以换算的,我想说说这种换算。
小说中,你在几处地方都提出了一个难解的疑问:你们这样活着,钱是从哪里来呢?在诗会上,梅宁问过一位首席诗人:“我是说你的经济来源,你靠什么维持生活?”而首席诗人的回答等于没有回答。我们都是分沾了“首席诗人”这样的生活,试图把精神世界看得很重,而实际上压根儿就没有能力维持这样的生活。维持理想也是需要高额付出的,这就回到了一个基本的问题:选择。我觉得“活着”不是靠换算能够持久下去的,我说的“活着”,是有意义的对独特人生的认定与选择。梅宁到最后有所选择,大致是看到了自己还能做些什么的可能性,但他的选择还不是残酷与终极的。那位首席诗人更不是。选择独特的活法,实际上也同时选择了怎样死去。只有对死亡敬畏,才能从残酷的倒逼来安排自己的“活着”。何有情、沙沙、娜娜、高正人都是不想死的,他们都只是常规的等死之人,只有梅宁隐隐觉得不能将就活着,所以,梅宁要“选择”。
通常,小说的结局,作者为了“一己私利”,是可以让主角死去的,就像《包法利夫人》,福楼拜安排爱玛的自杀一样,好像作者是可以掌握人物的生杀大权的。但你没有让梅宁死去,只是安排了他为时已晚的“选择”,也许你觉得,这种活着是更加煎熬的,是生不如死。当然,我这样解读不一定符合你的意思,我只是读出了我的理解与期望。“你靠什么维持生活?”这个问题不需要回答,其答案已经在“选择”的认定里了。
小说中不经意之处所贯穿着的哲思语言,我也是很喜欢的。我猜测,这些语言也许是自动写作中的自然流露,但我感受到了某种犹疑与停顿,因为这里“有事”,这里需要“转折”或是“拿腔拿调”,这里需要新感性……所以,你码出的所有带有运思的语言,也都是经过打磨的,小说与哲学的混搭,它们串着味儿地一起“诗意”,而这种“诗意”是陌生化的,更是沉重的。比如:“存在不能离开感知,没有不被感知的存在”;比如:“信念就是对不确定的追求”;再比如:“意义不是给出的,知觉本身就是意义,离开生存无意义。”在人物的对话中,在对人物的心理描述中,在人与物之间的距离中,这种哲思语言在其中的穿梭与搅拌,我感受到了一种语义上的厚度。至于你的俏皮的文字,我就不多说了,因为太多了。
你不是观念写作,所以不会在一个批判的框架中对人物预先设置。我猜测,你的兴趣是在小说中写小说,所以,你的人物是在过程中逐渐清晰的。你也许把批判转换成了一种张力,它体现在人物之间心理上。我从自己的创作中,只是在你的小说里看到了一种平面,是一种现代主义意义上的“平面”,你的好奇与兴趣,或者说你的工作重点,是把这个“平面”整理得更干净、更优雅、更高级以及更理性。而这一切,你都做到了。
你通过梅宁之口,实际上是自己要说:我一直推迟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我理解,这个“推迟”,也是对“选择”的不确定,其中包含着“迟到”或是“放弃”。我想,只有沉默难耐,你才成功地流放了你的言说。所以,你觉得天使与魔鬼都暂时放过了你,我理解你说这话的更为深层的含义。
好,我就说上这些。
我喜欢梅宁,喜欢《梅宁的选择》。
金锋
2022年11月23日
于上海名企公馆191号
朱力平:致当代艺术家金锋
金锋兄:
您通过当代著名诗人祁国兄转给我的信收到了,信中言辞恳切,高山流水,直觉老友相逢,喜出望外,感谢您对拙作《梅宁的选择》的厚爱!小说家渴望一个知音,正像果戈里遇见普希金。
您信中说给许多已故大师写过信,我清楚是表示喜欢通信这种形式,不过我很高兴您这次是在和一个活人通信。
《梅宁的选择》的创作虽历经十年,却仍有许多缺陷,尤其是经伟大的艺术阿罗汉祁国先生的斧评,许多问题要到再版修订时解决。
比如您敏锐地注意到的“选择”问题,就颇有值得商榷之处,也许它是现实或哲学中最紧要的问题,却不一定是小说艺术的首要问题,小说的上帝视角决定了人类生活中的一切包括各种哲学思潮都只是小说的素材,小说家不能干预,只能如实呈现。一部《红楼梦》,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是极好的。正如您的来信所说:“作为小说,梅宁选择什么,这已经不是最要紧的追究了。”而《梅宁的选择》引起了您对选择这一存在主义本质核心问题的重大思考,则是对作者的最高奖赏,也是小说获得专业界认可的标志之一。
感谢您在信中提到了我的艺术上帝福楼拜和他不朽的《包法利夫人》,他说“离开文体无作品”,这也是我追求语言和形式的动机。另一方面这也显示出我的笨拙和缺乏灵感,灵感这种事我听说过,却从来没有遇见过,正如福楼拜所说,流畅的诗,艰苦地写。
小说中的“哲思语言”的出现的确是“经过打磨的”,“这里需要新感性”,需要“沉重”和 “厚度”,您作为著名艺术家和评论家,自然逃不出您的眼光。我在小说的第一页对读者实施了语言轰炸,只有过关者才有可能继续读下去。这对读者提出了过高的要求,效果不一定好。小说的归小说,哲学的还是归哲学家的好。
关于观念艺术问题,也被您在信中极为专业的提出:“你不是观念写作,所以不会在一个批判的框架中对人物预先设置。我猜测,你的兴趣是在小说中写小说,所以,你的人物是在过程中逐渐清晰的。”
对极了!我以为,观念艺术是诗歌和绘画的命门,因为这些艺术形式本身就是世界观就是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小说则不同,小说不是说,而是呈现。小说不像散文那样是我手写我心,而是尽量把作者隐藏起来,尽量把作者的真实意图隐藏起来,隐藏得越深越好,甚至正话反说。观念艺术的主题先行对诗歌和绘画的鲜明性是至关重要的,对小说却有可能造成重大伤害,它会造成人物脸谱化和情节简单化,从而有悖社会、生活和人性的复杂化。真正的小说家多么希望把生活中的一切都搬到小说中来,而对这种小说的阐释又是多么的无穷无尽啊!
最后,我要说,您对梅宁一直推迟真正意义上的写作的分析,达到了心理学家的程度。不过需要提醒您的是,梅宁不是我,他是小说中的人物,即便在他身上有作者的痕迹,也不能对号入座把梅宁等同于作者,小说是虚构,作者必须以艺术为第一位。
再次感谢您高屋建瓴热情洋溢的来信!
朱力平
2022年11月24日
于北京雅园
金锋:给朱力平的回信
力平兄如晤:
你的回信经由祁国之手转到了我这里,认真拜读了。我想,现在这封信回函,一切客套的应和都免去了,直奔主题,继续说说我的思考。
来信中,你说出了你对“观念写作”之“观念”的理解。你认为,“观念艺术是诗歌与绘画的命门……观念艺术的主题先行对诗歌和绘画的鲜明性是至关重要,对小说却有可能造成重大伤害,它会造成人物脸谱化和情节简单化,从而有悖社会、生活和人性的复杂性……”你说出了你的担忧以及对“观念”的警惕,这也解释了我在你作品中期待“观念”而不得的原因。也正因为这样,我在信中说:在你的小说里看到了一种平面,是一种现代主义意义上的“平面”……你把“观念”与脸谱化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现代主义思维。但我又觉得你的写作不是“现代”,而是“当代”的,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在你的作品中,我看到了某种“非小说”,它是由多种文本构成的,比如,叙事、哲学与心理学,是它们的汇聚在给我期待。这些我把它暂时叫做文本的“材料”,它们只是“能指”的“原材料”。假如,它们不能被“观念”对接上一个开放而激烈的“所指”,那么,这些“能指”原料还只是在“小说”里丢圈圈,它还是“小说”,而不是“非小说”。我是试图想在你的小说中完整地把“非小说”像套现一样套出来,结果没有实现。所以,我理解了你在后记中说的,你的写作,首先想到的不是意义。
所以,这里,我想跟你交流一下对“观念”的理解。我们的工作领域不同,但对问题的思考应该有许多“交集”的。你担忧的观念,在艺术史中属于现代主义中的“概念艺术”,把握它的关键点,就是能指对接的所指,这个所指还在艺术的内部,属于艺术上的“闭环”,“为艺术而艺术”,就是早期现代主义的“闭环”。而当代的观念一定是走出艺术的,它的“所指”是艺术外部更激烈、更棘手的现场,对于这样的现场,观念是提供“思想力度”的,使得“能指”智慧地对接到社会现场的“所指”中来。所以,“非小说”中一定是用观念来撬动语言的,而且,“非小说”一定不会轻易地让观念成为单一的脸谱化的观念。
在“观念”上,政府的手笔一直是有力度的。比如,疫情中,百姓是能指,健康吗是所指,核酸是观念。从文学或者艺术的角度看,这个观念拉平了什么?它拉平了一切的“在地性”,使得所有城市都是无性格的,形式上都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这就玩出了在病毒中超越病毒的全社会的“新感性”。“非小说”就应该这样吹涨与起肿,在平常中显出异常,你说呢?所以,要谦虚地向政府处理棘手问题的手段学习。这在我这里,也在你那里,或许都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深刻命题。
在小说的地盘,以及我自己工作的地盘,如何像政府那样玩转一切?想清楚这个问题,其实是不容易的。我期待的“观念写作”,是处理生活中更大的麻烦,更大的遭遇,更大的苦难,是把外部包括政治的一切都纳入其中的独特写作。让“能指”千变万化且不择手段地去切割、篡改、搅动与扰乱所有的媒介。这样,小说、哲学、政治、心理学混搭着搅拌,作品才有型,才有更有力。我觉得,只有在观念的冒险中,小说才是大于一切的。观念是理论装置,它拉平了思想创造与语言创造之间的不同,使得语言带着哲学味儿自己在言说,既出卖自己,又有能力获得对自己回收。我想,在这样的境地中,梅宁想要沾点荤腥、趟点浑水,怎么做都是可以的。但是,仅仅把哲学置换成了心理学,它就不可能理直气壮地覆盖政治,人性的东西就回不了家。
我感受到了你对激烈写作的藏捏,藏匿了写作者,甚至藏捏了虚构的密码。假如,激烈的理论与激烈的诗,在不戴套的情形下彼此激越,小说的“所指”,那个独特而激烈的观念,才会给生活本身以有力的打叉。设想一下,一切脸谱化与简单化的形式,在这样的写作中会有存在空间吗?我想是不会有的。
当然,上面这些,也是我个人的一点思考,不一定带有普遍性。我只是喜欢在里面琢磨一些可以起哄的出口,以便撬动我们身上的罗格斯。
好,就写这些,谈的有些跑题。
金锋
2022年11月26日
于上海名企公馆191号
朱力平的回函
金锋兄:
26日来信收悉,正在看世界杯,生命爆发出来的活力令我惊讶。看,我对生活的理解总是很“平面”,实在谈不出多么高深的东西来。
我以为,一个作者谈论自己的小说是不合适的,一个人不可能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既是厨师又是营养学家。创作更多的依赖的是跳动的脉搏,而不是按图索骥的理论概念。一个足球运动员在踢球时不会想到这有什么意义。
可见,评论家的作用是多么的重要,他们的专业眼光能从作品中挖掘生发提炼出无穷生尽的意义。
本来可以就此打住,不过我想再多啰嗦几句。
从新小说派鼻祖福楼拜的没有主题到高行健的没有主义,强调一个小说家声称自己有一套体系是避之唯恐不及的,创新永远在路上。其实,为艺术而艺术又何尝不是一种观念。小说家有时更乐于接受评论家给自己贴上的各种流派的标签。 虽然作品建筑在作者对世界和生命的形而上认知上,然而文学的目的就是文学。小说应该就是语言文字的杂耍,是人类语言文字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准的集中展现。现实只是作家使用的材料,在生活中有好人和坏人,在小说中只有描写得好和不好的人,这是怎样善良的愿望也无法替代的。
好小说就是一堆奇妙的文字。写作的激情来自于此,来自于对文字的喜爱,来自于寻找和创造一些别的字、词和句子的乐趣。“人们不是用思想来写诗的,而是用词语来写的”,“世界被创造出来,只是要达到一本美的书的境界”,(马拉美语)。脱离现实的困厄,梵高是满怀热爱而不是憎恨在创作的。那么,纯文学是脱离现实的象牙之塔吗?
正相反,越是艺术的,才有可能越是本质的,从而越具有批判的道德属性和永恒的价值观念。
朱力平
2022年11月27日
于北京雅园
金锋:致力平
力平兄如晤:
来函收悉。
其实我不是搞批评的,我只是一个艺术家,一个真诚地阅读你小说的读者。也许你会奇怪,一个艺术家怎么会像批评家那样来言说?这也是有原因的。在我自己的创作中,有些问题自己糊弄不过去,才习惯在棘手的难题中做一些追问。继而觉得,一个艺术家,也应该成为自己的批评家,这完全是我个人觉得很是重要的方面。所以,也很自然会把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带到与你的交流中去。
我跟祁国说,我与力平兄的交流,假如能成为一个“文本”,这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文本”其实已经实现了。因为,通过我们完全没有预设的书信交流,我们都执着而严肃地表达了自己,包括态度与立场。
你的这封来函非常重要,许多想了解你作品背后思考的人,在这封信中都能找到答案。这封简短的回信一如你小说的“后记”,我读出了你的坚持与真挚,也读出了你的爱。
我们都爱创新,创新中有着自由。
这里,我非常想邀请你来我的工作室,来看看我的作品,我想,我们一定会有更加深入的交流。为此,我期待着。
金锋
2022年11月28日
于上海名企公馆191号
朱力平的第三封回函
金锋兄:
28日来信收悉。
拙作长篇小说《梅宁的选择》问世八年来,没有受到多少关注,连我自己都淡忘了,我奇怪当初我是怎么魔怔的。小说是供⼈消遣的,互联网时代提供给⼈们的消遣太多了,小说自然很少有人去读了,何况我这本破玩意儿。我想,我的书能够“在某个鲜有人问津的图书馆的某个角落享受上架待遇 ”(奥兹),就不错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艺术的阿罗汉大祁国先生在疫情闭关期间读到了我落满时间灰尘的小说,如获至宝,誉为文学饕餮之徒的珍馐美馔。他不但盛赞之,推广之,还提出很多真知灼见,与我如琢如磨,催促我尽快修改以便再版,搞得像是在抢救什么似的。起先我还有所抵触,实在是懒到不行心志已平了。待我振拔精神重回以往,才发现此书在刀斧一番后,才能画上最完美的句号。
您的来信让我信心倍增,如见曙光,有您这样的读者,实在是作者的莫大幸福。在我们周围大多数人连自由的头脑都不需要,就更别提什么意识流和空灵内在了,能够对这些玩意儿感兴趣的人不会超过十万分之一,这个比例对一个孤僻的自我也是太过庞大了,幸运的话,也许会有十个会心的人,三五个知音,半个伴侣,足矣。
谢谢邀请,有机会一定去欣赏大作。
朱力平
2022年11⽉29日
于北京雅园
来源:金锋 日常陈述 2022-12-01 14:20 发表于上海
作家简介:朱力平,诗人,作家。1955年生于北京,毕业于清华大学。曾任职于某央媒。自闭症自愈者。常年闭门潜心写作,作品较少示人。《梅宁的选择》是作者历时十年完成的长篇小说。
《梅宁的选择》,以当代中国真实生活为背景,充分展示了小人物梅宁丰富的内心世界,并通过对人性的探讨,挖掘和揭示出个体存在的本质,同时以幽默的笔调探讨了时代和命运这两大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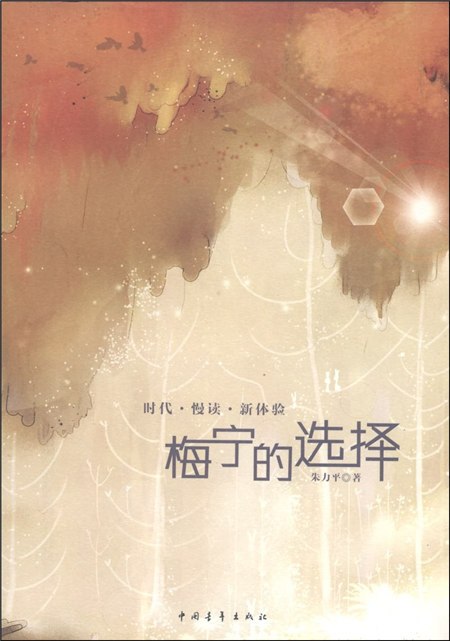
附:资料
书名:《梅宁的选择》
作者:朱力平。
ISBN9787515322032
页数:219页
定价:30元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4月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内容简介:
《梅宁的选择》主人公梅宁是北京的一名普通职员,由于好幻想和沉思的性格,而很难融入乏味的集体生活中,他身上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孤独感和自闭倾向,也使他和物欲横流的社会显得格格不入,在他身上充满了一个有文化的现代人的精神困惑和各种矛盾,以及理想和现实的种种冲突。
目录
卷首诗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卷尾诗
后记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纯贵坊酒业
纯贵坊酒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