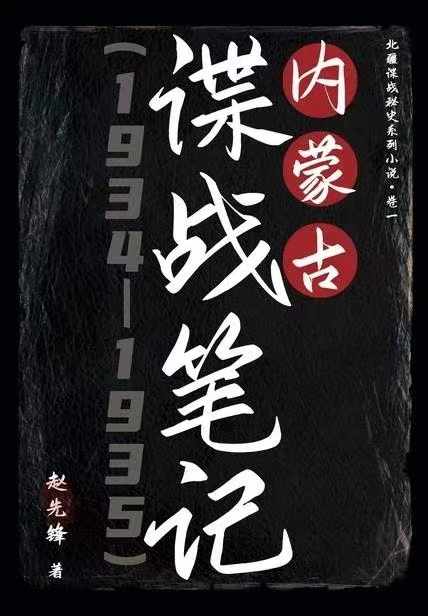
万里北疆图
——赵先锋的《内蒙古谍战笔记》
作者:阎锡四
前些日子,著名作家孙甘露的那本名为《千里江山图》的长篇小说,获了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这个小说写的是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谍战故事——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保护中共一位重要领导人转移出上海,和国民党特务斗智斗勇,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孙先生以前是先锋小说家,可以说以晦涩和异端的表现方式著称,二十年后,他在质、数双量上的侧重点,以及从文本技术上,非常中规中矩了;开句玩笑话,孙先生已不复当年之勇。这两天,我碰巧读到了内蒙古作家赵先锋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写谍战故事的,发生地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北疆(俄境、蒙古和内蒙古一线上),竟然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中国的影院和电视、视频平台上,谍战片(剧)一直保持着不错的票房和收视率,比如谍战片《风声》《悬崖之上》等,比如谍战剧《潜伏》《暗算》《风筝》《悬崖》《黎明之前》《伪装者》等,一位出品过多部谍战剧的影视公司老板说过这样一句话,(大意)谍战题材是永不过时的朝阳产业。这说明,在中国谍战题材是个成熟的文艺类型。
赵先锋的这部长篇小说命名为《内蒙古谍战笔记》,乍一看,走的是“厕所读物”的商业路子,但读过之后,发现若不是囿于题材的限制,作者呈现的其实是个纯文学文本(据说,这是一个网文版本,还有纯文学版本),叙事、语言、修辞、结构、对话等都做得不错,有美国作家科马克•麦卡锡、斯坦贝克和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风格。其实,赵先锋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直以笔名赵卡在从事诗歌、小说和随笔批评写作,现实主义和具有先锋性质的文本在他的笔下并行不悖,但突然杀出个谍战类型而且是独树一帜的公路谍战小说,着实令人吃惊不小。
众所周知,近二十年来的谍战媒体作品几乎集中于那几个城市:北京-如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上海-所有聚焦在极司菲尔路76号的作品;重庆-如电视剧《风筝》;哈尔滨-如电视剧《悬崖》《和平饭店》;天津-如电视剧《潜伏》,等等。诸方狂喜过后,忽视了这里面有个审美疲劳问题,所以至少近三年来乏见还有高收视率的谍战片(剧)。
谍战作品问题的结症,从赵卡的《内蒙古谍战笔记》这部长篇小说就可以得到启示:从谍战类型里再细分类型,即从城市(密室)谍战转向公路谍战。
应当说,“北疆”这个领域对大多数人来说太陌生又太神秘了,无论历史还是地理,但在作者那里,就有了讲故事的巨大弹性,作者也因此强调,“北疆”概念在小说里具有不可取代的独特性。由此,我们可以想到科马克•麦卡锡的墨西哥平原和肖洛霍夫的顿河,在时代生活与个人知识经验上,大师启发了作者的强劲想象力。
作者的“鸡贼”(原谅我不礼貌地用了这个词)主要表现在叙事信息密度极强的故事奇观上,从结构、人物、对话和场景转换上看,作者绝对有改编成影视的意图,一旦将小说变成影视,将来呈现给人们的肯定是视听奇观。也就是说,小说的影视化效果,是作者故意为之。
小说讲了一个秘密转运战略物资的故事,从俄境的恰克堡到中国的延安,曲线行程近万里。故事是双线讲述的,一条走人,一条走物;走物的驼道又分出一明一暗两条来,使得小说的公路性质极具张力,甚至叙述结构也有了某种隐喻的功能——走上歧途。
作者写这本书之前应该是做了大量的功课,但这些功课并没有支配他的写作,也就是说,地方性知识不能以知识的方式和想象力竞争,这是作者的基本认知。由此,我们看到,这本书里的历史、地理地貌和民俗背景,有可能是假的,或者说,被作者篡改了,或被重新杜撰了。“篡改”和“杜撰”,是任何一个抱有雄心的作家的一项基本素养,目的在于迫使读者读的时候信以为真;在罗伯特•麦基那里,体会这些看似合理的东西,则是另一番面目:“一个作家为什么要在虚构事件上对我们进行误导呢?原因有二:强化可信性,强化好奇心。”
这本书的内容糅杂,覆盖面也够大,故事跌宕起伏,好读,但深度上略有欠缺;所以我更愿意认为它的影视改编价值大于原著的出版价值,因为历史、谍战、战争、公路、冒险、寻宝等任一元素类型均可放大,从故事体量和内容跨度方面看,尤其适合电视剧或网络剧。但改编电视剧或网络剧的话,“节奏”的强化是一个重点。比如,以人物带动节奏,尤其是,在内容强化方面最好是削弱主角光环强化周边人物。这个想法是剧集的,即为每一集核心人物不同,在内容创作方面,针对主角及周边人物的功能性和事件作用进行强化,从而单集以事件核心人物作为主角启动故事,其中不排除配角和反角形成单集主角概念。此设定在故事展现方式和剧集概念方面的新颖度可以做出新的高度,并在整体观感上和核心故事的驱动上更为饱满。
扯远了。一句话,这本书的故事有明确的 IP 养成基础及系列影视作品开发价值。
很长时间以来,内蒙古的文学是被边缘化的,由此,有时我们不得不感叹内蒙古作家不被各方重视的命运,一种文学史的自卑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而如何克服自卑又是个问题;是啊,这就是命运。我所知道的赵先锋,以前是写纯文学作品的,在全国各种期刊上发表了五十多篇中短篇小说,也获过重要的的文学奖项,但他在业内的名声竟然来自文学评论,这就有点令人匪夷所思了。这部小说是他的第一部长篇,而且是类型的,看来赵先锋在对自己的写作进行了一次极为重要的也极为艰难的转型,就是具有文学底蕴的类型小说;我还知道的是,他的偶像虽然有肖洛霍夫、托尔斯泰、科马克•麦卡锡、斯坦贝克、马尔克斯等,但也有类型小说大师乔治•马丁和肯•福莱特,这样就可以解释他的转型了。
需要强调的是,赵先锋的《内蒙古谍战笔记》不是历史小说,按图索骥式阅读会让人误入迷宫,曾经有读者跟赵卡探讨他小说里的人名、地名和相关历史上的事件,他都一概答复为他所有的小说全是虚构,甚至明明是真实的人名、地名,他也坚决不承认是真实的,称那纯属巧合。他如此执拗,不接受对号入座式的阅读规则,定是有着不可为外人道的某些隐秘缘由;或许,他希望他的文本还有其他可能的阐释。
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省域行政建制上看,内蒙古的建区(省)史是崭新的(可追溯乌兰夫“单刀赴会”的英雄事迹),内蒙古的文学起步比较晚,所以我前面说过可能内蒙古的作家存在一种文学史的自卑,文学史的自卑其实就是作家的自卑,但这种自卑并不愚钝,毕竟内蒙古以双语(汉语和蒙古语)形式涌现出了那么多的诗人和作家。但若做个简单地描述,我是不忌惮使用集体主义语气这个现象概念的,特征太鲜明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初期内蒙古的文学的确出现过一阵小高潮,后就迅速滑落到了低迷期,直到以赵先锋为代表的若干70后作家在最近十年内的崛起。
基于“北疆”概念的地域写作,是内蒙古一些作家包括本书作者发现的一大法宝,此地面积巨大,环境亦险恶,犹如一幅万里北疆图,而以赵先锋这一类作家,内心里都驻扎着一个尤利西斯,在归返文学的伊萨卡岛途中总能化险为夷。就如眼下这本公路谍战小说《内蒙古谍战笔记》,作者将他的类型观念发展成了一种地域写作美学体系,比方说,在故事叙述的进程中,他会有意彰显某时某地的实物场景,并从中挖掘出奇观性的特征,令人叹为观止。
我听说这部小说两年前在爱奇艺平台下的一个影视小组手里驻留过,不知什么原因(或许是疫情)无果了,最早的IP定位是“中国版的《权力的游戏》”和“抗战版的《长安十二时辰》”——如果是“中国版的《权力的游戏》”,重点强调多线程同时推进、多人物命运轨迹、多地形画风跨越、多情节节奏变换;如果是“抗战版的《长安十二时辰》”,则强调事件与人物同时推进、时间炸弹分秒必争、错综复杂扑朔迷离、多重势力诡诈漫天。我认为两者的开发方向都是不错的。如今,这部小说由杭州沙发娱乐机构重点包装打造“中国公路谍战小说第一书”概念,我相信书会引发阅读狂潮,作者也会被他的读者谈论。
作者简介:阎锡四,来自网络,信息不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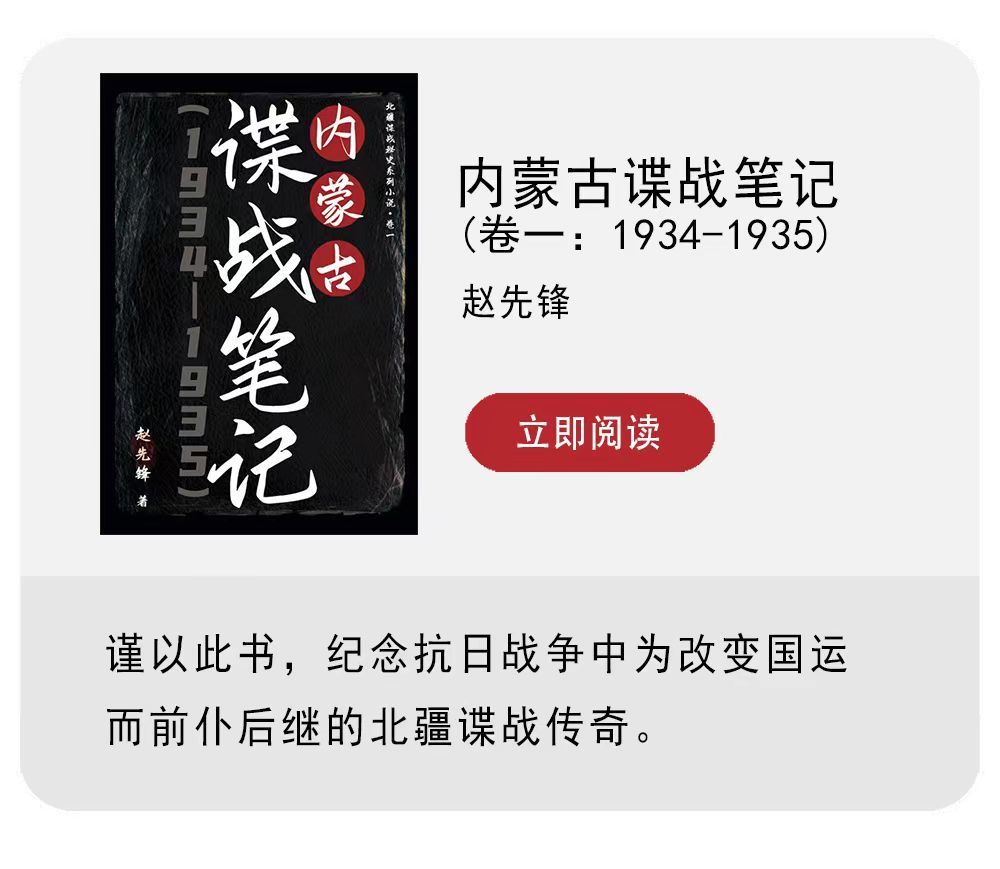
附:
微信读书阅读链接:
微信读书9月联合出品精选书单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m86FIpbZ-JxCiXjl3e605g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纯贵坊酒业
纯贵坊酒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