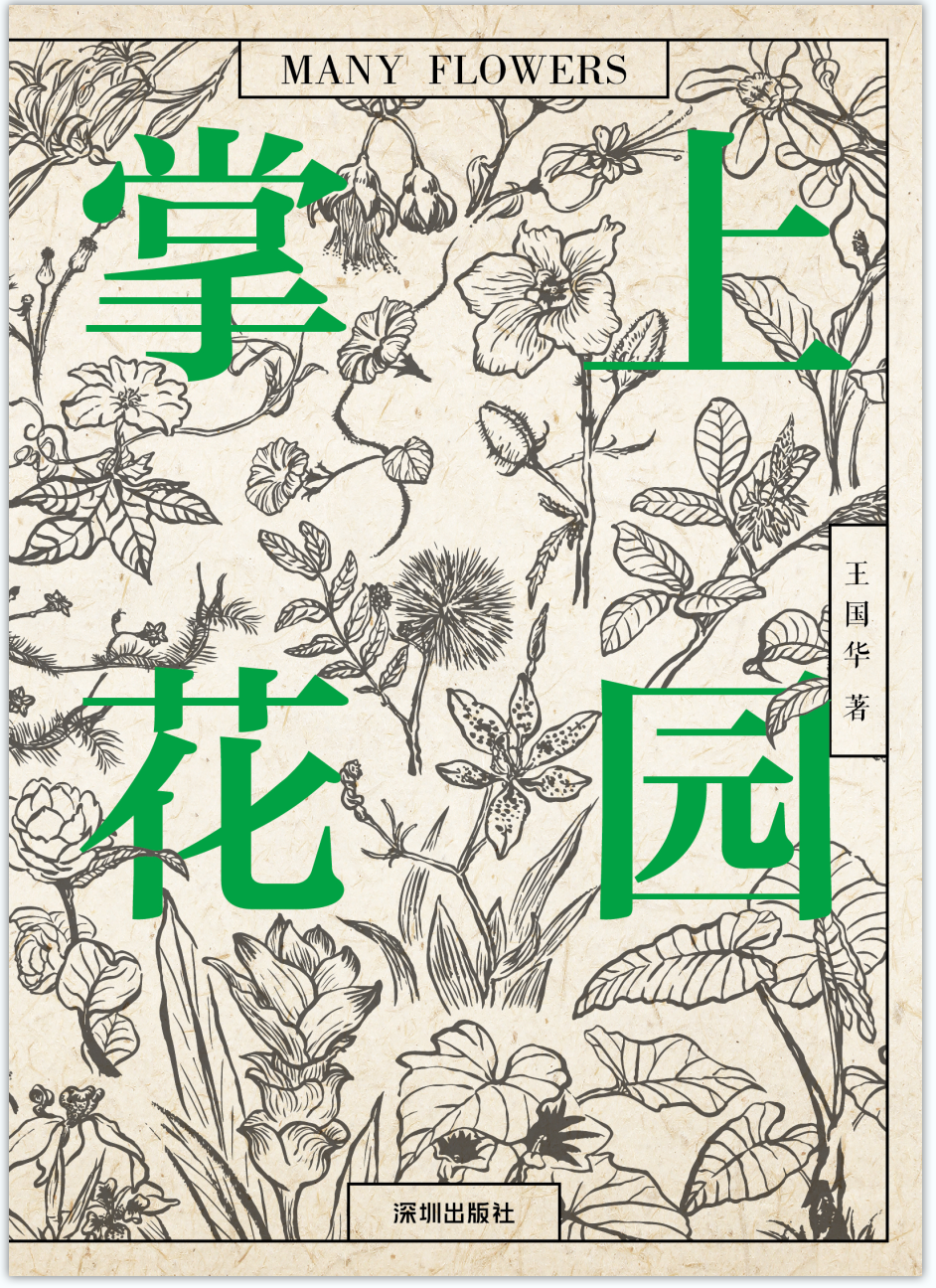
鲜花文字,口角春风
——王国华的《掌上花园》
作者:赵卡
2014年的夏天,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有一个活动,麦家的两本书在英国的企鹅出版社出了,这是稀罕之事,嘉宾席上坐的是莫言和李敬泽,下面则挤满了各位大咖的拥趸。主持人王二若雅问莫言,你对麦家的小说怎么看,莫言当着麦家和大家的面,不假思索地说麦家那种小说他写不了。
这话,说得滴水不漏,简直油滑至极。证实了我对莫言的印象,长得憨厚,其实满脑子主意。换一种情境,等于是比尔·盖茨盛赞乔布斯,既抬高了别人,也没降低自己。扯这个小故事,是我想谈谈王国华的《掌上花园》,首先要声明一点,他这种鲜花般的文字,我写不了。
王国华的散文,在圈内有口皆碑,虽谈不上如史铁生那般煌煌巨笔,却可常见大家影子的端倪。比如《夹竹桃》一文,长不过180个字,又不得于典故,却道尽这有毒之花的鲜为人知之苦楚,“有毒是唯一的自卫方式,也不知前生到底受过多大委屈。”
花草文章,看似简单,于我却是个天堑,就像莫言也有写不了的文字一样,我笔走龙蛇各种酒局还行,哪有王国华那般细腻与耐心。在自序中他不无虔诚地说,“我笔下的这些花,每一种至少要亲眼看见两次。每次对视不少于五分钟。”第一人称视角,过于真实的缘故,又慢条斯理,仿佛孔乙己先生再世,活灵活现地给人卖弄他茴字的四种写法。
这本书没有详细的文章目录次序,意思显而易见,翻到哪页就读哪页,作者不埋伏线也不前后呼应,也就无所谓凤头豹尾或虎头蛇尾了。读者自然省了事也省了心,眼睛可以在纸上东一脚西一脚大行其道,或大快朵颐,端的一个会心之处发出啧啧声。
我感慨内蒙古人是写不了这种文章的,盖因地处万里边境,气候狠戾而无情,一年只有两个季节,西部区的冬天持续干冷,东部区的冬天则常常暴雪崩落,夏天持续干热,雨水总是像财主那么吝啬,我和导演呼可夫甚至决定拍一部名叫《祈雨》的电影。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山地、林地、河地、草原、农田、城镇和现在的沙漠、戈壁里,苟活下来的花草其实过得比囚犯还惨,所以,王国华写得那些花,是无法在我们这块含盐的黄土上落地生根的;哦,温室花棚里可以。
写这么一本书,读者可以想象作者像德布林那样漫步于柏林街头的一种叙事情状,他对花草的自然主义白描观察如摄影机一般写实,如“满树的红啊,远望像是被泼了红漆。”(《刺桐》)“盥洗室里常用的刷子。”(《火炬花》)“地上几只蓝色的耳朵。”(《山牵牛》)“这是一种藤类植物,茎细。小叶,两两对生。五个花瓣,深蓝,互相搂抱着,外三内二,皱皱巴巴,仿佛一只蝴蝶。”(《蝶豆》)等等,但字一落到纸上就他就无法冷静下来,蒙太奇技法拟人化处理,赋予了每种花草超现实生命,写报春花,“大多沉默寡言不愿再做人间俗事。”(《报春花》)写炮仗花,“炮仗花如能点燃该多好。炸他们。”(《炮仗花》)写朱顶红,“朱顶红走得安然、充实,地下有灵,当有所感知。”(《朱顶红》)等等;这种写法,花便不再是花草也不在是草了,一个个原创的类人的形象活生生地被创造了出来,或者干脆,就视为历史上的那些无名人物转世而来的分身吧,虚实相间,反观尘世,醒目之甚,小俗中有大不俗。
要说这本书写得有多好,我怎么说个漂亮话呢?单是一句“我写不了”是无法交代的;最好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北疆的阴山,虽层陵云举,但就不如南方的峰峦峭秀。或者再比方,我们这里满地枯叶风萧索时,就不如南方的一片姹紫嫣红大烂漫。我其实是神奇于王国华对呆物呆名的耐心,一个中年闷骚男人,别人掉书袋他掉眼袋,就那百八十种花名就让人叹为观止了,诸如我闻所未闻的鬼针草、假连翘、龙吐珠、红纸扇、炮仗花、狗牙花、蓝猪耳、十字爵床、金腰箭、鳢肠、通奶草、黑面神……多啦!我不得不叹服他的专注度堪比《昆虫记》的法布尔和《水经注》的郦道元,总之,说让我获益匪浅这种话并不为过。
最后我想说两句题外的话,像《掌上花园》这种写花花草草的书,其实并不中规中矩,因由花草让大家看到了人性和世情,已经冒犯了关于花草的正确知识和正统知识。那么,我觉得我们非常有必要有一类朋友应该像王国华那样,才子书,有趣人,鲜花文字,口角春风。
2024-6-14 呼和浩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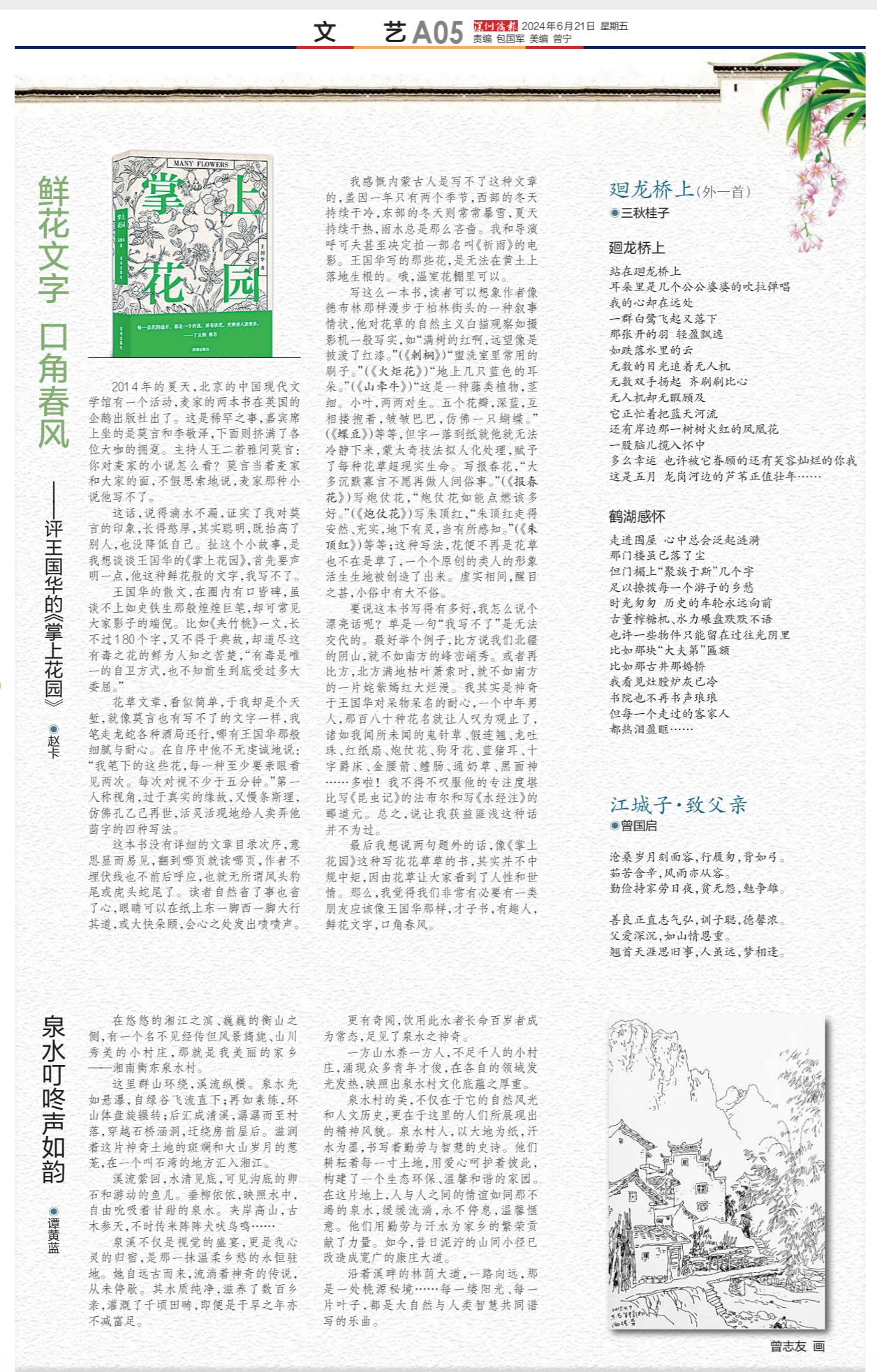
原载于《深圳侨报》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纯贵坊酒业
纯贵坊酒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