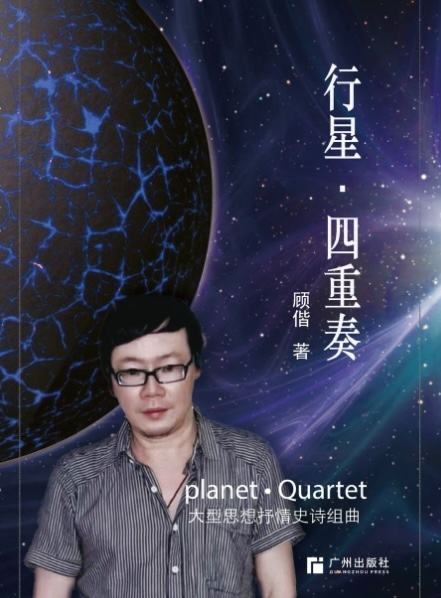
论一种终极美学的张力结构
——顾偕《行星·四重奏》“消逝纪”译作随笔
林元跃
第二乐章竟然在“破碎”中打开的完整觉知与精神超越,正是第一乐章“一种边界的转译不是终点”的残缺处,召唤圆满内涵的“壮丽张力结构”——引领我走向一个更为深邃、更具主体性精神的“完整”之境。可以说顾偕的意象思维兼具哲人的冷隽,他似乎一直就这么固执地引领着人们去追寻真理。正如世纪之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灵光乍现·西川访谈录》关于“在场与真在”的主题时西川说的:诗是哲学的最高境界,诘问终极性对宇宙天地和人性的探索、生命意识的醒觉,以此自觉呈现作品重建诗歌精神的脉律。此话对应顾偕的《行星·四重奏》,今天就像大地升起了一个天启式的鲜活灵气在翔动和飘浮。顾偕看得见“大地只是一个你存在的距离”,是光年每秒30万公里飞行“常春藤在醉意中缠绕(出自广州出版社2024年出版的《行星·四重奏》下同),他的前瞻性,抑或是在穿越平行宇宙时作了哪些超越?他承上启下地作出音乐的姿态,并从“命运舞会”展开的“脚步在缓缓靠近喧嚣的海洋/音乐不愿听苦难的声音/没有一种歌唱再是尝试”,这种着实超越了无数边界的关联,就此使我想起上述访谈录中西川说过的歌诗:“音乐可以表现尖锐冲突与命运激烈对抗,李斯特的辉煌灿烂的燃烧性扭曲”。这种诗坛一直少有触碰的主题,无论规模还是内容,是否确已构成了世界级诗人越性文本写法的那类格局?亦即既用全球化的人类经历,体验各不相同的疯狂与苦难的崩溃,更为当代情绪的现实创作,强烈注入了尤为深邃而通透的诗性思想,如“在虚无中发掘重铸与超越”,无疑这便是该部史诗全篇的哲学基石和总纲。它描述了一种积极的创世行为——不是从丰饶中获取,而是直面“虚无”这一终极背景,并从中“发掘”意义,“重铸”形式,最终实现精神的“超越”。如此像是亦更呼应了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存在主义思想,验证了道家“无中生有”的智慧。
也许最宏阔的宇宙美学诗篇,往往不是给出答案,而是巧妙地划出可知的边界,并指向那更深邃的不可知领域。它保留一种神秘余韵,让敬畏感由此得以续存在预言层面。
顾偕为什么会提出“一种终极美学的张力结构”这个命题?因为在其“思想抒情史诗组曲”第一乐章《我在太阳系》中,解构和重构存在与虚无,一开始便是个极具深度和魅力的主题。它融合了宇宙学、量子力学、诗学、哲学与美学;它探讨的是一种在极致宏大与无限精微之间产生的、令人战栗又心醉神迷的那种超凡审美体验。这种体验的核心,现在于《消逝纪》得到了深化,且由多重对立统一要素,构成了一个充满动感的“张力结构”。譬如这些诗句:“生长无非都是热爱中的匆匆过客/波涛和山峰最懂摧毁的意义”。意象的悖论与恐怖转化的壮美,将终结与起点的宇宙运行根本法则,形成了敬畏的源头感官与通感,并将神圣的超越体验推向了极限,用意象、节奏和哲学思辨构建起了一座语言的圣殿。在“消逝纪”这章乐曲里,自然的终结不过是永恒之书翻卷时抖落的尘埃,无非都是热爱中的匆匆过客,生长与星河共舞的瞬息现象,惟有身心震颤的“共鸣”,努力在用蔚蓝的碎裂雕塑着新的海岸,在创造与泯灭的呼吸间,传授着太古的箴言!当群星如钟锤,撞击时间的薄暮灵魂坠入对光明的敬畏,黑洞万物初生的火焰,坍缩为一粒星尘在引力的咏叹调里,浩瀚地再也无法点燃生命的血液,就此所有逆行的光束,照亮了诗人极端认知的尺度,同时亦以对比的节奏,在一切行将“消逝”空间,营造出了从“仰望”到“融入”的另一种更富视角转变的主体与客体不再对立的终极美学。
“宇宙”与“诗”的张力,秩序与自由的协奏,物理的、数学的引力方程绝对的客观性和极致的主观性,这三者潜在废墟的“破碎与疏离”,仿佛在所有断裂处,均能续写无穷叙事,召唤想象、情感、哲思,并将人生的“碎片”重组为更具深度和韧性的“完整”。终极美学张力的核心关联指涉,实际就是“虚实相生”与“残缺即圆满、破碎即浑全”的建设性想象的意蕴。这个机制强烈暗示了形态曾经的繁华与当下的衰败,巨大的时空张力,还会迫使人思考世界兴衰、诸如存在与虚无、永恒与瞬间等终极命题。“永恒圆满”幻象的打破,“废墟迟早是每个人的故乡”,等等精神迸发出的最具极致的热爱与勇气,它使诗人叙写了一个灵魂终极与永恒达观问题的完整性哲学循环:“我们一生都在学习逝者的东西/消失一直在回味历史”。既然点明了历史的传承性与生命的延续性,在虚无中发掘与重铸,在“灵魂归宿与终极永恒”中展现全诗的核心矛盾,就此便不难揭示出人类精神的两个永恒面向。一个不断追求超越与未来(灵魂散步),一个执着于回归与出发,着力营造文化美学“虚实相生”与“残缺即圆满”的意境。
让我产生玄想的张力结构是否就是律动轮回?如同宇宙本身不断膨胀与律动的过程,其实便是宇宙处于守恒状态的一个独立空间,无论辉煌还是幻灭,物质总量不变,但是空间还是明显变小了,甚至形成奇点的时候,空间可以说是进入到了无穷小。既然宇宙是一个独立空间,能量守恒的质量与空间可以彼此进行转化,那么在虚无中重建神圣,穿越废墟,“存在很长时间会突然永不再见。”诚如顾偕早在1998年出版的英汉双语诗集《太极》“神在检阅人类的精神”时写的“今夜是永生的开始……所有报废的时光/已被进步的代价修复”,当这种本源性言说进入“自然终结”状态,意味着语言符号系统客观真理主观内化的悲壮,可能真的就能凭借辉煌的张力,完成理性与感性的极致。在几种力量被撕扯的瞬间,湮灭性与疏离感生成出的神圣与敬畏,以及由创造与消逝的不断拓展的张力,所指向的更为深邃的不可知领域,恰好以宏大法则抽象与具象的两极贯通,拥有了一种终极的深度:“一一场膨胀之旅后,其实/我已同星河交汇/时空再怎么翻滚,从此我已/不在乎任何永无尽头的起始”。更高层次动态的平衡战栗,永远是宁静”或“狂喜的安详”的,它直白地揭示了世界的无常性、有限性、以及解脱性。而思考和追求形而上的“无限”与“本质”,自是关乎到宇宙的动态平衡,亦是一种直觉体验与理性追求作品的终点。它几乎能使所有人仰望星空时,不再有那种突如其来的战栗,由于认知路径上最为深刻的张力展开的神圣景象,世界的循环消逝,尤让我们深感当下的弥足珍贵。
于此我再作一个惊奇地比较:在这之后顾偕刊载于《欧洲诗人》杂志2025年域外头条的《不朽者你叫什么名》:“你已开始成了我/ 前所未闻的必寻之物/成了我⾄关重要需要理解的宁静/你废弃了时间和所有⽕⼭的敌意……关于腐朽的破解/钻⽯的⼼脏可能都是由真理换来的”。这首诗所表达的对人类命运终极关怀所追寻的另一种眼光,更是在宏大的视角下,仿佛让我们能于一种循环的引力逆转中凝视星空,反观自身存在的奥秘,一如《我在太阳系》所述:“事物的终点全将由认识拆开”的情景,宇宙不是戛然而止的句号,而更像一座富矿、一首由无数循环乐章组成的交响诗,那里甚至有可能还安放着有无数灵魂充盈的生命境界。
因此,在精神上“完整”地对生命本质的洞见,在“消逝”断裂处续写无穷叙事的重构,并在特定时空超越性地承载所有人的理想,使之作品内涵得以无限地延伸,或许这便是“道”的运行与“永恒回归”的法则,体现在“梵我如一”上的真理。从被动接受转为主动建构,用毁灭张力甚至包括可知与不可知的张力,即不断拓展理解的边界指向那更深邃的不可知领域,也许这就是悲壮的辉煌,共鸣在生命质感中的升华。灵魂穿透现象的迷雾,情感于一种深度上感怀,应当这也是对存在本质莫大的一种领悟。
所谓神圣而崇高的主体性超越,顿悟崇高美这一瞬间的照亮,它无疑混合了敬畏、狂喜与平静,是有限个体触及无限时的心灵震颤,是康德所言“数量的崇高”与“力量的崇高”在精神领域的体现。“人类如少女”,“你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你”。静默的来临,宇宙已说完了它所能说的一切。生命必然短暂,困境亦始终充满了突破。这是“在场”(Anwesen) 在现象学中,通常所指事物通过意识直接呈现自身的状态。突破新的在场方式诞生,不是通过“说”而在场,而是在“不说”中更纯粹地显现夜空中的星群。它们的在场不依赖任何描述,它们在其静默的闪烁中自明宇宙规律,哪怕是不断地“消逝”。海德格尔那里的本真存在临界体验是:“生长无非都是热爱中的匆匆过客”。所以守护“无言之真”,即从言说到倾听存在无声的言说,更当成为诗人存在思想显现的通道。里尔克说过:“我们只是在经过万物,如一阵空气的交换/一旦离去,我们便成了那无垠。”
“彩虹没有伸出最终的精美/无限之路,其实/就在过去的岸边”。这些诗句重建了诗歌精神,表达了瞬间与永恒、亲密与疏离、生长与消亡,可以用存在主义哲学解读,但需避免术语堆砌,需要聚焦在诗歌本身的情感张力上。时间是个没有血统延续的幻觉,“一千年的事情都可在舞池发生/如今湛蓝的潮水/全是你无法想象的美酒/音乐不愿听苦难的声音”。最终,人类都将在宇宙的交响曲中,找到自身位置后与自然重新浑融一体。“人类命运其实是个滑稽的影子”,重建深度体验,保持本体开放,可以在“光明的界限其实都是/一些世纪荆棘/波澜总在孕育阴影”,但绝不可让任何既定概念封闭在奥秘浅薄表达的盛行处,诗歌守护当有不可言说之物的重量。
我之所以乐于沉浸式的解读《行星·四重奏》,就因为一种终极美学的张力,它不断延展的结构如同乐章,已用一种广阔视角创意性的启迪,丰富了我在翻译这部作品过程中的理论突围或建设!并将保持诗论“在场”(Anwesen)与“真在”(Eigentliche Existenz)的原则,定然将会开拓出更多文化本质创新的路径。“消逝纪”以"哲学循环"为隐性结构,将生命历程重构了作为宇宙能量的暂时聚集与释放过程,这是一种生命历程在时空扭曲中,感知碎片化存在的现代性焦虑的"存在危机"。当个体意识放弃对"自我"边界的执着时,有限的生命感知惟有融入无限的宇宙意识,所有现实或许就机会,展望到那些不光只有诗中才有的永恒循环的超越性意义。
2025.10.31于四川自贡

作者简介:林元跃,笔名岭南,四川轻化工大学主任编辑,文化学者,诗人。著有诗集《意象神雕》、《大学精神的培育创新》,多篇小说、音乐、文旅、茶文化等诗文作品获奖,并获首届1573金沙诗文二等奖、上海“傅雷杯”全国文艺评论奖、深圳大湾区诗歌奖、四川疫情防控诗歌一等奖。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纯贵坊酒业
纯贵坊酒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