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谁有病
作者:贠靖
丁四元半夜里被蚊子叮醒,穿条大短裤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着打蚊子。媳妇儿夏丽花面朝墙壁搂着五岁的儿子睡得正酣,毛巾被蹬到了地板上,露出两条雪白的细长腿。
丁四元用手在空中扑打着,突然听到客厅里有隐隐约约的响动声。他惊岀了一身冷汗,停下手来侧耳倾听,又没了声音。
过一会,又有声音从客厅那边传了过来,好像是椅子被撞了一下,又像是桌上的花瓶什么的被撞倒了,发出噼哩哐啷的声音。他的汗毛一下竖了起来,惊恐地朝后退缩着,伸出手去捅了捅媳妇儿。夏丽花将脸贴在儿子后脑上轻声地呓语着,翻个身又沉沉地睡去。
丁四元猫着腰伸出手去,抓起床头上的枕头举在手里,脚却像生了根,站在那挪不动。他将半个身子探出卧室,壮着胆子颤悠悠喂了一声。
客厅里一点回音都没有,媳妇儿在床上发岀细微的鼾声。
谁?丁四元开了灯,举着枕头一惊一乍地低头寻找着,客厅里什么也没有。夏丽花嗔怪道:大半夜的不睡觉,你发什么神经啊?
嘘——有人进来了!他一边说一边朝桌子下面瞅着。媳妇儿打着哈欠拧过脸去看了一眼窗户,窗户关得严严实实的。
哪有什么人进来呀,快睡吧,明天还要上班呢!媳妇儿坐起来抻个懒腰又一头栽倒在床上。
丁四元还站在客厅里一脸疑惑地嘀咕着:真是活见鬼了,门窗关得好好的,不会是院子里的野猫白天闯了进来吧,就躲在什么地方?他过去推上窗户玻璃,拧上锁扣,又左右推了推,然后弯腰在桌子底下仔细地寻找着。
早上起来,丁四元从桌上拿起一块面包,拉着儿子的手准备出门。媳妇儿夏丽花在卫生间里刷牙,一嘴的白沬子,偏着脸问:哎,昨晚你不睡觉,在客厅里找寻啥呢?
没有啊!丁四元眨着眼说,他低头看了看儿子,儿子一脸的茫然。
丁四元在单位一直干审计。上了班,他又从财务室抱来一大堆凭证,一整天都埋头在凭证里一遍遍地翻找着,似乎想要从中找出什么蛛丝马迹来,结果什么也没找到。单位里的人都说他心态出了问题,老是疑神疑鬼的,觉得账有问题。但又没人敢阻止他查账,那是他的职责所在。
吃午饭的时候夏丽花打来电话说,我下了班要和同事去一趟四方城里,前些天在东大街的百货商场相中一条涤丝裙子,想再去看看。她说,好好的一个东大街修地铁给挖得稀巴烂!又叮嘱丁四元,你接上儿子就带他在外边吃东西点吧。别老带他吃快餐,那些不健康的食品吃多了对孩子身体不好。他说,这我还不知道呀,你不用叮嘱,偶尔吃一两次没事的。什么就偶尔吃一两次没事的?她厉声道:不许带孩子乱吃东西!他只好地点头称诺。
夏丽花在研究所干会计,她和丁四元是财经学院一个班的同学。那时的夏丽花没现在这么瘦,脸上屁股上都肉嘟嘟的。
在谈恋爱这件事情上夏丽花比丁四元要主动一些。她老说他是个呆瓜、提线木偶,除了算账查账来劲,连谈恋爱都没劲,打不起精神来。一次他们去学校旁边的影院看电影,黑暗中夏丽花在丁四元的脸上亲了一口,他吓得低了头,半晌不敢抬起来。夏丽花逗得仰面大笑,池子里的人都扭过脸看着她,她这才止了笑,拽了拽丁四元,将头枕在他肩上。
多少年后,夏丽花仍清楚地记得,新婚之夜,竟然是她把丁四元拿下的,现在想起来她还有些脸红心跳。
那晚闹洞房的人都走后,她插上门坐在床沿上,闭上眼,想像着他会迫不及待地过来挨着她,轻轻地拥抱她,然后……可等了半天,却没见动静。她忍不住窥了一眼,他似乎比她还沉得住气,坐在那一下一下绞着手指。她又窥了他一眼,说,我肩膀酸,你过来给我揉一揉,他这才往她跟前挪了挪。最终还是她放下矜持,捶了他一下,小声骂了一句呆瓜,将脸贴在他怀里,伸手解开了他的扣子。
有一次,夏丽花和几个闺蜜聚会,喝了点红酒,脸红扑扑的,眯着眼说,这辈子嫁给丁四元这样的男人,虽然不指望他能给她一个浪漫的拥抱和亲吻,但却让她一百个放心,她从来不用担心他会做岀对不起她的事情来。有一个低了头一直不说话,挨着夏丽花坐了,怀里抱着一个十几万的包包,看上去小鸟依人的闺蜜听了半晌没言语。过了一会,她将包包丢到一边,捂着脸,抽抽嗒嗒哭了起来,夏丽花劝了半天也没劝住。
当然,夏丽花和丁四元的夫妻生活也是有缺憾的。在那件事上,多数时候都是她主动。但怀上儿子后,慢慢地她也就没了多少激情和兴致。
吃晚饭时丁四元和往常一样,没看出什么异样。他坐在餐桌前一口气吃了三个煎饼卷土豆丝,一个劲地说好吃。剩下一个,他看了看儿子,儿子摇摇头说不吃了。他又看了看媳妇儿夏丽花,夏丽花也摇摇头说,老公——人家减肥,不能再吃了,再吃要长肉肉的!他就抓起来瞅了瞅,一口塞进嘴里,脸噎得像个红冠公鸡,脖子一抻一抻的,嗓子眼里发出丝丝的咕噜声。夏丽花忙端起水杯递给他,他喝了一口,打了个嗝,这才缓过气来。
凌晨两三点的时候,夏丽花迷迷糊糊睁开眼,发现客厅灯亮着,丁四元不在床上。夏丽花嘴里自言自语着,下床趿拉上拖鞋,探头探脑地迈岀卧室。丁四元光膀子穿条短裤,低头在客厅里寻找着什么,说是有人进来了,就躲在屋里什么地方。夏丽花听了嘴角抽了抽,有些毛骨悚然。
一连折腾了几个晚上,夏丽花就觉得丁四元有些不正常。她说,你请个假,一会把儿子送到幼儿园咱去医院瞧瞧吧。丁四元说,我没病,我才不去医院哩,上午去单位还要接着查账呢。
巷子里的风不紧不慢地刮着。丁四元蹑手蹑脚地往前走着,噏噏鼻子说,谁家的铁锅烧干了,有一股子难闻的焦糊味。夏丽花闻了闻说没有啊,他把丁四元硬塞进车里,一踩油门拉到了医院。
往常没病的话夏丽花是不会进医院的,因为她一闻到福尔马林的刺鼻味儿就忍不住捂着嘴想吐,一看到白大褂就晕。
大夫听夏丽花皱着眉头描述后,示意丁四元在他面前的凳子上坐下。他问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让丁四元看着他,用拇指和食指翻开他的眼皮,拿电筒照着瞅了瞅说,没什么大碍。说着站起来擦擦手,走进里边的检查室。夏丽花忙跟了进去。大夫将食指压在上下唇间,嘘了一声,小声道:轻度抑郁症!夏丽花问,您要不要再给做做检查,大夫说不用,这种病我见多了,一眼就能瞧出来。夏丽花说,好好的咋能得上这种病呢?大夫问:他是不是老疑神疑鬼的,还有情绪低落,干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来,包括那方面?夏丽花听了脸刷一下就红了,难为情地低了头。大夫说,这就对了嘛。又问:他平时有没有受过什么刺激?夏丽花还是摇头。结婚这么多年,他们连一句嘴也没拌过。
那可就不好说了,也许是工作压力大吧,又装在心里不愿和别人说。大夫说,这种病人很可怜,其实他心里是很孤独的,没有人能够理解他。这样,我先给开点药吧,回去调理调理,过段时间再来复查一下。对了,要多关心他,千万不能让他再受任何刺激。不然,病情只会加重。夏丽花又试探着小声问了一句:大夫,你说这种病严重的话会怎么样?跳楼!大夫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夏丽花吓岀了一身冷汗。如果她没记错的话,她姥爷就是得了啥“夜游症”,症状一模一样,大半夜不睡觉,起来光着屁股在院子里乱跑,结果一不留神从一口枯井口栽了下去,不知这两种病是不是一回事。
从医院回来,夏丽花便得了失眠症。整宿整宿睡不着。她一闭上眼,就感觉像走在一条漆黑的长得没有尽头的巷道里。丁四元不声不响地跟在她身后,她能听得到他喘息的声音,却看不清他的样貌。
一会她又听到轰隆轰隆火车穿过漫长的黑洞的声音,她和躺在身边的丁四元就像两列相向而行的列车,只是眨眼的工夫她和他就擦肩而过,渐行渐远,直至互相看不清对方。
一会她又像坐在易俗社的戏楼里看戏,偌大的台下就她一个人。台上一男一女在唱秦腔折子戏,唱来唱去就一句台词:戏开了,落幕了,各回各家睡觉了!让她感到奇怪的是,台上的人就是她和丁四元。她有点弄不清楚,台上台下,哪一个夏丽花才是真实的自己。
天快亮的时候,夏丽花又做了个噩梦,这回她梦见丁四元一丝不挂从楼上一跃而下,悄无声无息地在空中飘着飘着,像一张皮影一样坠落下去,一动不动地扒在地上的草丛里。她蓦地坐起来,喘着粗气,见丁四元卷曲着身子侧卧在床榻上,她揪着头发咦了一声又重重地躺下了。
奇怪,丁四元最近一直睡得很好,他弯着腰,背对背躺在她旁边,像个听话的孩子一样。她突然觉得躺在身边的这个男人很陌生,像从来就不认识一样。她已不记得他们有多长时间没有肌肤之亲了。
夏丽花怀疑自己得了焦虑症,夜里一有半点风吹草动,就吓得坐起来,战战兢兢地没了一丝睡意。在研究所上班她也心不在焉,做账老是岀错,已被领导叫去批评了好几回。
后来夏丽花慢慢地恢复了平静,却发现丁四元又有些不正常了。他半夜里从床上跳起来,惶恐万状地在客厅里跑来跑去,说是有人要加害他,还大声地嚷嚷着要打电话报警。经他这一通叫喊,楼上楼下的住户就都被噪醒了,他们揉着惺忪的睡眼挤在楼道里敲着门问咋会事,大半夜的嘈嘈嚷嚷还让不让人睡了。夏丽花在门里说着道歉话,死死地抱住丁四元,捂上他的嘴,说是闹着玩呢。她想不明白,自己当初怎么就稀里糊涂嫁给了这么一个男人。
单位的人还是知道了丁四元患抑郁症的事,他上班后埋头在屋子里一遍遍查看账本的时候,办公室的人就在外边嘀嘀咕咕地小声议论着。丁四元在里边呆烦闷了,便岀来走到窗户那里,推开玻璃窗扇,将半个身子探出去透着气。办公室的人吓得赶紧打电话把保安喊了上来。几个人哈着腰悄没声地合围过去,将丁四元拦腰抱住,拖拽进屋子里,反锁上屋门。丁四元突然受到惊吓,在里边手舞足蹈大喊大叫。
夏丽花肩上挎只包惊慌失措地赶过来,耳朵贴在门板上听了半晌,里边竟一丁点动静都没有,她心里便有些慌张,让人打开门,丁四元伏在桌子上,头埋进一堆半人高的账本里,嘴里嘟嘟囔囔翻看着账本。见夏丽花进来,他眨着眼问:你咋来了?
夏丽花白天受了惊吓,晚上心慌得不行。
她搂着儿子,就像躺在空无一人的荒野里,一会浑身冰冷,一会又热得不行,像泡在水里,不停地岀汗,浑身上下湿漉漉的,像刚从水里捞岀来。
渐渐地她有些眼皮发沉,朦朦胧胧中刚闭上眼,丁四元倏然大喊大叫着坐起来将她一脚踹到床下。他从床上蹦下来,在客厅里挥舞着手臂,边跑边喊:站住,好一对狗男女,瞧你往哪里跑?看老子不打死你!
夏丽花站在卧室里,静静地看着他,问他在干嘛呢,丁四元说他在抓流氓。他怪模怪样地盯着夏丽花问,你咋会和那个人在一起?刚才我看到你一丝不挂躺在床上,他就爬在你的身上,在和你干那事!
你胡吣啥呢!夏丽花站在那胸脯一起一伏,脸蛋儿红红的。
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她搞不明白,丁四元咋会做这样的梦?难道是他察觉到了她和那个人的隐情,故意装疯卖傻,想看看她的反应?更叫她意外的是,他竟把她和那个人说成是一对狗男女,并且破天荒用了“老子”这个词语。要知道,他平日在她面前总是战战兢兢唯唯诺诺的,还从来没这么大声和她嚷嚷过。
夏丽花已被丁四元折腾得神经衰弱了。那天她在办公室里低头核对凭证,听到有人走动的声音,一抬头看到不知谁在她面前的桌上放了一束黄玫瑰,就是她喜欢的那种带着淡绿色的玫瑰,插在瓶子里,上头闪烁着晶莹的露珠。她闭上眼嗅了嗅,一股淡淡的清香立刻扑进鼻孔里。她睁开眼小心翼翼地伸手去触摸,摸到的却是一只冰冷的保温壶。那壶也是绿色的。本来她是要去开水房打水的,不知谁打了个岔,说要查一下上个月的账目,有一笔数字对不上。结果她放下壶,就把打开水的事给忘了。
为人莫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她抬手拍了拍额头,有点搞不清楚她和那个人之间的事情到底是梦还是真实的存在。有时觉得真实得连对方急促的呼吸都能够感觉得到,有时又觉得是那么的遥远,或者说虚无缥缈,压根就没发生过。
夏丽花镇静了一下,沉着脸道,你要再敢胡吣我就和儿子搬出去住!她说话的语气明显有些底气不足。但这句话还是起了作用,丁四元听后便垂了头,乖乖地到床上去躺下。很快,他又发岀沉沉的鼾声。夏丽花却没一点睡意。
城里的夜晚不似乡村那般寂静,偶尔有一辆两辆货车踩着刹车从什字路口开过去,发出刺耳的尖叫声。
那个人也是夏丽花大学的同学,在校时交往似乎不多,毕业后他就出国了。据说在国外和一个金发碧眼的洋妞如胶似漆地好过一阵子。半年前他突然回来,不知从哪打听到夏丽花的联系方式,打电话说想请老同学聚一聚,希望她能够赏光。本来夏丽花是不想去的,但他都那样说了,她就有点不好意思拒绝。思来想去,她竟鬼使神差地答应了他。到了那里才发现他就请了她一个人。
他还跟以前一样,一副风流倜傥的样子,穿一身白色的西装,系一条红色领带。就是看上去很有质感,价格不菲的那种。见了面他微笑着张开手臂,上前轻轻地和她拥抱了一下。这正是她内心里一直渴望的那种浪漫的感觉,她居然没有任何抗拒就欣然接受了。
那天他们俩人喝了一瓶法国波尔多红酒,到后来俩人都有些站立不稳,说话舌头僵硬,前言不搭后语。
但他们还是有一句没一句地聊了很多,还聊到了《红楼梦》。他说她很像《红楼梦》里的薛宝钗,容貌丰美,举止娴雅,又博学多才,正是他喜欢的那种类型。她心里明明知道他是没话找话,在想着法子讨好她。但她还是感到很受用。尽管她有点不喜欢薛宝钗。她喜欢的是林黛玉,喜欢那种弱不经风的,被人宠爱的感觉。
或许是借着酒劲,他醉眼迷离地瞅着她,有些动情道:你知道吗丽花,我一直喜欢你的……说着紧紧地抓住她的手。她紧张地将手抽了回来,抬手拢了拢零乱的鬓发,神色慌张道,那,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上大学那会,他的确追过她,但被她拒绝了。虽然她是个骨子里渴望浪漫的人,但却觉得她和他不是一路人。他就是一个多情的公子哥儿,给不了她想要的安全感,不是那个她要托付终身的人。
他隔着餐桌目光灼灼地瞅着她,瞅着瞅着眼里就有了些许冲动,过来挨着她坐了,伸出手轻轻地搂住她。她挣扎了一下。他身上的那股男性荷尔蒙气息让她浑身不由自主地颤栗,她感到身子有些发软。
记得后来他拉着她的手踉踉跄跄跑下楼梯,在昏暗的地库里,他拉开车门,疾风骤雨般裹携着她上了车。在酒精的作用下,他们疯狂地拥吻着。
一番激情过后,她拎上不整的衣衫,拉开车门,想要下去,但浑身无力,腿脚软绵绵地迈不开步子。他轻轻一拽,她就倒在了车座上。他俯过身去,给她系上安全带,轻轻地在她的面颊上吻了一下说:我送你回去吧,亲爱的,太晚了。她没再挣扎。
到小区门口看着她下了车,他摇下车窗玻璃,抬手冲她送了一个飞吻,才一打方向开走了。她突然觉得很恶心,觉得自己很龌龊,胃里顿时翻江倒海,蹲在地上哇哇地呕吐起来。
她曾经想要删掉他的号码,从此不再跟这个人有任何瓜葛。但拿起手机犹豫良久又放下了。此后他们又有过几次激情的幽会。虽然她一再在心里发誓这是最后一次了,但又抗拒不了他那令人神魂颠倒的诱惑。她觉得自己很下流,很可耻。
她至今仍不知道他和那个洋女人有没有结过婚,在国外有没有妻儿。他没说过,她也没问。她觉得那个黄头发蓝眼睛,人高马大的女人和她没半点关系。
她和他充其量就是一时冲动,她并没想过要和他在一起。
除了男女间的那点事,让她对他产生几分好感,甚至依赖的是,他很懂得女人的心,会讨女人的欢喜。比如时不时地嘘寒问暖,送一些化妆品什么的给她,还有一只很贵的包包,正是她喜欢的款式。她一直想买,但犹豫很长时间还是没舍得买。
有一阵子,她为儿子小升初的事儿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得知后抚着她的手说:丽,你放心,这事交给我来办吧。他说话的时候含情脉脉地注视着她,眼里充满了令人无法抗拒的柔情。这让她苍白的内心感到无比的温暖和踏实!更让她感动的是,他为此托了不少的关系,还花了二十多万,提前给儿子争取到了一个市级重点中学的名额。
令夏丽花感到十分纠结和懊恼的是,小升初统考成绩岀来,平时看似学习不用功成绩一般般的儿子竟然超常发挥,自己考上了那所市里排名前三的重点中学。
月光水一祥从窗外泼洒进来。窗户半开着,卧室里没一丝风。夏丽花觉得周身湿冷,就像躺在冰窖里,手脚冰凉。她渴望丁四元能从后面轻轻地拥着她,他却睡得很死。
她怀疑他一定是察觉到了什么。否则,他为什么会说自己做了那样的梦?
夏丽花的心情很复杂,她低头看了一眼在怀里熟睡的儿子,决心和那个人做个了断,不再见面。
现在丁四元每天晚上都睡得很踏实,夏丽花却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她老是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梦,梦见她一个人在小时住的巷子里低头往前走,走得很快,面前的路很长很长没有尽头。一会又像走在没有人烟的荒漠上,口渴得厉害。
她还梦见自己站在大学图书馆前的梧桐树下,手里拿着一本钱钟书的《围城》。头顶上巴掌大的梧桐树叶下雨般轻飘飘无声地掉落下来,落到地上就变成无数雨点溅起来。她淡漠的目光穿过飞舞的梧桐叶,漫无目的地在空中游荡着,找寻着,却看不到丁四元的身影。
冥冥之中那个人好像远远地跟在她身后,穿一身白色西装,系着鲜艳的红领带,任她怎么奔跑也甩不掉他。
后来她又梦见曾是工程师的姥爷不说话,光着身子在院子里跑,头顶上有无数只红嘴乌鸦在飞来飞去,最后风卷残云一样掠过楼顶飞走了。
夏丽花陷入了痛苦的旋涡之中。
她怀疑丁四元没病,是装的,倒是她自己有可能患上了抑郁症。
如果他没病,那可就太可怕了,她想一想就有些脊椎发凉,头皮发麻。
有时她又想,或许她和那个人之间的那些事根本就不存在,只不过是一些零零星星破碎的梦而已。这样一想,她心里便有些释然。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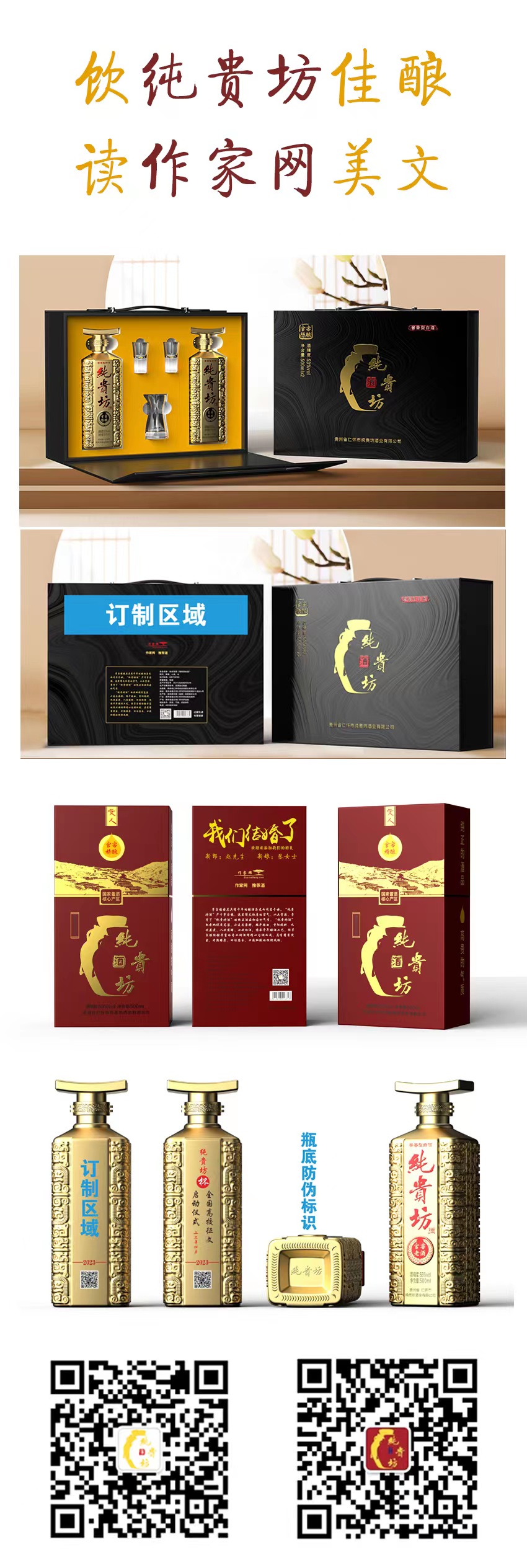


 纯贵坊酒业
纯贵坊酒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