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的焦虑
——任洪渊诗歌专题
曾先后执教于京城两所高校的任洪渊,无疑属于当代学院派诗人。迄今为止,他公开发表的诗作,计有《汉字,2000》10首,《司马迁的第二创世纪》10首,《东方智慧》11首,《女娲11象》11首,《初雪》15首,《黑陶罐》9首,悉数收入其在大陆出版的唯一诗集《女娲的语言》中(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9月版)。论创作数量并不算多,但其特色鲜明,在当代诗歌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他的诗是典型的文人诗,大量使事用典,指涉古典诗歌和传统历史文化内容,从而使他的大部分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古典诗文构成“互文性”的文本关系。但其诗作并不显得古色古香,陈旧熟俗,而是充盈着鲜活的当代性,灌注着饱满的个体生命体验,具有强烈的艺术冲击力。任洪渊多用“后现代”的眼光写法,去解构、重构传统经典之作和原型意象,探索汉语词汇和汉语诗歌在当代的一种新的表现可能。因此,被论者指为“文人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伍方斐《生命与文化的诗性转换——任洪渊的诗与文人后现代主义》,《今日先锋》,1996年第4期)。本文关注的是被指为“后现代”的任洪渊诗歌,与“前现代”的古典诗歌和历史文化的深刻、复杂联系,进而对这种关系进行初步的诠释,以期获得在“后现代”的生存和语境之下,关于诗歌写作的一些启示。

一、从两首情诗说起:《黒陶罐里清莹的希望》和《她,永远十八岁》
谈论任洪渊的人生和创作,都离不开一个关键的人物——F·F。与F·F的相遇,改变了诗人后半生的生活和命运。诗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诗歌创作,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蓬勃的现代意识,饱满的生命张力,无不来自与F·F相遇的激活。在诗人与F·F由朋友而情人而妻子的关系演进中,诗人被时代迟滞的青春激情和创造力,得到了持续的张扬,写出了一首首高质量的传世之作。黑陶罐里清莹的希望,已经变成骄人的现实。爱情,又一次创造了人间奇迹。而奇迹,是从浩劫中的一次“对视”开始的:
又是洪水。混浊的泛滥/只有你的眼睛是一汪蔚蓝/我最早的黑陶罐/存下的清莹涟漪/我和你相对//大火不息。书籍和画卷/焚烧着你美丽的影子/蒙娜丽莎谜一般的笑/在你的唇边,没有成灰/我和你相对//不知是第几次崩溃。我不再担心/罗丹的《思》也被打碎/有你梦幻的额头,白色的大理石/都会俯下暝想的头,倾听/我和你相对//有过洪水。大火。崩溃/黑陶罐里清莹的希望/我和你相对(《黑陶罐里清莹的希望——给F·F》)
据诗人说,那是在十年动乱期间。1976年春天的一次大批判会上,一群暴徒疯狂地焚烧书画,凌辱他人。人类文明的成果正在遭受空前的破坏,人格尊严正在遭受粗暴的践踏。世界仿佛到了末日,洪水泛滥,大火不熄,天崩地裂。爱、美、思的破坏,使人类文明面临着灭顶之灾。这时,诗人发现了一双清莹的少女的眼睛,透过这双纯美的眼睛,诗人看到了时代的污浊丑恶疯狂,看到了自我灵性丧失的屈辱变性扭曲,同时也看到了历万劫而不灭的人类生命之美,思想之美,爱情之美,看到了最早的黑陶罐里存下的最初的一汪清莹的希望。诗人顿时感到他内在生命的复活,重新激发了他创造未来的热望。
此诗有两点最值得注意:一是“黑陶罐”的意象选取,具有原型的意味。诗人拿来这一龙山文化的标志性器物设譬作喻,暗示他们的相遇,是几千年前宿命的注定。黑陶罐里的一汪清莹,是人类的生命之美、爱情之美、思想之美的象征,是人类美好的生存希望的象征。这一意象写眼睛,不仅是诗人全新的创造,更预示了诗人此后创作《汉字2000》、《女娲11象》、《司马迁和他的第二个创世纪》等作品的文化价值取向。二是通过眼睛写灵魂的交流,眼睛是心灵的窗口,一见钟情总是从眼睛开始。诗中的相遇相知,仍是传统的“目成”模式。从屈原《少司命》的“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开始,一直到《西厢记》里崔莺莺的“临去秋波那一盼”,古典诗词曲中借眉目传心意的描写所在多有。但由于时代因素的加入,涤尽了此种模式在旧文学中的某種轻佻艳俗成分,加之喻眼睛为黑陶罐,取象高古,使得“我与你相对”的“目成”显得奇美动人。此外,诗的取象和复沓也来自古典诗歌传统手法。
《她,永远十八岁》写与F·F遇合的辉煌,辟古今咏月诗未写之境:
十八年的周期/最美丽的圆/太阳下太阳外的轨迹都黯淡/如果这个圆再大一点 爱情都老了/再小 男子汉又还没有长大/准备为她打一场古典战争的/男子汉 还没有长大//长大/力 血 性和诗/当这个圆满了的时候/二百一十六轮 满月/同时升起/地平线弯曲 火山 海的潮汐/神秘的引力场 十八年/历史都会有一次青春的冲动/红楼梦里的梦/还要迷乱一次/桃花扇上的桃花/还要缤纷一次//圆的十八年 旋转/老去的时间 面容 记忆/纷纷飘落/陈旧的天空/在渐渐塌陷的眼窝 塌陷/十八岁的世界/第一次开始//年岁上升到雪线上的 智慧/因太高太冷 而冻结/因不能融化为河流的热情 而痛苦/等着雪崩/美丽的圆又满了/二百一十六轮满月/同时升起
一曲青春爱情的颂歌,美妍而又典雅,热烈而又深沉,犷放而又辉煌。“永远十八岁”的“她”,即任洪渊诗中多次出现的F·F。诗人与她初遇时已年近四十,而她,正是女儿十八好年华。于是,“她”的“十八岁”,就此镌入诗人的记忆,成为永恒。这是永难磨灭的“第一印象”。诗的抒情即从“十八岁”切入并展开。第一节写“十八年的周期”,成就了“最美丽的圆”。如果这个圆再大一点,爱情就老了;如果这个圆再小一点,男子汉还没有长大;十八岁成就的这个圆,是最完美的圆。因为,不迟不早,不疾不徐,他们在这一年相遇且一见钟情。那真是一场光辉灿烂的遇合,瞬刻的直觉中,成熟的男子汉的“力、血、性和诗”伴随着十八年来的“二百一十六轮满月/同时升起”;地平线弯曲出浑圆的流线,火山喷发出滚烫的岩浆,大海潮汐,汹涌澎湃,连一向沉稳持重的历史老人,也难抑青春的冲动,红楼梦里再度情梦迷乱,桃花扇上又是芳花缤纷……
辉煌的遇合带来巨大的幸福晕眩,在酒神的沉醉迷狂的幻觉中,那个十八年的最完美的圆“旋转”起来,老去的时间、面容、记忆,陈旧的天空、眼窝,纷纷飘落塌陷。岁月的雪线崩落,积雪溶为河流,冷漠化为热情。激情焕发的爱,摒除了一切衰老陈旧和冷漠,再造了诗人的青春和生命。仿佛乾坤初开,在这“二百一十六轮满月/同时升起”的璀璨的遇合时刻,诗人感到,世界年青得有如十八岁的情人,而他的生命,正第一次簇新地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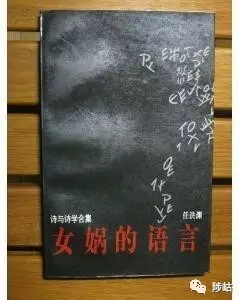
这是一首典型的文人爱情诗。浪漫热烈浓艳,而又不失典丽文雅深沉。既泛溢着浪漫的绮思,热烈的情绪,秾妍的色彩,又富含典雅的格调。对荷马史诗、《红楼梦》、《桃花扇》的典故的现代性运用,使得西方的海伦,东方的黛玉、宝钗、香君,这些个不朽的爱情故事中臻于极致的女性的美,而今都被诗人的情感体验所唤醒,皆集于F·F一身,用典赋予诗中的爱情以纯美深厚的文化内涵。尤其是那“十八年”的“二百一十六轮满月/同时升起”的亘古罕见的“天象奇观”,也只有在现代爱情诗的无比绮丽的幻境中才会出现。从《诗经·陈风·月出》开始,月亮就成为中国诗歌的原型意象,月亮意象是女性柔美和家园安谧的象征,含蕴着思念故乡、思念亲人、思念远方的感情,寄托着高洁美好的人生理想,喻示着清高脱俗的人格心理,渲染着清幽孤寂的环境氛围,烘托着朦胧飘渺的审美意境,映现着澄澈空明的物境心境,代指着自然、宇宙和永恒的存在,启示着人生意趣的活参顿悟,触动着寥廓的宇宙意识、苍茫的历史意识和深邃的生命意识,它的圆缺,又成为人间聚散离合的象征。在科学的领域,美国宇航员1969年7月率先登上了月球;但在审美领域,三千年前的中国诗人就开始了对月亮的动情吟唱,月亮的光影从古至今洒落在中国人广阔而又敏感细腻的心灵空间,它凝聚着我们古老民族的生命感情和审美感情,成为高悬中国诗歌天空的文化原型。月亮和月光,无疑是属于中国诗人和中国诗歌的:“只能说月亮为东方而存在/为东方在云层中沐浴/月亮黄色的面孔/竟这样接近我们东方人的肤色/东方人因此也为月亮而存在/……/东方原本是月亮的国度/读东方诗就象步入月色中/没有月亮的晚上/东方诗人从不吟诗”(阿吾《元宵夜随想》)。尽管20世纪的霓虹灯和摩天楼遮住了月亮的清辉,但新诗中的咏月之作仍极多,立意构思和意境韵味多数未逾古代咏月诗词的藩篱,显示了植根于中国诗人文化审美心理中的原型意象的强大生命力。但在任洪渊的笔下,在当代人热烈浪漫的爱情幻觉中“同时升起”的“二百一十六轮月亮”,对于惯读古今无数咏月诗词的读者来说确属见所未见,相比之下,谢希逸的月亮,张若虚的月亮,李太白的月亮,苏东坡的月亮,似也难及任洪渊笔下的月亮光华烂漫。此诗不仅辟开了古今咏月诗未写之境,而且奠定了任洪渊诗歌赞美青春、讴歌生命、厌弃衰老、超越死亡的抒情基调,和他用典拟作、古典美与现代美互映互衬的写作手法。
二、“互文性”的用典、拟作和改写
使事用典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诗歌创作手法,这种手法在西方诗人如庞德的《诗章》、艾略特的《荒原》、《四个四重奏》中也被使用,西方文论称这种手法为“互文”或“互文性”。魏晋以来的中国诗人诗歌,把使事用典作为创作时的常备手法加以普遍地运用。一方面是诗人的学者化,遍读典籍,学问淹博,创作中信手拈来,为我所用,无不妥帖。另一方面,古典诗歌尤其是近体诗词形式精短,字数有限,要达到以有限传示无限的创作目的,嵌入典故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做法。还有就是诗人不便、不愿直说时,可以用典故来代指、暗示。古代诗歌的使事用典手法,在现当代新诗中得到了传承,尤其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诗歌和台湾诗歌中,使事用典的例子极多。二、三十年代新诗人和台湾新诗人,都有较好的旧诗旧学根底。五十年代以后,大陆部分诗人知识结构较为贫弱,使事用典在主观上非其所能,客观上也与大众化、通俗化的提倡相违背。至80年代社会生活渐趋正常,诗人的知识结构普遍得到改善,随着传统文化热的持续升温,在朦胧诗人和新生代诗人中,都有一些“文化诗”创作者,写出了一批规模宏大的“文化史诗”,其中包含了大量的传统诗歌和历史文化内容,使事用典成为这类“文化诗”的必备手法。任洪渊的学院派文人诗,总体上也是传统文化热的产物,可以归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盛一时的“文化诗”的范畴。但任洪渊又不像那些文化诗人竭其心力,演绎、铺排历史文化知识,构筑史诗规模的鸿篇巨制,他的诗大多写得精短,保持了抒情诗的纯粹性,在当代人的生命体验和语境氛围中,恰到好处地嵌入典故,唤醒民族成员关于古典诗词和历史文化的共同记忆,激活读者新鲜如初的审美感觉。使事用典对任洪渊的诗歌美感是一种丰富和深化,同时也是对典故意象的一种敞亮与刷新,他让古典美焕发出簇新的当代光芒。试看他的《你是现在》:
如果没有你的眼睛/斑竹上打湿了几千个春天的泪/怎么会打湿我的/秘密如果不在你的唇边/诗经初开的那朵笑,也早已枯萎//有你的江天,春潮花潮月潮/才汹涌着你/假如你不倾斜,如大陆/天上的黄河/也奔流不到海//假如敞开你的四月/随李贺的红雨乱落/那么你的落在哪里/你有一个最深的黄昏/淹没所有的傍晚/你有一个滂沱的雨季/落尽过去的云/你是现在,现在是你
诗中的“你”,应该就是诗人的“F·F”。诗人强调“你是现在”,凸显此时此刻的“你”,对诗人的感知的无比重要。但在这“现在时态”之中,无法遏制地泛涌而出的,却尽是“过去时态”的内容:“斑竹上的泪”用舜帝之二妃的凄美爱情神话,同时指涉了古代无数咏此神话的言情诗词;“诗经初开的那朵笑”,用《诗经·卫风·硕人》对庄姜“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出色描写形容;“江天”与“春潮花潮月潮”,用初唐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意象和诗境;“李贺的红雨”,用晚唐李贺《将进酒》诗句“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中的意象;“黄昏”既与李贺诗句中的“日将暮”相关,同时又关合了古典诗词最常写及的“黄昏”时空意象和意境;而“滂沱的雨季”、“落尽过去的云”中的“云”和“雨”,起码在潜意识中,恐怕也暗含有宋玉《高唐赋》中“云雨”意象的原型意味。诗人就此曾经说过:“宋玉的高唐梦,曾经是一个美的极限。从那以后,中国漂载着女性的想象似乎都再也飞不过神女高唐的高”,就是到了今天,诗人们面对巫山,也“没有一个现代眺望不顿时掉进宋玉高唐的古典里”(《找回女娲的语言——一个诗人的哲学导言》,《女娲的语言》代序,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9月版,第3页)的确如此。在这个文本里,我们发现一个奇妙的现象:那就是古典与现代的互相映衬,互相唤醒,互相激活,诗人面对的是“现在”的“你”,恍然之间,又从你的眼泪里读出了“娥皇女英”洒在斑竹上的泪痕,从你的笑靥里读出了“庄姜”的动人巧笑,从你的“江天”读出了初唐汹涌澎湃着青春之美的“春潮花潮月潮”,从你的“敞开的四月”读出了晚唐那场美艳伤感到让人难以为怀的“乱落的红雨”,从你的“最深的黄昏”读出了巫山飘渺的云情雨意……“现在的你”因了纯美的古典内涵的加入,而更见惊采绝艳;那已淡入历史记忆的渺远的古典美,也被“你的现在”复活过来,宛然在目,焕然一新。诚如诗人所言:“不是由于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她(按:即这首诗中的“现在的你”)的唇边才有笑的神秘。相反,由于她笑了,蒙娜丽莎的笑才没有在嘴角枯萎。不是蒙娜丽莎的笑照亮了她的面容,而是她的笑照亮了蒙娜丽莎的面容。她的笑才是最初的。因为她,画里,诗里,神话里,甚至埋葬在厚厚的坟土里的迷人女性,再一次活在我们的四周,与我们相追逐”( 《找回女娲的语言——一个诗人的哲学导言》,《女娲的语言》代序,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9月版,第2—3页)女娲、娥皇、女英、简狄、褒姒、庄姜、巫山神女、虞姬、卓文君、昭君、李香君、金陵十二钗,海伦、蒙娜丽莎,这些中外传说中、历史上、诗歌里、艺术中的“迷人女性”,全都姿容妙曼地出现在任洪渊的诗歌里。作为读者,当我们看到“前人的文本从后人的文本里走出来”时,我们在鉴赏中所获致的美感就不仅仅是当下的、单一的,而是集合了文化史上、诗歌史上无数经典的青春爱情之美的内蕴无限丰沛的复调,“古典美”和“现代美”,在这首大量用典的当代诗歌文本中实现了“双赢”。
任洪渊为数不多的诗作中,使事用典之作所占比重极大。《汉字,2000》、《司马迁的第二创世纪》、《女娲11象》三组诗,此处姑置不论,仅就《东方智慧》、《初雪》、《黑陶罐》三辑中的诗稍作分析。《黄昏时候》用了李商隐《乐游原》、《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诗典故;《她,永远十八岁》用《桃花扇》、《红楼梦》、《伊里亚特》典故;《最后的月亮》有句“唐诗宋词里的许多月亮”,指涉了所有咏月的唐诗宋词;《四十八种美丽,哪一个是她》写山西晋祠的48尊宋代瓷塑侍女像,其中的“虞美人”,既特指《史记》中的虞姬或唐宋词词牌,也可泛指“宋瓷”般美丽的古典女子,诗中又出现了“金陵十二钗”和宝玉“男人是泥做的”等《红楼梦》典事;《鲲,幻想的化石》用庄子《逍遥游》鲲鹏变化的寓言;《远方》用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故事;《望》与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那几声钟,那一夜渔火》与张继的《枫桥夜泊》,构成古今对应的拟作性质的“互文性”文本;《第一个早晨》用《史记·项羽本纪》“乌江自刎”和屈原赋《离骚》、投汨罗典故;《你是现在》用娥皇女英神话、《诗经·卫风·硕人》、宋玉《高唐赋》、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李白《将进酒》、李贺《将进酒》典故;《时间,从前面涌来》用《诗经·陈风·月出》、宋玉《九辨》、司马迁《史记》、陶渊明《饮酒》其五、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典故;《蝴蝶》用《庄子》和李商隐《锦瑟》“庄生晓梦迷蝴蝶”典故;《秭归屈原墓》是一首吊古之作,大量化用、指涉屈原《离骚》、《涉江》、《天问》等作品的诗句、意象;《香溪》写于昭君故里,用昭君出塞故事和杜甫《咏怀古迹五首》“群山万壑赴荆门”诗意;《巫溪少女》用瑶姬、阿诗玛神话传说,同时指涉了历代题咏“望夫石”的诗词;《太阳树》用《山海经》和屈原辞赋中的“若木”神话;《长江》用“后羿射日”、“夸父追日”神话,屈原《离骚》、《九歌》,宋玉《高唐赋》,李白《早发白帝城》、《望天门山》、《渡荆门送别》、《大鹏赋》、《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行路难》等诗赋的句子、意象。
用典之外,任洪渊的组诗《女娲11象》、《司马迁的第二创世纪》,与相关古典文本之间的关系则属跨文体改写性质。前者改写了女娲、嫦娥、后羿、刑天等神话传说,后者改写了《史记》多篇传记中的人物故事。改写成的新诗文本灌注饱满的现代意识,对古老的神话传说和历史人物作出了崭新的诠释。《女娲11象》分上篇、下篇两辑,共11首。上篇6首,改写女娲创世、造人的相关神话传说,而旁及斯芬克斯之谜和山顶洞人的头盖骨。下篇5首,前三首改写女娲补天、嫦娥奔月、后羿射日、刑天舞干戚神话,第四首写象形文字和黄河,末首分写“神:普罗米修斯的火与鹫”、“佛:释迦牟尼的鹰与鸽”、“人:庄子的蝶,鲲鹏”。组诗铺陈描写和思辨议论较多,表现出诗人融合神话传说、历史现实与东西方文化的努力,借此构建宏大史诗的意图明显。从抒情诗的角度看,似不如改写《史记》的一组来得集中、鲜活、纯粹。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文学史上各体文学的取材渊薮,不仅叙事性的戏曲小说从中大量借取人物故事,诗歌特别是咏史诗,也喜欢以《史记》的人物事件作为题咏对象。任洪渊的《司马迁的第二创世纪》,作为跨文体改写的新诗文本,性质上属于咏史诗的范畴。组诗的标题即揭示了司马迁以其饱蘸诗性的不朽史笔,为中国上古史“创世”的巨大功劳。中华民族从黄帝到汉武帝之间3000年的发展历史,正是这个古老的民族的青春期,那如火烈烈、如水滔滔的激情岁月,正当5000年民族历史文化和文明的“创世”阶段。如若不是借助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代表的历史典籍记载,过往的激动人心的一切,早已云消雾散,灰飞烟灭。那远古时期一幕幕社会生活的场景,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故事,以及众多的日常琐事与细节,之所以能够完好如初地展示在后人面前,正是有赖于具有“良史”精神的司马迁手中那支凌云健笔的出色挥写。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迁的确具有“创世”的功劳,他的《史记》堪称“第二创世纪”。组诗选取司马迁、项羽、伍子胥、聂政、孙膑、高渐离等悲剧人物的故事加以改写,与这组男人对应的,是对简狄、褒姒、庄子妻、虞姬等几位著名女性的题咏。组诗首先切入“创世者”司马迁,正是缘于遭受了男人不能承受的奇耻大辱的“阉割”,才使“他成了男性的创世者”,他用“汉字”,复活了已经消失的历史场景和人物,使“一个个倒卧的男女”重新“站起”,使过往的“历史第二次诞生”。改写《项羽本纪》的《项羽:他的头、剑、心》,对“心”与“头”加以区隔,“心”代表性情,“头”代表观念,当项羽自己用“剑”割下头颅,“抛给那个需要他沉重的头颅的胜利者”时,“胜利者”得到的其实已经是“一个失败”。人的“心”,悲剧英雄的“心”,是无法征服的。逃难者伍子胥夜过昭关,“用最黑的一夜辉煌了一生”,昭关的一夜,成了“最明亮的黑夜”,使“一个个早晨凋谢在门口”。自毁面容的刺客聂政,毁坏的是“衰败和死亡”,留下的是永远的青春。击筑者高渐离眼睛被挖掉的一刻,“黑暗破了”,他的“灵魂”,又回到了“白衣冠”送别的悲壮的易水边,而“生命,痛楚得雪亮”。在这些题咏悲剧人物的诗中,任洪渊关注的是人的悲惨命运,张扬的是悲剧生命的壮烈辉煌和崇高尊严,这都是现代的意识和理解,与古代诗人的相关题咏并不重复。改写《孙子吴起列传》中孙膑故事的《孙膑:断足,没有凯旋的穷追》一首,最具内涵深度,孙膑在灾难中创造了生命的辉煌,在常人无法承受的灭顶之灾中,创造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生命辉煌:“断足/他完全放出了自己,穷追/天下的男子,没有一支大军/逃出他后设的/三十六计”。然而,可惜“只是没有一次凯旋/回到他断足的/这一天”,戕害和创伤,也是永远无法平复的,毕竟让人悲怆!这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于忧患”,不是对所谓“抗争命运”的简单肤浅的表现。人生历程中所遭受的不幸和痛苦,是无论怎样辉煌的胜利都不能消除和抹去的,诗篇因这最后三行,而显得异常苦涩沉重。
组诗对女性的表现,以题咏虞姬和褒姒二首最佳。“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推翻暴秦,“推到十二座金人”的力量,最后“全部静止在”虞姬肢体的“曲线”上,仿佛不是项羽,而是虞姬“轻轻举起古战场/在巨鹿/在鸿门/在垓下”,战场上“钢铁与青铜击杀的铿锵”,最后都“缠绵在她的一只歌里”,正所谓“柔弱胜刚强”,这是对女性的力量,对美的力量的前无古人的礼赞。把这种礼赞推向极致的,是改写《周本纪》中“烽火戏诸侯”故事的《褒姒:他烂漫男人,烽火桃花》一首:
等她一笑/一丛丛无花期的花,开了/烽火//男人的桃花//一笑/灼伤了太阳,融化了太阳/乱涌的星云/老了的血,谢洒成灰烬/只剩下最小的一滴,开始生长//残败在最红的开放里/耸峙的塌陷/又一种金属,在身体的深处/乱坠为花/没有火/没有刀兵的,烽/烟//等她烂漫/男人,烽火桃花/嫣然的战争
天生丽质的褒姒,一笑永恒。女性之美,乃是“一丛无花期的花”,常开不谢。男人的血性和膂力,需要女人的美色来“烂漫”,来点燃,来激扬。有了女性美的加入,不仅“烽火”绽放“桃花”,连恐怖的“战争”也妩媚得“嫣然”。倾城倾国,原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美,不是罪恶。美女褒姒,不是亡人家国的“妖姬”。看来,任洪渊的确是唯美的,迟到的爱情,使他对青春女性之美,有着近乎膜拜的迷醉。所以才能写出这首洗尽传统视野中褒姒身上的道德罪恶感的现代“咏史诗”,诗中表现出的历史观、道德观和审美观,诗人用女性之美来拆解历史和道德教条、诠释性别和战争关系的做法,已有某种“后现代”的意味,这是“前现代”的古典诗人无法写出的颇为“另类”的咏史诗。
任洪渊的一些诗作与古典诗歌作品之间,还存在着一种类似模拟、仿写的关系。创造从模仿开始,从魏晋时代起,因为有了丰厚的古代诗歌传统积累可资效法借鉴,诗人中开始兴起拟作的风气。西晋诗人喜欢模拟《诗经》、汉乐府和《古诗》。陆机的《赠冯文罴迁斥丘令诗》八章、《与弟清河云诗》十章,潘岳的《关中诗》十六章、《北邙送别王世胄诗》五章等,均为学习《诗经》的四言体名篇,但文辞趋向华美。在《乐府诗集》的《相和歌辞》中,大多数曲调都有陆机的拟作。其中陆机的其他乐府诗也多成为后来拟作同题乐府诗的样本。陆机的《拟古诗》十二首,基本上都是拟《古诗十九首》的,在内容上皆沿袭原题,描写由简单趋向繁复,格调由朴素趋向华丽,显示出诗歌的文人化倾向。此后,拟作成为历代诗人的一项基本功训练,或抒情达志的一种方式。连文学史上最天才的李白,也曾经前后三拟《文选》,皆不满意,辄焚之,今惟存《拟恨赋》一篇(9)。李白今存的乐府体诗,大量地沿用乐府古题,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皆能曲尽拟古之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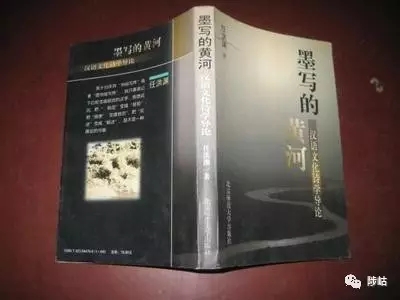
在20世纪新诗创作领域,模拟和仿写古典诗歌文本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略举数例,如何其芳的《罗衫》与班婕妤的《怨歌行》,陈江帆的《穷巷》与王维的《渭川田家》,郑愁予的《错误》与苏轼的《蝶恋花》,席慕蓉的《悲喜剧》与温庭筠的《梦江南》,高准的《香槟季》与《诗经·关雎》,舒婷的《船》与《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冯青的《最好回苏州去》与周邦彦的《少年游》之间,都存在着前者模拟改写后者的关系。任洪渊的《那几声钟,那一夜渔火》与张继的《枫桥夜泊》、《望》与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之间,也是一种模拟改写性质。先看他的《那几声钟,那一夜渔火》:
寒山寺/那几声钟,震落了夜半的/月,霜,鸦,震落了泊在这晚的/船和梦,也震落了/钟。此后的钟声都沉寂/还要震落我今夕的躁动成永久的宁静/从未绝响的那几声钟//那一夜渔火犹自燃着/一个个早晨都已熄灭/渔火自那一夜,燃着/一丛不凋的枫/暖着寒山/一个秋深过一个秋/在我的身上堆积//我的一切都沉进霜夜里/只有这瞬间照亮的笑容/不会隐去,一个明亮的裂痕/黑夜不能在这点上合拢/等千年后的相见/等一个一个微笑和我相对/围着这一夜渔火,在几声钟之间
诗共三节,第一、二两节模拟、改写唐代张继的名诗《枫桥夜泊》,突出诗中的“钟声”和“渔火”两个意象,寒山寺的夜半钟声,成了诗歌史上和历史上最著名的钟声,它不仅“震落了夜半的/月,霜,鸦,震落了泊在这晚的/船和梦”,它“也震落了/钟。此后的钟声都沉寂”。唯有那几声钟,千年未曾绝响;还有那“一夜渔火”,从唐代一直燃烧到现在,从张继泊船的那夜一直燃烧到今夜,一个个早晨都熄灭了,只有那渔火一直燃着,燃成“一丛不凋的枫/暖着寒山”。因了那永久传响的“钟声”和永不熄灭的“渔火”,任洪渊沉浸于展延自历史深处的永久的霜夜,永久的秋意,永久的宁静。这里有任洪渊对于古典诗歌所达到的不可逾越的艺术高度的深刻认知。第三节里渔火“瞬间照亮的笑容”,如“黑夜不能合拢”的一道“明亮的裂痕”,是属于任洪渊的,属于当代和今夜的,因了千年前传响至今的“钟声”和燃烧至今的“渔火”,任洪渊期待自己的“笑容”也能在千年后与“一个一个微笑相对”。这里,任洪渊通过拟作,实现了一个当代诗人与经典诗歌文本一起百世流芳的不朽愿望。再看他模拟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望》:
幽州台不见了/幽州台上的那双眼睛,还望着今天/等我偶然一回顾//回头/已经远在他的视线之外/不能相遇的目光/碰不掉他眼眶里/千年孤独//幽州台不见/寂寞的高度,还在/空濛的视野,还在/太凛冽了/幽州的白日/被距离隔成孤零零的眸子/寒冷地发亮//不用登临,一望/我已在悲怆之上/能在我的眼睛里/睁破这一片空茫吗/仰起头,接滚过幽州的泪滴/从我的脸上落尽/尽落谁的脸上
“怀才不遇”是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体制性的永久生存困境,缘此,生不逢时的“千年孤独和寂寞”,也就成了古典诗歌抒写不尽的永恒的主题。面对无穷无尽的时间和无边无际的空间,只存在于时空相交的微不足道的一点上的“现在”的人,无比渺小短暂,如不能及时有为建功立业,时光一去,将万劫不复。心非木石岂无感,念此怎能不怆然涕下?!当年登上幽州台的陈子昂如此,当代看不见幽州台但可以诵读《登幽州台歌》的任洪渊亦然。尤其是任洪渊那一代经历了1957年“反右”和1966年“文革”的知识分子,磨难不断,命途多舛,大好年华,付诸流水,读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特别容易引发共鸣。任洪渊的大学时代在“蓟门”、“幽燕”度过,后来也在北中国生活、工作,他自剖心迹说:“我在这里的剑气和筑韵里慷慨悲歌。我总想在幽州台上量一量我寂寞的高度,悲怆的高度。我尤其想在黄金台上量一量我知识分子的现代价值。尽管幽州台连残迹都没有留下,但我时时回头,总想碰见幽州台上那双最孤独的眼睛,碰掉眼眶里的千年孤独。”(《女娲的语言》代序,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9月版,第17页)任洪渊可能比谁都明白,生逢极左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的时代,他自己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价值”究值几何。看来任洪渊对命运的确已有自觉,不然写不出诗的末几行:“仰起头,接滚过幽州的泪滴/从我的脸上落尽/尽落谁的脸上”?他已意识到到自己的悲剧命运传承者的角色,陈子昂的泪滴滚落任洪渊的脸上,再从任洪渊的脸上落在“谁的脸上”?这诗末的一问,暗示这一切也许真的还远远没有结束。
三、影响的焦虑:组诗《汉字,2000》
20世纪新诗人面对古典诗歌传统的“影响焦虑”心理,在任洪渊的组诗《汉字,2000》里有着集中的体现。这组诗一共十首,指涉了孔子的“泰山”,屈原的“昆仑落日”,庄周、李白的“鲲鹏”,陶潜的“停云”、“菊花”,王勃的“落霞”,王维的“长河落日”,李白的“月亮”、“黄河”,宋玉、杜甫的“秋”,苏轼的“长江”等经典意象。它是任洪渊的文学史意识觉醒后的产物,充分证明了作者是一个具有清醒的文学史意识的诗人,而不是一个盲目的、自在的、无意义的诗歌写作者。
新诗史上有不少诗人,限于知识背景的某种匮乏和知识结构的某种欠缺,其实并不真正明白前人和他人都写过了什么,写到了什么程度,自己动手写诗的时候,应该如何避免和前人、他人重复。更有一些用现代汉语写作的诗人,对母语的微妙处并无解会,甚至缺乏起码的母语敏感,他们要么依靠一时的情绪冲动,要么图解流行的意识形态概念,要么模仿翻译过来的域外诗歌,尤其是近年来在西方诗歌中讨生活的诗人,还博得了与“国际接轨”的“新潮”、“先锋”的“美誉”。经济、政治是可以也应该接轨的,文学和诗歌恐怕还是要坚守民族性,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接轨导致民族性的丧失,克隆的赝品,其艺术个性和价值将无从体现。一位当代诗人认为新诗“并没有一个可以直接师承的传统——古典诗歌由于语言的大断裂成为一种束之高阁的东西”(《回答四十个问题》,见《游动悬崖》,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对一般人来说可能确是如此,但一个汉语诗人如果出于语言障碍而无法阅读古典诗歌,那么他还如何去做一个汉语诗人呢?事实上,现代新诗人和当代台湾有成就的新诗人,旧学和旧诗根基大都相当深厚,因语言障碍而读不懂古典诗歌,是大陆50年代以后没有受过系统教育却去写诗的一些人的情况,当代名校中文系出身的诗人,竟然也存在这个问题,的确令人费解。在《一份‘现代性’的美丽》一文中,这位当代诗人认为:废名对林庚《沪之雨夜》显示的“晚唐的美丽”的评价不确;他把古典诗歌中比比皆是的意象跳跃、画面组接的手法,硬说成是西方诗歌的现代手法,并从《沪之雨夜》里读出所谓现代诗的“现代性”,实在是惊人之论。作为开放的二、三十年代诗人,林庚的诗中肯定有现代性,但肯定不是这首意象、语词、意境、韵味酷似古典诗词的《沪之雨夜》,他不得要领的牵强分析,真正莫名其妙,让人怀疑他作为一个中国汉语诗人,对一首中国汉语诗歌美感风格的基本感受能力。因为稍有一点古典诗词阅读经验的人,凭着直觉,都不难发现《沪之雨夜》散发出的浓郁古典气息。而另一位“先锋诗人”,写过一首在蛮荒的青藏高原之夜“仰望星空”的诗作,诗的前半神秘、幽邃,但后面突然出现了一句“我像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显得不伦不类,这句典型的“后殖民”话语,破坏了整首诗的抒情调性,让人怀疑他的种族、文化属性,他好像不是在中国的青藏高原写诗,而是在欧洲的神山上或教堂里写诗,中国神话和民族的源头昆仑山,此刻就矗立在他身旁,屈原的《离骚》、《涉江》和诗歌史上许多诗人都曾写到过的昆仑神话世界,他却毫无感觉。因此,在严格的意义上,很难说这一类诗人是“中国”诗人。因为昧于古典诗歌传统,他们没有影响焦虑心理,创作上和理论上的压力减轻了,但盲目性也随之增加。任洪渊显然不是如此,他的一段自述值得注意:
直到1987年,王维的长河落日依旧圆在我的黄昏。阅读,书写,我竟自以为在检阅一场又一场光华夺目的语言仪式——直到被词语压倒的一天,我才惊觉,我不过是在被阅读与被书写,而且在被别人的词语阅读与书写而已。……王维的落日照临在我的天边。在语言的照耀下,我是谁?我在哪里?一轮王维落日的落日。词语的落日亮着,我光芒四射地消失。……既然王维的落日,已经永远圆在一个下降的高度,从此,我的每一次日出都在王维的落日下。王维必定是从生存的起点就向往终结的空无,他才把一轮落日升到如此的高度,并且升得如此圆满,以至成了一个无边的圆。王维的圆,已不在世界之上和生命之外,所有的高度,方向,时间和空间,都沉落在这个圆的无边里。……王维落日圆的宁静与浑茫,是他的生命达到的无边的空明,却也同时给自己和自己之后的生命设下了一个逃脱不掉的美的围困:一座光明的坟。因为这是终结。他已静美到不能打破自己。……这是被阅读与被书写的生命虽生犹死的时刻,不得不死的时刻。我要从我的天边抛下王维的落日。词语的落日只能由落日的词语击落。(任洪渊《墨写的黄河——汉语文化诗学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153—154页)

因为谙熟古典诗词表现艺术的极致,憬悟了作为一个晚生的当代新诗人所处的语言困境,任洪渊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焦虑”心理,和强烈的寻求突破的愿望。的确,在屈原、陶潜、李白、王维写过诗之后,后起的诗人怎样写诗,这的确是摆在每一个“晚生”的诗人面前的不容回避的严峻问题。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还有类似的表述:“还没有完全死在语法里的汉语,是中国人自由的天赋。但是几千年的文化沉积,已经使每一个汉字如此沉重,以至当代诗人几乎再也动摇不了一个词语。”“我们近三千年文字的生命已经衰老。历史、文化的压迫集中为词语的压迫。现代生命承受不起一个古老的词。”(《联合文学》1990年8期,第165—179页)(这是对汉语的创造与变革的呼唤。)他深切地感到“三千年古典大师的卓越创造,已经缀满整个汉字世界”(59)。面对陶潜的停云、王维的落日、李白的月亮等经典意象,如何寻找个人的新词语,是摆在当代诗人面前的几乎无解的难题:
鲲 / 鹏 / 之后 已经没有我的天空和飞翔/抱起昆仑的落日/便不会有我的第二个日出/在孔子的泰山下/我很难再成为山/在李白的黄河苏轼的长江旁/我很难再成为水/晋代的那朵菊花 一开/我的花朵/都将凋谢(《我只想走进一个汉字,给生命和死亡反复读写》)。
古典诗歌杰作不仅是令后人肃然起敬的艺术典范,而且也是让后人难以逾越的“海拔高度”:“可惜没有一颗星的速度/能够飞进李白的天空/他的每一轮 明月/照 旧圆”(《月亮一个不能解构的圆》)。“当王维把一轮 落日/升到最圆的时候/长河再也长不出这个 圆/黎明再也高不过这个 圆”(《文字一个接一个灿烂成智慧的黑洞》)。于是诗人急切地叩问:“我的太阳能撞破这个圆吗/我的黄河能涌过这个圆吗”?诗人失神地看到:“纵使太阳燃烧成 黑洞/月月年年/照旧 石头的月亮碎不了文字的月亮/半缺的上弦补圆了未破的下弦”,那轮属于李白的“月亮”,已经成为“一个不能解构的/圆”。现代人即使“穿越了南极的冰雪/也走不出一个秋字的边疆”,宋玉的《九辨》、杜甫的《登高》等经典之作对秋天具有“母题、原型”性质的表现,使今天的诗人遭受“一个字的永远流放”。而属于“陶潜的停云”、“王勃的落霞”的天空,“就是升起一朵一朵 原子云”,再也“华采不了”,诗人沮丧地发现:“原子云也原始着”那朵“停云”,而“天空已经旧了”(《天空旧了原子云也原始着那朵云》)。无数汉语诗歌的经典语词“一个接着一个/灿烂成智慧的黑洞//好比/恐/龙/庞大到吃掉世纪/也吃掉了自己/空洞为一个无物的/名词 活着的死亡/最虚无的存在”(《文字一个接一个,灿烂成智慧的黑洞》)。面对这一个个灿烂的“汉字黑洞”、“汉字恐龙”,也就是古典诗人已然臻至的汉字表达力的极限,有多少“晚生者”已经被诗国昔日的辉煌成就不幸地压垮了。所幸任洪渊是勇者,在古典诗歌那“解构不了的圆”、“走不出的边疆”和“飞不过的北回归线”面前,高山仰止的任洪渊一方面承受着巨大的心理焦虑的压力,一方面勇敢地寻求着突围的出路。他把创造新鲜语汇和诗歌的希望,寄托在对原初汉语词汇的寻求上:
那么多文字的/明月,压低了我的星空/没有一个/陨/蚀//等你的第一声呼叫/抛在我头上的全部月亮/张若虚的/王昌龄的/李白的/苏轼的/一齐坠落/天空是你的/第一个月亮,由你升起//词语击落词语/第一次命名/你,一个新的主语/孤零零诞生/抗拒死亡,穿过词与词/遥远的光年/追回所有的象形文字/你的新月,依然圆在/苍老的天空/几千岁的童年
当那么多古典“文字的明月/压底了我的星空时”,是呀呀学语的女儿的“第一声呼叫”,使“抛在我头顶的全部月亮/张若虚的/王昌龄的/李白的/苏轼的/一齐坠落”,于是女儿新鲜的“词语”击落古典的“词语”,天空仿佛第一次升起一轮属于儿童的崭新的“月亮”,“苍老的天空”也重新回到了“几千岁的童年”(《词语击落词语第一次命名的新月——给女儿TT》)(60)。在这里,新生的儿童充当了当代汉语诗歌的“新的主语”,也就是说,汉语诗歌新生的希望,在于未经使用的童真语言的发现上。但这个“月亮”只对学语的女儿来说是“新月”,是她用概念来“命名”存在的第一次新鲜的经验,“天空”仍旧是“苍老的”,对成年人来说,“月亮”其实并不新鲜。任洪渊的本意,是回到汉语词汇的“原初”,找回汉语词汇第一次使用时的仿佛新生儿般的原始的新鲜感,从而实现创造崭新的诗歌文本的目的。“月亮”自从在《诗经》的《陈风·月出》中升上中国诗歌的天空,就成为永不陨落的原型意象,古代诗人说“无限新诗月下吟”,当代诗人说“在没有月亮的晚上/中国诗人从不写诗”,月亮催生了古今诗人无数动人的诗篇,不管是怀乡也好,思亲也罢,大要总不出《陈风·月出》的“望月怀思”心理情感模式。任洪渊的诗情也是月亮催发的,这一点和古今诗人并无二致,此诗和《月亮,不能解构的圆》、《她,永远的十八岁》都是如此。所不同的是,任洪渊作为当代新诗人,不愿意再去因袭几千年诗歌中月亮意象的意蕴,他试图“解构”月亮,也就是想赋予“月亮”这个古老的诗歌原型意象以新意,这就是前人和他人的咏月诗里所未曾写过的,任洪渊的咏月诗也因此而出新意。他的《她,永远的十八岁》中所写“二百一十六轮月亮同时升起”的天象奇观,和这首《词语击落词语第一次命名的新月——给女儿T·T》所写的新生儿第一次看到并呼出的“月亮”,都是古今咏月诗的未写之境。
任洪渊突破汉语词汇表达极限的努力,在《没有一个汉字,抛进行星椭圆的轨道》一诗中也有出色表现:
俑/蛹/在遥远的梦中,蝶化/一个古汉字/咬穿了天空也咬穿了坟墓/飞出,轻轻扑落地球/扇着文字/旋转//在另一种时间/在另一种空间/我的每一个汉字,互相吸引着/拒绝牛顿定律
任洪渊在另一首诗中曾经表示“我只想走进一个汉字,给生命和死亡/反复读写”,这首诗可谓诗人愿望的最好体现。殉葬的“俑”代表死亡,蝶化的“蛹”代表新生,“俑”与“蛹”读音相同,字形相似,意义完全相反,构成了“生与死”的两极对立。禁锢“蛹”的茧壳也与埋葬“俑”的坟墓相仿,那就是囚禁它们的全部空间,它们的“天空”。但“蛹”毕竟不是“俑”,它在“蝶化”的过程中,“咬穿了天空也咬穿了坟墓”,获取了解放和新生,自由的汉字释放出巨大的审美能量,在另一种时空——不同于西方科技文化语境的东方审美文化语境中,“拒绝牛顿定律”。 这也是另一种形态的“词语击落词语”。作为原型意象的“蝶”,出自《庄子》,诗中描写的“轻轻扑落地球/扇着文字旋转”的自在和迷醉,依稀之间也有“庄生梦蝶”的遗韵。
《汉字,2000》之外,影响焦虑心理在其它几辑诗中也有程度不同的表现。比如《东方智慧》中的《第一个早晨》、《时间,从前面涌来》、《黄昏时候》、《远方》等诗。由于“晚生”,诗人发现自己“一步就走进汉代走进/司马相如堆砌成了赋的岁月”(《远方》)。任洪渊的家乡在四川邛崃,即古临邛,是汉代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爱情故事发生的地方。他说:“我从小就吃着汉代的盐”,他感觉“历史一直停留在汉代的盐与铁里,停留在卓文君、司马相如的琴与赋,井与酒里。”但他决计要走出那“走不出的”对“故乡的眺望”,不管“倒下再多的背影”,他也要“第二次出发”,走向“远方”。同样由于“晚生”,“夕阳”把任洪渊和“李商隐拉到”了“同一条地平线上/牡丹花开败的地平线上”,黄昏“从他的眼睛涨过我的眼睛”,“落日”半沉在“他的天边和我的天边”,朦胧了“他和我的黄昏,今天和明天的黄昏,圆满失落的黄昏,起点终点的黄昏”(《黄昏时候》)任洪渊渴望走出李商隐的“夕阳黄昏”,他要把把自己的“夕阳”,“抛成一个升起,给另一个天空”,“把所有的眼睛拉成一条地平线/开满红牡丹”。这里,已不再是晚唐“近黄昏”的“夕阳”,而是今天“升起”的朝阳;不再是雨中已“开败”的牡丹,而是正在盛开的“红牡丹”。因为“影响”的严重“焦虑”,任洪渊执意回到原初,回到“第一个早晨”,回到“你走到乌江/那一场悲剧才完成/你走到汨罗/离骚才开始”的“第一个早晨”(《第一个早晨》)。这是诗人“自己创世纪的第一个早晨”(《女娲的语言》代序,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9月版,第17页)。时间和空间从这个“史记最早的纪年”的早晨、从这个“神话的边缘”的早晨开始,这个衰老的世界回到诞生之初,“还是第一次月出/第一个秋/第一座南山/第一杯酒”和“第一个人”,于是有了《司马迁的第二创世纪》和《女娲11象》的写作,这是一种回到远古的重新开始。诗人痛感“在西方语法严密封锁的关口前,西方现代诗人无不一一陷入一批又一批扭曲的、残缺的、伤痕累累的词语中。叛乱的语言完不成语言的征服。世界多一个现代诗人就多留下一批受伤的词语。思与诗同在的语言,离现代西方人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遥远。人被破碎的语言更浑浊的淹没了”,而反观我们无时态、无词尾、不需关联词的最具诗意的灵动的“古汉语”,“虽然还没有完全死在语法里,但是几千年它已经衰老:名词无名。动词不动。形容词失去形容。数词无数。量词无量。连接词自缚于连结。前置词死在自己的位置上。”所以诗人要“给名词第一次命名”,“给动词第一动力”,“还原形容词的第一形容”,让“语言随生命还原:还原在第一次命名第一次形容第一次推动中。”(同上,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9月版,第21—22页)诗人要“第二次找回女娲的语言”,也就是找回“汉语言的自由和自由的汉语言”,实质上就是要找回母语的原初新鲜感和初始表现力,找回“晚生”的诗人运用母语自由创造的能力。

任洪渊的创作,无疑给“晚生的诗人”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他的用典、拟作、改写,为具有母题、原型性质的古典文本、意象,注入了鲜活、饱满的现代意识和美感,古典美和现代美互映互衬,在他的诗作中实现了“双赢”。缘此,他的诗作带给读者的审美感受就不是当下的、单一的,而是集合了诗歌史、文化史上无数经典之美的意蕴丰沛的“复调”,因而能让读者得到最大限度的享受和满足。他的影响焦虑心理,使他能够最真切、强烈地感受和体验到古典诗歌的无与伦比的美,看清楚古典诗人和诗歌所达到的几乎无法企及的表现高度,古典的诗艺和美感,因他的审美观照而平添无限的魅力。影响焦虑心理也催动他多方寻求突破的努力,他要找回汉语词汇表现力的完好的“原初”。他甚至用后现代的眼光和标准,去解构经典文本与表现定势,使得他的诗作于古意盎然之中新意迭出。这一切,都给处于后现代生存环境和语境中的“晚生的诗人”们,昭示了一条“向死求生”、“与古为新”的写诗出路。古典也好,现代也好,后现代也好,对待概念,诗人其实不必太当真,诗歌不能困死于概念。重要的是为我所用,写出美感,创生新意。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但对许多“晚生的诗人”来说,却未必做得到。“前现代”注定要走向未来,“后现代”也同样割不断过去,这是由时间的、血缘的、文化的历史连续性决定的,用任洪渊的话说,叫做“无时空”。晚生的诗人,应该进入任洪渊所说的“无时空体验”状态:“时间和空间由你开始由你结束:时间的0度和空间的0度。这一瞬间就是此刻就是最初就是最终。这一片空间就是此地就是来处就是归处。这是生命最纯净的显现:是创世也是终古。”(《女娲的语言》代序,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9月版,第16页)像任洪渊那样感悟瞬间即永恒、是道也是禅的美妙,融时空为一体,冶古今于一炉,在纯粹的生命体验和审美陶醉中,“创世”“终古”——开始并完成自己的诗歌文本创制。
(2010年12月写于扬子居)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典诗学与20世纪新诗》(09BZW038)、河南省哲社规划项目《中国古典诗学与新诗名家》(2006BWX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杨景龙
来源:陟岵
http://www.zgshige.com/c/2017-07-17/3828776.shtml


 纯贵坊酒业
纯贵坊酒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