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第六卷出版发行(目录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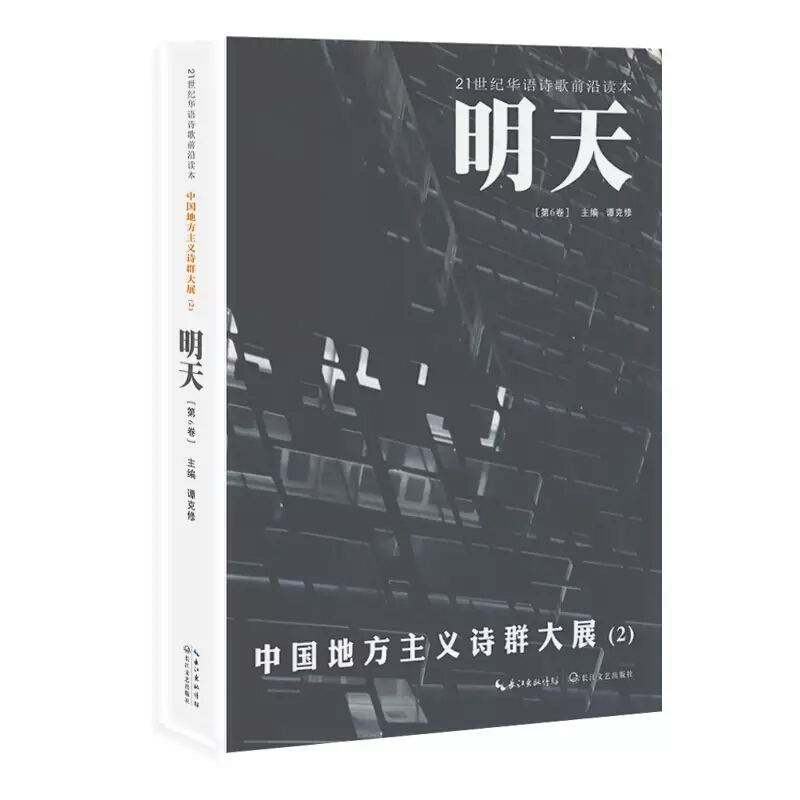
近日,被誉为汉语诗歌前沿读本的《明天》第六卷,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明天》创刊于2003年,刊名由北岛主编的《今天》启发而来,坚持独立的民间诗歌精神,以刊发作品的高迈品质著称,侧重于朦胧诗群以后的国内一线诗人作品,被认为是新世纪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民间诗刊之一。新一期《明天》诗刊的主题是“中国地方主义诗群大展2”。
《明天》第五卷之“地方主义”诗群大展专号出版后,在圈内产生了良好口碑。“地方主义”也成了近几年诗歌领域被广泛谈论的词。作为《明天》诗刊主编,也是地方主义诗学的提出者,谭克修认为,“地方主义”最初的提出,是为对抗 “全球化”和“速度”这两头怪兽的。提倡在瞬息万变的外部世界的面前,要在此时此地,精确地建立起诗人自己的坐标系。让自己深陷于这个坐标,只关注脚下的土地,和土地生长出来的事物。而在艺术风格上,谭克修说,虽然用的“主义”,骨子里却是反各种“主义”的。“地方主义”反对各种标签,无论是生硬的现代主义,或花样翻新的后现代主义,以及各种语言学派标签。打着主义的旗帜反对各种主义,想让诗回到此时此地的脚下土地,即“这里”,回到肉身,即“个我方言”。
谭克修说,这些年,各诗歌圈子之间,不同风格的诗歌之间,依然有很高的美学壁垒,关于诗歌的论争从没消停过。谁都认为自己是武学正宗,别人是邪教。但被他称为“地方主义”先行者的昌耀,如一叶轻舟,已过万重山,是因为他根本不去听啼不住的两岸猿声。地方主义诗学抛开了狭窄的个人诗歌审美趣味,直接从生命与土地之间的根本关系中去确认诗人的有效性。只要他的写作从“这里”出发,用他的“个我方言”,无论他坚守的“这里”是大城市还是偏远地方,是政府大楼、董事长办公室还是菜市场、荒地,也无论他带有自己气息的“个我方言”是口语、书面语,还是泛口语,只要他在生命与脚下土地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语法关系,他的写作就可以是要倡导的地方主义写作。新诗的未来发展空间,将存在于这样的作品里。所以,《明天》第六卷依然聚焦有“地方主义”诗学品质的,此前未曾参与地方主义诗群大展的优秀诗人。《明天》依然坚持此前的编排风格,用10个页码较为充分地展示每位诗人的肖像,随笔和作品。
《明天》第六卷现在已经上市,京东,当当,亚马逊等主要网站均有销售。如果你还没读过《明天》,建议你尽早入手一册,看一看被视为华语诗歌必备的前沿读本之庐山真面目。
主编:谭克修 本期编委:李之平,草树,程一身,谢小青,路云,谭克修
前言:从“这里”出发,用“个我方言”
谭克修/文
最近,我们谈诗时,容易滑入“新诗百年”陷阱。除了各种总结文字,对汉语诗歌未来发展的展望,也成了一个问题。《辽宁日报》记者邀我展望,许道军代表《雨花》杂志也发问:“从古体诗到白话诗,从意象诗到口语诗,从政治抒情诗到‘纯诗’,从‘上半身写作’到‘下半身写作’,中国新诗在百年中摸索向前,表面看来乱象纷呈,实际上充满活力,一直保持着先锋姿态。但近来诗歌好像沉寂下来,一些概念、设想、创新性想象等等似乎都没有超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次‘现代主义诗歌大展’的范畴,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新诗将来发展的可能性空间在哪里?”我对两个问题都力有不逮,只能爽约了。我觉得诗歌不同于科学问题、经济问题,很难去展望。诗歌唯一可信的是,有某个大诗人,写出了让人信服的、可能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了,其作品展示的空间就是新诗未来的发展空间。诗歌未来发展的可能性空间,不是旁人可以规划出来的。即便每个人对自己写作的规划,说到的未必能做到,其说服力,完全仰仗于其作品的现身说法。虽然眼界高了手才能高,但我们通常见到的,还是眼高手低的诗人多。
别说未来可能性问题,就算面对过去一百年的诗歌,这一年开了多少会,催生了多少论文,人们又达成过多少共识?在《辽宁日报》的“重读新诗”系列文章里,汉学家顾彬认为新诗百年以来涌现出来的众多杰出诗人里,冰心超出了她的时代。这个观点显然难以得到汉语诗人的认同。越来越多的当代诗人,认为新诗最初三十年那些著名诗人,其意义主要体现在历史价值上,文本价值并不大。真正有成熟品质的文本,主要出现在 1980 年代以后。这是从总体上得出的印象,若具体深入到最近三十多年的文本,却没有在谁的作品上凝聚了普遍的共识。或者说,包括那些大牌的诗人名字,也在不断地被否定。比如说,当代最大牌的诗人,多年诺奖的热门选手北岛,其作品也不再被视为经典来传颂,质疑声音越来越多。其实,80 年代充当时代英雄角色的“朦胧诗”整一代诗人,他们赢得老外和普罗大众关注的,主要靠作品在意识形态和伦理上的表现。而在洞悉当代诗歌内部秘密的人士看来,老外们关注的,恰恰是我们应该警惕的问题。他们的关注,反而形成了对当代汉语诗歌真相的遮蔽。
对汉语诗歌真相的认知问题,还可以多说几句。2016 年的汉语诗坛,除了新诗百年纪念活动外,还有 1986“现代主义诗歌大展”三十周年纪念活动。关于那次大展的意义,被说得太多,我不再背书。我只想说,第三代诗人都是幸运的,有那次大展作为标志性事件而得以集体崛起。当年参加大展的年轻诗人,年纪相当于现在的“85后”、“90 后”诗人。他们年纪轻轻一夜成名,看上去要归功于那次大展,其实主要原因还是 1980 年代汉语诗歌整体水平不高。不然读惯了直白政治抒情诗的人们,不会把北岛舒婷顾城们不算复杂和晦涩的诗,要称为“朦胧诗”(多多、杨炼等极少数诗人才真正称得上是朦胧诗)。1980 年代的汉语诗歌森林里,应该说并没有几只真正的老虎(多多当年未被列入朦胧诗《五人诗选》阵营,昌耀这样的老虎还处于被遮蔽状态),才一下子窜出那么多小霸王。现在的“80 后”、“90 后”诗人,由于受到更好的诗歌教育,诗歌创作和理论水准,已经要高于当年同龄的第三代诗人们。但现在的年轻诗人只被当作小字辈,难以被真正重视。这也不冤屈,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大波 60 后、70 后的成熟诗人,一群同样是还没有被真正重视的诗人。而“60 后”“70 后”诗人虽已届中年(少数“60后”里的第三代诗人除外),无论多么优秀,前面被第三代“大诗人”压着,似乎永远被视为晚辈,最多是被视为次等重要的诗人。当然,现在谁也没有了爆发机会,大家一起来拼内力,拼文本,也不是什么坏事情。
我并非要刻意否定第三代诗人。在回答杨黎关于“新诗百年”问题时,我明确提出,第三代诗人开始,才出现了有成熟品质的诗人群体。此前的成熟诗人,只有少数个案。第三代诗人里有成熟品质的诗人,也是指部分在中年以后创作能力依然旺盛,且保持了高水准的诗人。我想,一个大诗人的形象,是在不断对过去否定的过程中成型的,至少在老年痴呆症等身体疾病出现以前,创作力可以持续旺盛。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作品会显示出老而弥坚、炉火纯青的质地。年轻诗人,再有才华,只能说他早慧,很难说他早熟。年龄不只会给语言带来精纯程度的提升,更主要的是,带给诗人对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深度的提升。诗歌的心理深度,靠的是从内部裂开的精神地层的力量,这只能由随年龄而长的成熟心智给予,而不能依赖于语言的力量。何况,若一位诗人来到中年,还沉迷于年轻时期那种表层化的修辞,只会给诗歌带来伤害,很难写出真正成熟的作品。
前几日在西宁的昌耀诗歌研讨会上,批评家陈仲义从传播学角度,谈到昌耀诗歌的经典化程度远不如海子。如果这经典化主要指的是作品阅读量,当然。海子式的忧伤、幸福,和华丽的诗句迎合了这年代多少浮浪的心啊,他是华夏小资的最爱。而昌耀式的苍凉、孤绝,和滞涩的诗句,拒小资们于千里之外。他的诗或永远也不会流行。海子是天才型诗人没错。我在想,如果海子还活着,现在会怎么写,会不会对自己年轻时的写作——那种在神性尺度之下完全拥抱农业意象系统,大量采用传统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的典型青春期症候写作,不以为然?当然,假设不成立,那种诗歌内部的激情足以将一个人烧死。这样的生命写作,当然也成立。虽然是坐在书桌前自己燃烧自己,并不试图与脚下的土地建立某种关系。何况不少人喜欢青春的海子飘扬在空中,不要落地。但我不看好这种海子式高蹈之舞,在未来年代里的持续生命力。只要多一些明白诗人,不继续误传。而昌耀属于熟透了的诗人,他通过与青海高原之间牢固的心灵契约,在生命和土地之间建立的语法关系,不会追随这时代的大众口味流行或消逝。
我们无法猜测海子到中年以后的写作会如何,会不会转型。但我们看到与海子同龄的第三代诗人里的多数,包括曾经被视为天才的诗人,创作难以为继的窘况。他们中的一些诗人,有的虽然还在写,但水平明显不济。包括我年轻时尊重的几个人。他们在中年以后的作品,并没有被年龄带入成熟地带。他们的作品和后来者作品比较,也明显处于下风。这促使我回过头去看他们年轻时候的作品,包括那些所谓的名作。很明显,它们已褪去了光环。其实,他们在过去的年代里本来就算不上是多好的诗人。但历史造就了他们,给了他们大牌诗人的头衔。遗憾的是,他们也过早地把自己交给了那段历史。虽然他们的名字现在依然炙手可热,是各类活动热衷邀请的座上宾,被众多盲从者,包括学院派评论家们奉为大诗人。
那次昌耀诗歌研讨会上,众多学院派评论家发完言后,轮到诗人发言。我一开口说出的是,我不同意前面几位评论家的意见,而不是通常该说出的,我同意前面几位评论家的意见。第二天午餐时,我和同桌的谭五昌教授发生了点小争执。他说作为会议主持人,得到的反馈意见是,我的发言得罪了好几位评论家。我明白,这些年来的口不择言,无意中冒犯了一些人。虽然我尊重所有的同行,无意冒犯任何人,心里更没有设置过任何一个敌人,但我这个人对有些问题太过较真,说话也不太讲究。但造成误解的根本问题,应该出在对优秀诗人的判断上,诗人和评论家常有比较大的分歧。对百年新诗和当代诗的认识,我常和学院派专家们意见相左,也不奇怪。他们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朦胧诗及以前那些已成为书本知识的著名诗人,和少数几个第三代诗人。我和另外一些诗人的看法是,朦胧诗及以前的文本,有保留和研究价值的只有极少数。真正有成熟品质的新诗,还是第三代及以后的文本。
其实我也理解学院派们的犹豫不决。当代诗,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可靠评价系统。曾有不少人讨论过什么好诗标准,试图像古诗一样建立一套评价体系。但那刻舟求剑的办法,已经完全行不通。要说现代诗和古诗最大的区别,是前者在形式上的不可重复性。每一首现代好诗要求的形式必须是独特的。按柯尔律治的“有机形式”说,诗的形式是由内在冲动塑形的。由于每个人,每一次写作时内在冲动的不确定性,那么,其塑形的技术程序只能是一次性消耗品。而且,这技术还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没有尽头,每个现代诗人操持的技术大相径庭。现代诗的形式技术从来不是一种稳定的物质形态,成功的技术都融化在作品中,没有谁能剥离出来。每个诗人操持的技术都不一样,而且很难进行技术转让。你在外围谈论诗歌的任何具体技术,必然是笼统、抽象、无效的。所以我知难而退,几乎从不谈具体的诗歌技术问题。需要提醒的是,好诗虽然要强调技术,你若过于沉浸在技术里,也只能成为匠人,成不了真正的好诗人。从技术上升到更宏阔的理论,才能有一种格局的转向。
就算评论家意识到现代诗形式规则的变化性,而自己不常浸淫在写作现场,对各种变化难以吃准,很正常。如果他们也不太信任后来者的写作能力,哪怕那些优秀的“60后”、“70 后”已人到中年,来到了他们创作能力的巅峰时期,他们在评论家眼里,离经典化、离大诗人坐标,还有十万八千里,不能成为书本知识,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然,我说的是一般情况,那次会议的学院派评论家,也并不都对我有意见。有人就私下和我交流,说从我的发言里得到了启发,认为对当代诗的判断,需要建立在诗人和评论家的不断交流和碰撞上,不能再各说各话,光说一些好听不中用的拜年话,形成了现在诗歌批评和创作的严重脱节。
上面这些,似乎和我要说的地方主义话题很远了。荣光启写过一篇文章,从我提出“地方主义”诗歌运动的意图进行谈论。文章意思非常直接:“我们”——“第三代诗人”之后的这一批非常活跃的“60 后”、“70 后”——才是最应该被关注的“地方”。似乎地方主义运动变成了类似于当年 1986 年现代主义诗歌大展一样的行动。当然,如果地方主义诗歌运动,以一群当代诗坛最有创作实力的诗人的崛起为标志,恰好达到了改善当前诗歌生态的效果,把这次运动往诗歌政治学方向理解,也没什么关系。但地方主义运动的动机不是这样。有人已经把“地方主义”看成一个诗歌流派。我还记得诗评家沈奇在电话里的语气,他说中国新诗百年以来,有诗学价值的诗歌流派几乎没有。多数只有命名没有诗学,那命名还是权宜的,可以说称不上什么流派。看到地方主义诗学,以及这面旗帜下的这些优秀诗人,他有些兴奋。“地方主义”诗群是严格意义上的流派吗?这个问题交给专家去认证吧。虽然“地方主义”提出了自己的诗学主张,在这面旗帜下的诗人,更是一个个的独立写作者。他们之间,并不是像一般流派那样,讲究团结的力量。或许,在诗人之间,不团结会有另一种力量。无需讳言,这里面的诗人,诗学趣味分野非常大,他们谈到对方的写作时,也是互有臧否。但这不影响诗人们对“地方主义”诗学的大致认同。所以“地方主义”这面让部分人感觉不是太舒服的旗帜,才能在这个如此碎片化的年代,啸聚起各地英雄豪杰。
地方主义诗学提出来已经三年,依然有人对“地方主义”这个词很敏感。说怎么不取一个看上去更先锋的名字?哗众取宠一下也好。“地方主义”,容易让人望文生义,觉得土鳖,产生反感。诗群内部也有人反对,是我固执地坚持了这个名字。确实,在这个如此崇尚自由、个性的年头,很少有人愚蠢到动用带有“准则”性质的“主义”这种生硬的词。事先我想到过旁人的第一感受。可如果我本来就带有某种戏谑心理呢?我甚至不反对别人轻率地认定这个命名的可笑之处。有一位诗人还写了打油诗,用“臭豆腐”来形容“地方主义”。他是一位常年在国内国外两头跑的诗人,觉得自己见多识广,理所当然就这么认为了。我们在一个茶楼简单辩论过几句。他举例说,天上的云就没有地方性。我当时很惊讶。我说,在敏感的诗人那里,云也是有地方性的。长沙的云和斯德哥尔摩的云,当然不一样。我私下里还认为,这种敏感性,也是辨识诗人好坏的指标之一。他这么认为,也不奇怪。常在国内国外跑的诗人,享受的是“全球化”和“速度”红利。而“地方主义”对抗的就是“全球化”和“速度”这两头怪兽。当湖南诗人和新疆诗人在看同样的影像,长沙诗人和武汉诗人可以一小时高铁幽会情人,这不仅是时空的缩小性变化,而且是可能致使诗歌地方性的消失。这种时空的缩小,其实也是一种时空的分裂。我们的诗人身份,可能同时是北京的,也是广州的,是中国的,也可以是美国的。一些诗人就在这种身份的短时段内并存中失去了自我。时空的分裂,最终导致了自我的分裂。自我的分裂就是诗人地方性的失去。我希望“地方主义”诗人,可以对此做出有效的抵制或对抗。
地方主义诗人的重要性,正是在这种对抗性中凸显出来的。在回答杨黎“新诗百年”问题时,我谈到新诗要用汉语发声。昌耀的诗,不仅在语言上有滞涩的古语化倾向,汉语气质纯正,更主要的是,他凭一己之力,为汉语诗歌开辟了另一条路:用生命与脚下的土地建立起血脉联系。从土地的苦难生存直觉中滴出来的诗,发出的必然是纯正汉语的声音。昌耀可说是新诗史上率先做到“地人合一”的典范诗人。因此,在三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我奉昌耀为地方主义诗学的先行者。在地方性写作中,强调先建立精确的时间与空间坐标系,把自己像钉子一样钉在具体坐标上,以感受坐标里所有事物的细微变化,获取打通主观经验与客观世界之任督二脉的能力,帮助他体验到各种共时性事件带来的深刻的和谐力量,用内在的磅礴功力重新缝合这支离破碎的世界。这样的诗人,才能写出带着体温的诗,有生命痛感的诗,才能揭示自己和这片土地存在的真相。我们看到,广袤的青海高原,因为有了钉子一样的诗人昌耀,将生命和语言持续有力地注入,已经发生了神奇的变化,成为中国西部最有诗性意义的场域。2000 年 3 月 23 日,昌耀在西宁离开这个世界时,他或许没想到,自己用青海高原的 45 年生命换来的诗篇,并没有随他而去,而是在更大范围内发酵。这位远离风起云涌的当代汉语诗歌运动的西部 “地方性”诗人,已被很多后来者视为当代汉语诗歌的一座“高峰”,甚至是同代诗人的“孤峰”。
这些年,各圈子之间,不同风格的诗歌之间,依然有很高的美学壁垒,关于诗歌的论争从没消停过。那架势,谁都认为自己是武林正宗,别人是邪教。昌耀如一叶轻舟,已过万重山,是因为他根本不去听啼不住的两岸猿声。地方主义诗学抛开了狭窄的个人诗歌审美趣味,直接从生命与土地之间的根本关系中去确认诗人的有效性。只要他的写作从“这里”出发,用他的“个我方言”,无论他坚守的“这里”是大城市还是偏远地方,是政府大楼、董事长办公室还是菜市场、荒地,也无论他带有自己气息的“个我方言”是口语、书面语,还是泛口语,只要他在生命与脚下土地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语法关系,他的写作就可以是要倡导的地方主义写作。
这里,要特别提醒那些还把地方主义和乡土诗混为一谈的人,看到地方主义对城市诗学的贡献(见拙文《城市塑造着我们现实命运的具体形态——关于城市诗和城市诗学答许道军问》)。这日渐趋同的城市空间,由于有像钉子一样的地方主义诗人注入自己的生命体验,将变得迥异于它出现在照片里的公共空间形态,而成为带有诗性意义的场所。这城市公共空间,将成为属于诗人自己的世界,让他找到归宿感、安全感,以将自己安顿下来,并具有了特殊的场所精神。同时,这场所精神,也安顿了另外一些找不到灵魂归宿的同道。所以,即便诗人与其他市民一样生活,坐同样的地铁、公交,过同样的街道,呼吸同样的广告,但他们见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城市。可以说,城市空间再如何趋同,由于有了地方主义诗人对具体环境的场所精神的发掘,对人和城市的关系的深刻理解,用“个我方言”探测到城市的本质和存在的线索,就有机会把同质化的城市空间,变成多样化、复杂化、异质化的谜一样的空间,把碎片化的空间重新缝合成一个完整的世界。至此,我们才能发觉,人的本质、诗的本质和城市的本质,实际上处于某种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复杂关系中,它们相互遮蔽,又相互敞开。
当代诗歌的领袖式人物还是北岛,他依然代表着汉语诗歌被诺奖提名。虽然 1986年那次现代主义诗歌大展,在美学上差不多把北岛打倒了。但北岛的出现,对新诗的合法性和文学地位,都有好处。他若代表汉语诗人获得诺奖,我辈当然乐观其成。从诗歌的社会环境,和诗坛内部的混乱生态来看,新世纪出现下一个北岛的可能性并不大。你诗歌写得再好,也很难获得北岛在过去几十年来的影响力。除非有谁真能得到诺贝尔奖的加冕,吸引来盲从的读者群。过去许多年的新诗,或许像许道军在问题里描述的那样,诗坛表面看来乱象纷呈,实际上充满活力。但这种所谓的活力,各种以吸引眼球为己任的诗歌流派或主张,表明的是诗人心态的不成熟。心态不成熟的诗人,很难写出成熟的诗歌。所以,“地方主义”的提出,与其把它视为一种新的主义,不如说是对各种主义或流派的反对。“地方主义”一词刚出现时,我听到的质疑不少。其中也有我的朋友。现在,多数质疑转为了支持。他们明白,我这里用的“主义”,骨子里却是反各种诗歌主义的。“地方主义”反对各种标签,无论是生硬的现代主义,或花样翻新的后现代主义,以及各种语言学派标签。我是打着主义的旗帜反对各种主义,想让诗回到此时此地的脚下土地,即“这里”,回到肉身,即“个我方言”。所以,对前面那个关于新诗未来发展空间的问题,如果一定要给出答案,我觉得它将存在于有效地建立起生命和土地之间的语法关系的作品里。
地方主义诗学提出后,我看到一些诗人,已将它运用到具体的写作实践中,并产生了好的效果。本期“中国地方主义大展 2”,继续将作品是否有效地建立起生命和土地之间的语法关系,作为主要选稿依据。对参展人选和具体作品,编委之间也有些争执。但保留些争议也未尝不可。考虑到容量有限,参加过2014年“中国地方主义大展”展出的诗人,统一不再作为本次大展约稿对象。对于另外一些还没有进来,但有意参与地方主义大展的优秀诗人,我们将继续用专号展出。我希望好诗人总会在《明天》出场,《明天》也会给每个出场的好诗人,以足够的尊重。
2016.11.20 长沙
目 录
(按诗人所在省份纬度,自北向南排序出场)
前言 谭克修 从“这里”出发,用“个我方言”
吉林 孙慧峰 描绘和捍卫人类空间中最个人和内部的东西”
甘肃 李志勇 有关甘南的几句
阿 信 我在这里写作
辽宁 李轻松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疯人院
河北 韩文戈 诗歌写作札记
雷武铃 诗歌写作中的地方性问题
北京 西 渡 诗的源头
周瑟瑟 栗山:我的精神体
姜 涛 “郊区”或许是个人的地方
严 彬 南方的阴影下——为“地方主义”而作
山西 逼 戈 黄河向西流
陕西 伊 沙 守望长安
宁夏 杨森君 关于地域诗歌的几个片段
山东 轩辕轼轲 脑海的地方主义
河南 魔头贝贝 宛若诗歌
夏 汉 诗,在故乡与童年之间
四川 余幼幼 我等待的东西总会来
江苏 叶 辉 地气
安徽 余 怒 作为写作基础的语言观
张建新 与时间节点里的那个我遥相呼应
湖北 黄沙子 诗歌源头从未改变
李建春 地方主义与在地性
上海 肖 水 在另一地
浙江 泉 子 我在骨子里是一个徽人
商 略 道通著形迹,期无负初心
湖南 草 树 诗,生活,地方主义
横 关于我的文字与我的家乡
江西 曾纪虎 读和写,终不过是意味阑珊的游艺
贵州 赵卫峰 诗歌的地方性及其他
钱 磊 漫诗录
云南 王单单 我和诗歌,以及故土
福建 汤养宗 诗歌的靠椅
顾 北 躲在小楼写作
广西 非 亚 生活,与写作
台湾 颜艾琳 微美的起点,辉煌的落日
香港 廖伟棠 香港,我的诗歌和生活
海南 衣米一 陌生的雨落在陌生的屋顶上
评论 赵卡 作为一种“小语种”修辞的地方主义写作


 纯贵坊酒业
纯贵坊酒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