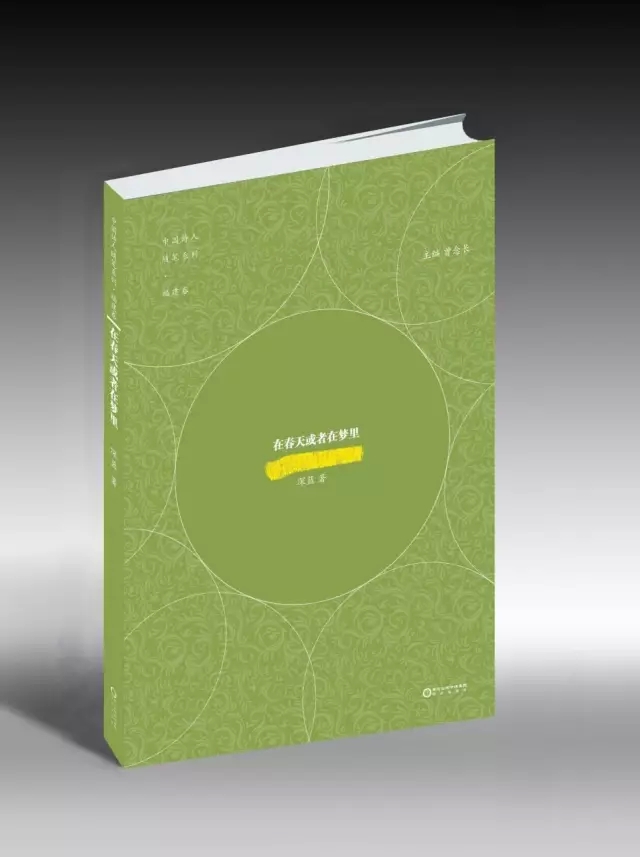
诗人深蓝随笔集《在春天或者在梦里》出版
诗人深蓝随笔集《在春天或者在梦里》2015年12月由阳光出版社出版。本书是作者近十年来的散文随笔作品集。十年来,她是“小镇上的单相思者”,也是“五里桥畔的梦呓者”。她从情感、生活、行走中的点滴感悟出发,自在随意地书写涂鸦。她的文字里有悲喜,有冷暖,有失落,也有希望。她向往远方和彼岸,热爱不羁与自由。她用感性温暖的笔触抒写尘世里最最琐碎的心情故事,以独到开阔的视角思考生命的沉重与轻盈。她的文字,清新不失成熟,成熟不失纯真。本书和安琪《女性主义者笔记》、鲁亢《被骨头知道》、老皮《知天命》、何奕敏《去远方寻找自己》一起,构成“中国诗人随笔系列•福建卷”书系,书系由福建省文学院曾念长博士作序。
目录
时间的尖叫
以荷的气质生活
回不去的故乡
春天的礼物
明媚的忧伤
你也在这里
是否你已将我遗忘
让我抱抱你
梦中的向日葵
我们的爱情
豆豆十岁
生活如旧
想念母亲的粽子
画出心中的美好
又见风的那端
落到一朵云上
开满兰花的峡谷
策马归来
纯手工活
整个八月
人生如戏
此刻已然过去
翅膀隐隐还在
南方
雨季漫想
桥上的光阴
等爱的狐狸
你真正想要的
烟雨韶光
这个茶香弥漫的秋天
山城记忆
触不到的恋人
如果尘世将你遗忘
现在还和相爱的人在一起吗
在水上书写
巴掌大的爱
亲亲,我的宝贝
花事
细微的存在
梦见一条会走路的鱼
那个叫扬的情人
秋日清源
你的名字
清晨从桥上回来
是谁推开黑夜的门
似有暗香盈袖
通往春天的地铁
突然很想你
从山中归来
褪色的抒情
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握紧回程的车票
行走江南
有谁是你
又见蔷薇花开
这有点暗淡的人生隧道
云中谁寄锦书来
那场下了千年的雨
一个令人不解的偶然
空岸
尘世很远,幸福很近
余生
我在这里活着
你永远看不见最初的那个人
我始终坚持的
黯淡也是明亮的
彼岸咖啡
不舍
尘世的尘
匆匆
仿佛有所等待
孤独的网
忽逢桃花林
像所有的天经地义
窗台上的那只鸟
也寂寥也安谧
有座岛屿在那里
赠你一朵
像石头陷入河流
就这样走啊走
永不再来的梦
蓝不是抽象的事物
老街转角
彼岸花
每篇字都是一个残局
你会不会像正午的凤凰木
谁正灼灼盛开
“每一次分手都无可挽留”
那样的两棵树
周渔的火车
梦里走过的路
恰似一朵烟花
山水有相逢
三峡行
深灰夜空,以及晚风
四月初的衬裙
突然间的自我
我在
小纸条
绚烂也许一时
“一直飞到你悲伤的心所在的地方”
银色的光芒
遗失的一页
挽歌
听到春天逝去
自己的书房
当我老了
如尘如寄
原来不是那么寂寞
曾见一人
一个人走着
“我总是意犹未尽地想起你”
寂静,也是喜悦
——————————
【书摘】
策马归来
深蓝
傍晚天色黯然,似乎酝酿着一场雨。这样的天气,特别适合一个人到桥上走走。拎一把伞走下楼,没走几步,细雨迷蒙。好一场及时雨啊。
这个傍晚,一定是上天有意安排,让我得以一个人安静地行走。静静地走,听着林木间追逐的风声,细细的雨声,听着斑驳的岁月里心头的蛩音。是的,我听见了。
那一面湖,宛然恩慈的母亲,敞开怀抱,迎接它远行归来的孩子,一个个顽皮的小雨点。那滴答滴答的声音,是拥抱的声音,还是轻轻的耳语?岸边的广玉兰,美人蕉,在雨里怒放。有一种特别的宁静与娇羞。轻轻地拾起地上的一朵白色花朵,花瓣柔美,仍有余温。让我想起青春里的那一树油桐,一地不忍踏过的芬芳。青春终是远了,留下我们在未知的路上踟躇。此时的我,终于可以轻轻捧起一朵花,没有忧伤,轻轻放下。那一树鲜活的桃红深红,和着身后夏天葱郁的深绿粉绿,徐徐展开一个雨后的夏日黄昏。
是不是会有一天,我可以站在春天的湖边,用最温柔的声音告诉春天、湖水,告诉那只多少回游进我梦里的蓝色水鸟,告诉这肃穆而活泼的自然万物,我终于老了。用了很多很多的挣扎,很多很多的迷惘,很多很多的张望,终于抵达,安详地老去。那时,会不会有清澈的雨水从眼睛里漫溢出来,上苍恩赐的眼睛依然眷顾着我和我的世界?
又突然想起一首歌,试着哼出一两句: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喜欢一个词,策马奔腾。人生的路千万条,我们极少伫立凝望,只是策马奔腾。很多人被路过,很多事来不及完成。然后有一天,站在岁月的尽头,回望那苍茫的来时路,会有一些遗憾和怅然吧。
打个电话,给谁?告诉他,这里只有一个人和一场雨,一面湖和一座桥,天然去雕琢的树木花朵,灰色的天空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明净柔和。或者发个简讯给谁。告诉他,我在湖边在桥畔,一把格子伞,撑开一小片晴空,其实不打伞亦无妨,雨下得未免温柔,一点儿也没有往常凌厉的撒泼。
终于还是没有,如果此刻无人将我想起,也请让我忘记尘世。一个人的漫步,天马行空,以梦为马。然后,在意念里系好我的那匹马。我回来了。
2012.6.14

深蓝:原名黄美瑜, 1974年生。小镇上的女教师。书写文字,作品散见于报刊。系福建省作协会员,泉州市作协会员。出版过诗集《等待一朵蕾》,散文集《静寂的角落》。曾获泉州青年文学奖等。现居福建泉州。
————————————
【总序】
走向“文学广场”的诗人们
——《中国诗人随笔丛书•福建卷》序
文/曾念长
就文学体式而言,散文与随笔可并成一大类。若要一言以蔽之这类体式之特性,我斗胆说:公共性。它是众多文学体式的公约数,也是无数社会性言说的公约数。所以,诗人、小说家往往要附带写写散文或随笔,学者、医生、演员、商人和官员,数不尽的各行各业的人,都会跑到散文或随笔这块领地上卡遛一番。它是文学的“公共广场”,无论你是专业的文学写作者,还是其他社会领域的各路神仙,只要来到这个广场,大家就享有同等的“文学身份”,就可以以文学的名义说话,甚至聊聊文学本身的问题。
作为社会物理空间的广场,天然具有两种功能属性:抒情性和议论性。在农村,村庙就是广场。每逢佳节,村民在此狂欢;但逢大事,族人在此定论。在城市,广场的双重属性在聚合,在放大,还变幻莫测地相互转化着。君不见,三十年前广场批斗小兵横行,三十年后广场歌舞大妈扰民。而我想说的是,散文和随笔,作为纯粹精神空间的“文学广场”,也有这双重属性,并且它们在这个时代发生着复杂的转换关系。
一般而言,散文亲抒情,而随笔亲议论。这种天然分化与中国古代的文章学传统并不相符,而是现代文学体式发生流变的结果。这里面不得不提鲁迅的特殊贡献。通过他的海量写作,杂文从广义的散文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种以纯议论为要义的文学体式。显然,在这个体式茁壮成长的背后,隐含着特定的诉求:对社会公共问题的介入。其结果是,散文中的抒情性和议论性分道扬镳了。不过,自1990年代末以来,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杂文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快速衰变为两个支流:一支最大限度地删除了杂文的文学性,发展为大众媒体时评;一支则向文学性回归,重新融合散文的大统,发展为随笔写作。于是,散文的抒情性与随笔的议论性在慢慢靠拢,“文学广场”上的两种声调正在汇合。让议论变得更加柔软,让抒情变得更加有力,这是世纪之交发生在“文学广场”上的交响曲。
这套丛书名为“中国诗人随笔丛书•福建卷”,其中对随笔这一文体的界定,必须放在这个时代的“文学广场”中给予具体的考察。随笔不仅仅是一事一议,而是在与散文大统的重新融合中走向新的“文学广场”,走向辽阔的精神世界。似乎有人说过,21世纪的写作是随笔的写作。我希望那些有考证癖的人能够考证出这句话出自何人。如果“查无此人”,那就当是我说的好了。就文体的普适性而言,我以为这个说法是符合实际的。随笔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章”,可长可短,可记事可议论可抒情,可写一己之私亦可言天下之公。它有其他文体不可比拟的精神容量,因而往往承接了从各种狭窄、僵硬的言说空间中溢出的话语。它是怎么都可以的一种言说体式,唯独如此,它才能够呈现言说者的真诚品质和精神形状。诗人于坚认为存在一种“散文化的写作”,它是“各种最基本的写作的一种集合”,其“出发点可以是诗的,也可以是小说的、戏剧的,等等”。我理解于坚所说的“散文化的写作”,就是接近于已被我们的文体观念接受了的随笔。它是一种最公共的写作,也是一种最自由的写作。这种写作本身,就是个体言说与公共言说的有效结合。
有一种传说试图指出,福建是一个“诗歌大省”。如果仅仅是指诗人的数量和影响力,我以为这种传说言过其实。哪个省域不是诗人成群?又有哪几个省域举不出若干有影响力的诗人?但我以为,如果是指诗人在一个特定时代中的精神境遇,福建的诗人及其写作是极具典型性的。从历史上看,闽人文学长于诗文,而对小说几乎没有什么贡献,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至今尚未完全走出这种宿命的循环。其中的原因,很难给出一个实证性的定论。一个较具有说服力的观点认为,闽地方言制约了闽人的大众化写作,因而也就失去了进入白话小说领地的优势。这一说法或许不假,但我以为还有一个因素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那就是闽人精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内排遣”传统。闽人是习惯于自我言说的。他们往往向自己的内心,而不是向外部世界寻找人生问题的答案。在依然保留着传统生活气息的乡村地区,拜神依然是许多福建人极具日常化的行为。他们习惯性地在神像前喃喃自语,实则是在与自己的心像一问一答。这种向内延伸排遣路径的精神构造,也正是诗歌和散文的天然形式。相比之小说指向社会的丰富性,诗歌和散文更直接指向了个人内心的细密纹理。闽人对诗歌、散文以及散文诗的偏爱,或许正是缘于此。他们的天然节奏不是东北人的唠嗑,不是北京人的段子,而是以沉默为外部表征的内心絮语。这种精神特征也让闽人背负了一项无端的罪名,那种通往内心的诉说与自救,往往被假想为深不见底的心计。我以为这实在是一种误解。人们对自我言说的恐惧与排斥,在“早请示、晚汇报”的时代一度达到极致。如果我们不理解自我言说是人类话语结构的重要基石之一,也就理解不了我们为什么要反驳那场极端化的话语运动。正是在这一点上,以蔡其矫、舒婷为代表的福建诗人,凭着对自我言说的时代性觉悟,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新诗潮中成为一面旗帜,也为福建诗歌赢得了至高的荣誉。
作为一种带有地域性特征的文化存在,今天的福建诗人(也包括批评家)依然保持着如隐士般构建自己的内心世界的精神传统。如厦门的舒婷、陈仲义,福州的吕德安、鲁亢等等,他们对这个时代的公共话语似乎缺乏志向,因此也很少像文化中心省份的诗人一样甚嚣尘上。与其说这是诗人的一种刻意姿态,不如说这是诗人的一种心灵隐喻。诗人就是这个时代的隐士。他们是一种逃遁式的存在,真实地辐射着一个时代的精神气场,却很少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太阳来到了隐士的家/隐士却不在家”。这是江苏诗人胡弦的诗句,在此我愿意借它来阐明这个时代的诗人的心灵志。但我还想说的是,现代诗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性存在,不可能完全隔绝于世。他们往往还借助诗歌之外的形式,介入公共事物,与外部世界进行对话。在此意义上,我们这个时代不乏有令我们素然起敬的国内同行。比如于坚,这位自称“在散文写作中向后退”的云南诗人,实际上是通过随笔这条言说通道重新抵达时代现场,将文学的态度和立场带入大地与环境、建筑与城市、本土化与全球化等一系列社会性问题。再说王小波,他不是诗人,却在小说中前所未有地开辟了自我言说的路径,因而比许多诗人更早抵达诗性的精神国度。即便如此,他还是出色地完成了一系列直面时代议论的随笔写作,并称这是知识分子在承担应有的道义和责任。我想诗人写作随笔的意义也许就在于此。诗人不仅仅是诗人。他首先是个人,具有每个人通常都有的两面性,以及由两面性拓展开来的多面性。当诗歌在表达一个人的多面性时变得言不及物,诗人就会借助另外一种表达形式,以探求诗人与世界之关系的多种可能性。写随笔就是诗人延展自己的精神空间的一种有益尝试。正如前文所言,随笔是“文学广场”,是个体言说与公共言说的交汇地带,也是诗人出来卡遛的绝佳场所。
我想这套丛书的多数作者是以诗人为身份自觉的,因此才有“诗人随笔”一说。这么说来,我们似乎可以将这些随笔作品看作是诗人的“副产品”。一个成熟的诗人对自己的作品是极为苛刻的,我想他们对自己的“副产品”也应抱有同样的态度。至于这些随笔写得如何,实无由我评说的必要。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再费口舌也是多余的。我更想借这个机会,谈谈对写作的两种精神向度的看法。呈现在我眼前的这些随笔作品,更多是延续了福建诗人的自我言说的精神传统。这种“路径依赖”是一种常见现象,也符合诗人的自我期待,以及多数人的阅读期待。一位学者来到广场,未必就能抛弃书斋里的习惯,遇见新鲜事恐怕要寻根究底一番,甚至与自己“死磕”。这在许多人看来是合乎常理的。依此类推,诗人出现在广场,也有自己的习惯性方式。他们左顾右盼,略带神经质,却不愿参与任何“群众聚会”,就像传说中的“打酱油”者,一溜烟又飘走了。我作此类比,仅仅是想说明,诗人自有诗人的专注精神。诗人最关心的,终究还是自己的内心世界。即便是写随笔,他们还是习惯于将文字的光亮照向自己的心灵空间。这本无可厚非,但又何尝不是一种遗憾!时代的声音牵扯着人心,我们又岂能充耳不闻?但我并非是要主张诗人们去做单刀直入的社会时评家。诗人自有表达时代经验的独特方式。像安琪一样立誓做一个女性主义者,将诗人与时代的紧张关系和左冲右突毫无保留地呈现在字面上。或像鲁亢一样写留学往事,写对疾病与死亡的深度凝视,并将它们与读万卷书的知性体验融为一体,再和盘托出。凡此种种,都是诗人介入公共言说并借以重构自己的精神世界的不同尝试。
我之于这套丛书的不少作者而言,算是老读者了。这里我指的是他们的诗歌。对于他们的随笔作品,我却读得较少。我愿意将这一次的集中阅读,当作一次发现之旅,去看看我似曾熟识的诗人,其实还有着不为人知的更为丰富的一面。
2014年12月

曾念长:文学博士,现供职于福建省文学院。


 纯贵坊酒业
纯贵坊酒业




